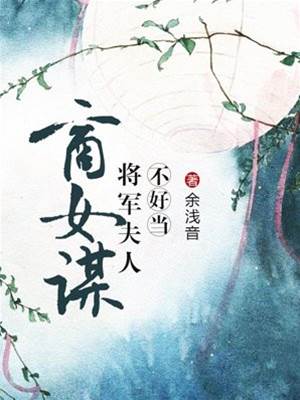《錦衣殺》 第22章 幫忙
陸珩站在堂屋, 詳細詢問大牢里的狀況,越問臉越沉。隔著帷幔,王言卿也聽了個大概。
保定終究不是京城, 看守不及京城詔獄嚴,梁文氏是眷,再加上曾經是錦衛千戶的繼室, 被關到了專門的區域。夜后,梁文氏用首飾賄賂獄卒,請他們去外面喝酒。自己則趁無人看守, 用帶自縊了。等巡邏的人發現時, 已經氣絕。
旁邊,留著一塊皺皺的中布料, 上面是用手指寫下的認罪書。供詞中,對殺害梁榕、陷害梁芙一事供認不韙,聲稱所有事都是做的, 梁彬只是礙于母子分, 被指使。
獄卒發現梁文氏自盡后慌忙出來報信, 驚了牢獄里其他人。梁彬聽到梁文氏死后大哭一場, 之后咬死了自己不知道,將罪責都推到梁文氏上。
陸珩聽到這里眸已經深不見底,他揮手,示意錦衛先退下,折朝王言卿走來:“卿卿,你自己先睡, 我去牢里看看。”
王言卿滿臉擔憂, 連忙走下腳踏,朝陸珩迎來:“二哥, 以我對梁文氏的了解,絕不是會畏罪自殺的人。突然自盡,肯定另有目的。我猜測,可能覺得自己難逃一死,便在牢里自縊,以保全真正的兇手。這樣看來,恐怕梁彬才是殺害梁榕的真兇。”
陸珩也是這樣想的,他將梁文氏和梁彬一同收押,但心里更傾向梁彬。梁榕是窒息而亡,梁文氏理論上有作案可能,但在男天然的力差距下,梁彬捂死梁榕的可能更大。所以陸珩派人去審訊時,大多也奔著梁彬去。沒想到他稍不留意,竟然讓梁文氏鉆了空子。
梁文氏和梁彬都是錦衛家庭的人,多年來耳濡目染,對刑獄也略有了解。無論梁文氏是不是殺害梁榕的兇手,謀害繼子、誣陷繼已經坐實,就算把放回梁家,梁氏族老也會自盡的。既然是一樣的結局,為何不搏一把,至保住的兒子。
Advertisement
梁彬聽聞梁文氏自縊后也很快反應過來,將所有罪狀都推到梁文氏上。如今死無對證,再加上梁文氏的認罪書,殺害梁榕的兇手只能以梁文氏定案了。
可是,這恰恰證明,兇手不是梁文氏。要想翻案,除非真正的兇手招供。
然而梁彬不可能招供,招了就是死,咬死不說便只是從犯,能撿回一條命。若是案宗以梁文氏定案,送回京城復核時,一定會被陳寅拎出來大做文章。到時候,倒霉的就是陸珩了。
這就形一個死循環。想要讓一個有可能逃出生天的兇手承認自己殺人,談何容易。王言卿擰著眉,問:“二哥,你打算怎麼辦?”
陸珩微不可聞嘆了聲,說:“原以為關起來嚇一嚇他們就會招供,沒想到,竟是我小瞧他們了。保定府的人手終究不能和京城比,若是在南鎮司,怎麼能出現嫌犯自盡、消息還傳到同犯耳朵里的疏。罷了,我親自去審吧。”
王言卿看了眼天,表凝重。夜已經這麼深了,陸珩昨夜便沒怎麼睡,今夜還去大牢里審問,太傷了。王言卿沉默片刻,突然說:“二哥,我興許能幫你。”
陸珩行停住,回,長久看著王言卿。王言卿被那樣的眼神看得慌,纖長的手指握了握,對陸珩擺出一個笑,說:“二哥,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并非想對你的事指手畫腳。如果你不高興……”
“怎麼會。”陸珩拉起王言卿張攥著的手,眼眸依然深深著王言卿,里面似乎藏著什麼王言卿看不懂的東西,“你愿意幫我,我還來不及。我是怕你不高興,大牢那種地方暗晦氣,你一個姑娘家,肯定不喜歡靠近……”
Advertisement
王言卿長松了一口氣,二哥不是生的氣就好。王言卿連忙說:“沒關系,我不在意。習武之人不避諱生死,只要能幫上二哥,我做什麼都愿意。”
陸珩眉尖了,分明在笑,眼神卻讓王言卿覺得不安:“真的?”
王言卿本能覺得二哥不高興了,但沒想懂二哥為什麼不高興,下意識點頭:“真的。”
“好。”陸珩握了王言卿的手,沒有往外走,反而拉著朝屋里走去,“不過你現在還在月信期間,要注意保暖。地牢里太了,你不能穿這服,要換更厚的。”
王言卿聽到陸珩以這麼自然的口吻提起的小日子,臉都紅了:“二哥!”
陸珩回頭,誠摯地看著:“怎麼了?”
王言卿紅了臉,眼神憤,支支吾吾,怎麼都無法說出口。陸珩了然地笑了,拉過王言卿說:“這是很正常的事,說明卿卿長大了,沒必要遮遮掩掩。你先在這里換服,我去幫你找雙厚底的鞋。”
陸珩自從打定主意在保定府多留幾天后,便差人給王言卿置辦了新服。他將特意訂做的保暖襖放到王言卿手中,走前看到王言卿緋紅的臉,心生促狹,故意問:“卿卿自己可以換服嗎,需要二哥幫忙麼?”
王言卿便是再遲鈍,也發覺陸珩是故意的了。抬頭,惱怒地瞪了陸珩一眼,一轉抱走了服:“我自己的事,不牢指揮使心。”
王言卿背過,都不再他二哥了,而是換指揮使。陸珩明知道王言卿在賭氣,可是邊的笑卻淡了淡。
雖然失去了記憶,但依然能看出原本格。為人世頗有些一板一眼,并不喜歡開玩笑。只是被人打趣都這樣氣惱,等將來得知他一直在騙,又會怎麼樣呢?
Advertisement
王言卿察覺陸珩很久沒走,不由回頭,用一種警惕又懷疑的目打量他。子都要換服了還不走,此等行徑無異于登徒子,陸珩立刻收斂起心緒,對王言卿笑了笑,很痛快地出去了。
王言卿關好門,拉住屏風,確定周圍沒人后才開始換服。一換上新襯就察覺出不對,這套襖特意改造過,靠近腹部的地方了細的絨,系上后腰腹仿佛綁了一個小暖爐,熱度源源不斷。而且后腰也修改了放量,摒棄一切觀、輕薄、顯瘦等功能,唯一的目的就是保暖。
王言卿換好服,屋外聽到走,敲門聲篤篤響起:“卿卿?”
王言卿快步走到門口開門,陸珩站在外面,目從上掃過,輕輕笑了:“果然我們卿卿長得,穿什麼都好看。”
陸珩后還跟著人,聽到陸珩的話,王言卿和對方都僵住了。府衙的人趕低頭,王言卿飛快掃了后方一眼,悄悄對陸珩使眼:“二哥,還有人呢。”
“這怕什麼。”陸珩走屋子,示意侍從將端盤放下,然后拉著王言卿坐好,“保定一時半會找不到鹿皮靴,只能找了雙兔的。你試試合不合腳。”
陸珩靠在榻邊,單手按在王言卿肩膀上,姿態自然隨意。王言卿心想他們兩人一起長大,以前這種事估計做多了,當面換鞋應當沒什麼大不了。王言卿也不再避諱,拿起一只兔皮靴,蹬進去試了試,發現剛好合腳。
陸珩站在旁邊,看到王言卿下鞋,出子只能給丈夫看的纖足。即便隔著羅,也能看出來的腳型纖細玲瓏,和的人一樣,是瘦長型的。穿鞋時腳部用力,繃出一截非常漂亮的小線條,從的小就能看出來,整條必然又細又長又直。
Advertisement
陸珩眼睛非常用,連心似乎都變好了。果然,他上朝時總覺得自己老得特別快,就是因為時常看那些丑臉。和卿卿出來兩天,他心態就年輕了不。
王言卿將兩只靴子穿好,靴子外面是淺灰兔皮,高度到的小中央,里面是細的兔絨,邊緣還綴著一圈蓬松的白兔。王言卿穿好,站起來轉了半圈,問:“二哥,怎麼樣?”
陸珩含笑點頭:“很好看。”
王言卿走了兩步,也覺得還不錯。陸珩給拿來披風,王言卿乖巧胳膊,套上披風。陸珩低頭給系領口的子母扣,王言卿盯著陸珩的臉,突然咦了一聲,問:“二哥,我是不是變高了?”
覺以前看陸珩,并不是這種角度。陸珩抬眸,含笑瞥了一眼,他拉了拉扣子周圍的料,慢悠悠直起:“現在呢?”
“哦。”王言卿默默應了一聲,“好像也沒有高很多。”
這雙靴子特意加厚了鞋底,王言卿穿上后高了一截,但和陸珩的高相比還是差很多。王言卿換上茸茸的服,就算天生態修長,被裹這樣后也有點圓潤了。王言卿了自己腰部的服,低低抱怨:“這樣看好胖啊。”
陸珩拿來暖爐,放到手中,不不慢掃了一眼:“胖什麼胖,好看重要還是暖和重要?”
陸珩一兇,王言卿也不敢說話了。陸珩讓抱好暖爐,一起往屋外走去。
一出門,寒風迎面灌來,王言卿都被風頂得踉蹌了一下。陸珩及時站到前面,擋住呼嘯的夜風,拉著往前走。王言卿著暖烘烘的熱量,發現二哥罵得對,暖和比好看重要多了。
有陸珩領頭,一路上本沒人盤問。路上陸珩大概給王言卿說了梁彬的份資料,王言卿一一記下,問:“二哥,我需要注意什麼嗎?”
“什麼都不需要注意,你和普通人不一樣,錦衛那些刑訊技巧對你而言本沒用。你按照自己的直覺審問就好了。”陸珩淡淡道,“保定府獄卒出現疏,已經被梁彬知道底線了。再怎麼壞都不會比現在更差了,我會陪你一起進去,你放手去做,不必擔心把案子搞砸。”
王言卿點頭,聽到陸珩也在,心里多安定下來。牢房的人看到陸珩帶了個人過來,臉上又驚又疑,陸珩靜靜掃了他們一眼,語氣不怒自威:“開門。”
獄卒行禮,趕開門。邁地牢后,溫度明顯冷起來,空氣中彌漫著一常年不見天日的味,不知道是還是水。王言卿不去想氣味的來源,亦步亦趨跟著陸珩,往關押梁彬的牢房走去。
保定府和京城不同,大牢里沒關多人,梁彬家又是錦衛又涉嫌命案,便是此刻保定府衙最重要的犯人了。他的牢房前圍著許多人,礙于陸指揮使沒待,這些人不敢輕舉妄。等聽到獄卒稟報陸大人來了,眾人趕迎過來,爭相行禮:“陸指揮使,刑已經準備好了,您看接下來要先上哪個?”
王言卿跟在陸珩背后,聽到這話牙痛了一下。早就知道錦衛橫行無忌,目無王法,最擅長嚴刑供,但聽到和真實見到,沖擊完全不同。
陸珩看起來倒很習慣,他剛才說錦衛的刑訊技巧不適合王言卿,并非隨口哄人開心,而是真的。錦衛的審問技巧總結起來就一個字——打,這樣做確實解決了十分之九的麻煩,但也有部分況,怎麼打都無法奏效。
王言卿,就是這剩下十分之一。
陸珩沒有發話,而是轉,靜靜看向王言卿。他的目從容幽深,充滿了無聲的信任,王言卿到鼓舞,說:“不能打。”
眾人一直心照不宣地忽略指揮使后的子,沒想到這個人不避讓,竟然還主說話。幾個錦衛百戶、校尉相互看了看,不甚樂意地看向王言卿:“為何?”
陸珩沒說話,但他站在王言卿邊,就是無形的底氣。王言卿沒有被這些人的眼神嚇退,說:“我自有安排。把刑都撤走,人也不要圍太多,我單獨去見梁彬。”
猜你喜歡
-
完結527 章

空間小農女:帶著全家去逃荒
壹場意外,該死的豆腐渣工程,全家穿越到古代。 家徒四壁,破破爛爛,窮到裝餓換吃的。葉秦秦歎息,還要她有個隨身商場,帶著老爹老娘壹起發家致富。 還沒開始致富,戰亂來襲,壹家人匆忙走上遷移之路。 當個軍戶種田,壹不小心將葉家名揚四海。 從此,高産黃豆的種植技術,神秘的東方料理……,成爲大夏朝子民瘋狂探究的謎題。 這家人了不得,個個知識淵博,拿出來的東西聞所未聞。 葉秦秦帶領全家走上致富之路,順便撿個小崽子。啊咧,到了後來小狼崽掉馬甲,原來……
95.8萬字8 58545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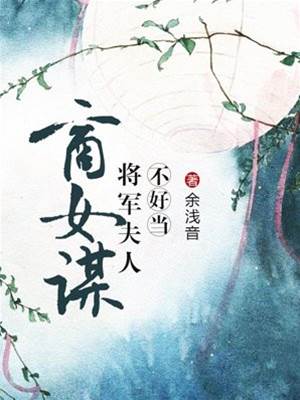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6634 -
完結121 章

短命白月光只想鹹魚
HE! HE! 日更,入V後日六。 既然有人強烈提了,那就避雷:血型文,女主攻分化後會有丁丁。 江軼長到十六歲,忽然覺醒自己是個穿書的,還是穿進了一本不可描述的小說里。 這本書的女主受,就是她便宜媽媽現女友的女兒——江似霰。 而她就是江似霰的短命白月光。 她要是被江似霰看上,按照劇情,妥妥早日歸西。 為了茍命,江軼決定:我! 要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拒絕早戀,成就輝煌! 我是絕對不會為了談戀愛搭上小命的! 珍愛生命,遠離江似霰從此成了江軼的人生教條。 但我們知道,人類的本質是真香,所以之後——江軼:我太傻了,真的。 早知道會有那麼一天,我絕對不會浪費那麼多時間在隱藏自己心意的事情上面。 我應該每一天都很認真的對你說「我愛你」 ,陪伴你渡過每一個難熬的發情期,永遠不會離開你。 ——大概是:行事囂張街頭小霸王x端莊典雅豪門繼承人。 江軼路子很野,會打爆別人狗頭的那種。 立意:有情人終成眷屬
36.2萬字8.18 4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