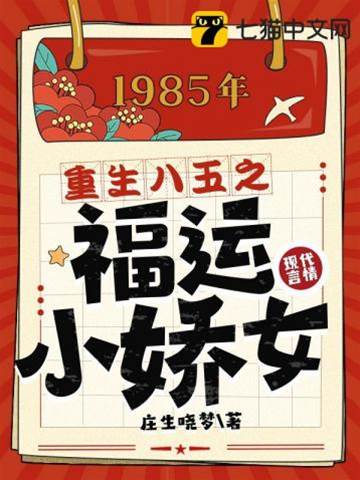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言歡》 第 16 章 第十六章
岑鳶沒太大的反應,只是點了點,說:“。”
就像,領證在眼只是件關要的事。
東西送到了,也就沒繼續留在這里的理由,推離開。
之,手扶著把,還是溫聲囑咐了句:“點煙,對不。”
去拿煙盒的手頓住。
開,又關上。
書房只剩下他個人,商滕眼睫輕垂,把手移開,垂放在桌面。
也不知在想什麼,那雙眼沒焦距。
整個人還是平靜的。
民政局八點才開。
岑鳶點事,要去趟布料行。
六點就起床了。
想著等忙完以再回來,可以趕上。
冬天路,就沒開車,而是到路口攔了輛的士。
冬日晝短夜長,這個點,天還是抹昏暗的藍。
路上沒多人,車輛也寥寥。
抵著車窗,盹。
昨天晚上睡的晚,今天又起的這麼早,算算時間,甚至都沒睡滿五個小時。
淺眠被驚醒,原因是面那輛車沒及時踩剎車,在等紅路燈的路口撞了上來。
即系著安全帶,可巨大的沖擊力還是讓岑鳶的往倒。
是疼痛把的思緒完全拉回來的。
手臂上出現了不算太長,卻也不短的傷口。
出量卻明顯比別人要多。
頓時慌了神,從包里拿出絹帕捂住傷口。
而此時,司機已經下車查看況了。
直在流,拉開車去,懇求司機能不能先送去醫院。
司機看到手臂上的傷口了,和追尾的保時捷車主說:“你看看你撞的多狠,的顧客都傷了,你說要怎麼賠吧!”
Advertisement
保時捷車主全程保持著他的禮儀和風度:“這車上了保險的,還是保持原樣等保險公司來吧。”
米杏的絹帕被染了紅,捂著傷口的手也變了紅。
也不知是冷的,還是怕的。
岑鳶的聲線輕微的抖:“能麻煩您先送去醫院嗎,這些賠償來。”
的士司機上下看了眼,似乎比起,保時捷車主看起來更錢點。
他毫不猶豫的拒絕了:“你這個傷口,不就是破了點皮嗎,沒必要這麼大驚小怪的。現在的小姑娘,真是氣。”
覺到周圍人異樣的眼神,岑鳶終于緩緩放下了手,沒再開口強求。
把這段路的車費付了,又往,想去攔車。
可是這個點人太了,路上本沒幾輛車。
拿出的手機,通訊錄上方,是商滕的名字。
想給他電話,猶豫了會,還是將手機鎖屏放。
寒風刺骨,刮在臉上,像是刀割般。
路邊的雪還來不及清掃,深腳,淺腳的踩上去。
紅的滴落,將那片潔白給染紅。
像是艷麗詭異的畫卷,岑鳶卻只覺得冷。
這種覺,不,這是在得了這個病以,第次傷流。
不知接下來會怎樣。
等待的,是什麼。
裹了圍巾,在心里安自己,不要怕,會沒事的。
幸,的士停在面。
從這兒去醫院,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不算遠。
這點長度的傷口,如果是別人,估計早就結痂了。
可直在流。
手捂著,便從指流出來,鮮滴在腳墊上。
空氣彌漫著腥甜黏膩的腥味。
Advertisement
那司機擔憂的問了句:“姑娘,你沒事吧?”
因為他從視鏡里注意到,本就白皙的臉,越發慘白,毫。
岑鳶手撐著副駕駛的椅背,虛弱的點:“沒事。”
的聲音仍舊是溫的,像四月的風,只可惜這風于微弱。
仿佛隨時都可能消失。
司機不由自主的將油踩重了點,開的更快。
到了醫院,岑鳶多給了他五百。
聲和他歉:“把您的車弄臟了,實在是抱歉,這五百是洗車費。”
司機原本是想拒絕的,可人已經遠了。
他看著纖瘦的背影,又低去看自己手里那幾張沾了淡淡跡的紙幣。
這大抵是,他見的最溫,最教養的孩子了吧。
可惜啊。
他看著視鏡倒車離開。
可惜,這麼的孩子,似乎沒被命運善待。
岑鳶已經不記得是怎麼進醫院的。
可能也沒進去。
因為暈倒了。
眼黑,徹底沒了意識,重重的摔在地上。
醒來的時候,護士在給換藥,些消炎的藥。
傷口已經做止了,不算嚴重。
暈倒是因為失多,再加上本就些虛弱。
護士邊給換藥,邊說著注意事項。
岑鳶從床上坐起來還些費力,因為提不起勁。
換藥,護士離開。
岑鳶看了眼窗外暗下去的天,突然想到了什麼。
拿起手機想給商滕電話,卻看到上面已經了三十幾通的未接來電。
全都來自同個人。
商滕。
猶豫的停下了作,最終還是解鎖屏幕,撥通回去。
Advertisement
只響了幾聲,那邊便接通了。
深的夜,他的聲音暗啞到如同生吞了把烈日灼燒的沙,連同聲帶也被燙傷。
給你了很多通電話。
在開口間,卻變了句,“為什麼不接電話?”
仍舊平靜的語氣,卻帶了些掩蓋不住的倦怠。
他善于管控自己的緒,論何時,都是副冷漠的臉。
但此刻,他可能是真的累了。
連偽裝都再沒力氣。
岑鳶開口想解釋。
是想告訴他的,在路上出了車禍,得了友癥,暈倒了,剛剛才醒。
所以才沒接到他的電話。
商滕卻在開口斷了:漠然的語氣:“就這樣吧,不勉強你。”
電話很快就掛斷。
岑鳶看著逐漸暗掉的手機屏幕,又將視線移向窗外的夜。
起風了,樹枝都被吹的撞。
是悉的天氣。
對陳默北印象最深的那天,像也是這個天氣。
岑鳶從小就不,次上課上到半,高燒暈倒,被送去醫務室,在里面輸。
隔著簾子,聽到外面的說話聲。
陳默北輕的聲線,帶了淡淡哭腔:“害怕。”
商滕語氣溫的安:“沒事,不會痛的,很快就了。”
岑鳶的藥水對胃刺激,醫生特地在床邊放了個垃圾桶,方便隨時吐。
岑鳶手撐著床沿,吐到沒力氣。胃空了,又開始難。
耳邊聽見,商滕問陳默北:“想吃什麼,去給你買。”
因為起去吐,以至于手背的針挪位,針了,那里迅速的鼓起了個小包,很疼。
護士進來給拔了重新扎。
簾子先開的那瞬間,岑鳶看到商滕微俯上,給蓋上薄毯。
Advertisement
他和紀丞不長的像,甚至連溫講話的聲音,也很像。
------------------
客廳沒開燈,窗外那點微弱的路燈線投進來,也起不到多照明的作用。
桌上的煙灰缸,零零散散的放著幾個熄滅的煙。
剛掛斷電話的手機被隨手扔放在桌上。
隔著寂夜,商滕西裝筆的坐在沙發上。
領帶是岑鳶給去年給他買的生日禮,袖扣是今年買的。
上的西裝,是他們結婚當天穿的。
他在家里拿著戶口本,不吃不喝等了整整天。
許是窗戶沒關嚴實,冷風吹進來。
商滕扯開領帶,出。
往樓上。
紀瀾的電話是在個小時來的,讓他回家趟。
他把服了,重新換了件。
視線落在那枚袖扣上,最終還是轉下樓。
紀瀾口的家,指的是在郊外的院落。
和商昀之分居多年。
也不是說鬧矛盾了,或是淡了。
他們的結合,本就是為了利益,與關。
雙方目的都達到了,自然也就沒再在起的必要。大風小說
雖然還在同個戶口本上,也是法律上的夫妻名義。
但也只是形同虛設。
紀瀾吃齋念佛這麼多年,早就對這種看淡了。
開垂落的竹簾,商滕進了里廳。
屋里燃著熏香,類似寺廟里的那種。
紀瀾穿著素旗袍,從樓上下來,看到他了,只輕聲句:“來啦。”
他間低嗯,未給太多的反應。
紀瀾也早就習慣,自己這個兒子的冷漠。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改變的呢。
也想不起來了。
不以,他也曾經是笑的。
至不像現在,什麼緒都自己藏著,旁人看不穿,也猜不。
深沉斂到,讓人覺得害怕。
但紀瀾卻不覺得這什麼不。
在這殺人不見的地方,為上位者的他,就該這樣殺伐果斷的狠勁。
沒肋,才沒弱點。
今天他來,是事要和他講。
流言傳的太快,紀瀾不能不管。
說:“那個孩子就放在這兒吧,來養。”
商滕神淡,聲音也淡:“不了。”
紀瀾嘆了口氣:“岑鳶那孩子再溫順,到底也是個人,那個孩子在你們之間,時間長了,總會變個疙瘩。”
“如果你今天找是為了說這件事。”
他站起,慢條斯理的把西裝第二顆紐扣系上,“那還事,就先了。”
紀瀾住他:“這麼久了,你還在耿耿于懷?”
離開的腳步頓住,但也只那瞬,商滕沒再給任何回應,開離開。
手里的佛珠攥在掌心,紀瀾看著窗外厚重的夜。
這麼多年了,不是沒悔。
可豪本就殘酷,優勝劣汰。
更何況,他們姓商。
也只能靠吃齋念佛,來緩解下自己心里的愧疚。
-----------
出院手續,是趙嫣然來幫辦的。
岑鳶思來想去,能告訴的,像只個人了。
趙嫣然拿著檢查結果的那刻,手抖的厲害,反復的去眼睛,可能是自己看錯了,或者是出現幻覺了也不定。
可論怎麼,眼睛都紅了,那幾個字都沒任何改變。
友癥。
當然知是什麼病。
岑鳶的臉仿佛大病初愈般,仍舊是憔悴的。
輕笑著安趙嫣然的緒:“醫生說這個是輕癥,沒什麼大問題的,只要盡量不要自己傷流,和常人就沒太大的區別。”
趙嫣然抱著,直在哭:“怎麼可能沒問題!”
因為得知生病,連抱時的力氣都變小了許多,生怕不小心就弄傷了。
這個反應,讓岑鳶奈輕笑。
真把當個瓷娃娃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不敢告訴他們的原因。
從醫院離開,趙嫣然開車送回去。
路上突然問起:“商滕知了嗎?”
岑鳶陷沉默,上蓋著薄毯,把視線移向車窗外。
“他還不知。”
就在剛才,是算告訴他的。
可是他沒給說出口的機會。
今天這件事,的確是的錯。
猜你喜歡
-
完結1161 章
他養的小可愛太甜了
他是商界數一數二的大人物,眾人皆怕他,隻有少數人知道,沈大佬他……怕老婆! 沈大佬二十八歲以前,對女人嗤之以鼻,認為她們不過是無能,麻煩又虛偽的低等生物。 哪想一朝失策,他被低等生物鑽了空子,心被拐走了。 後來的一次晚宴上,助理遞來不小心摁下擴音的電話,裡麵傳來小女人奶兇的聲音,「壞蛋,你再不早點回家陪我,我就不要你了!」 沈大佬變了臉色,立即起身往外走,並且憤怒的威脅:「林南薰,再敢說不要我試試,真以為我捨不得收拾你?」 一個小時之後,家中臥室,小女人嘟囔著將另外一隻腳也塞進他的懷裡。 「這隻腳也酸。」 沈大佬麵不改色的接過她的腳丫子,一邊伸手揉著,一邊冷哼的問她。 「還敢說不要我?」 她笑了笑,然後乖乖的應了一聲:「敢。」 沈大佬:「……」 多年後,終於有人大著膽子問沈大佬,沈太太如此嬌軟,到底怕她什麼? 「怕她流淚,怕她受傷,更……怕她真不要我了。」正在給孩子換尿布的沈大佬語重心長的
105.2萬字8 127617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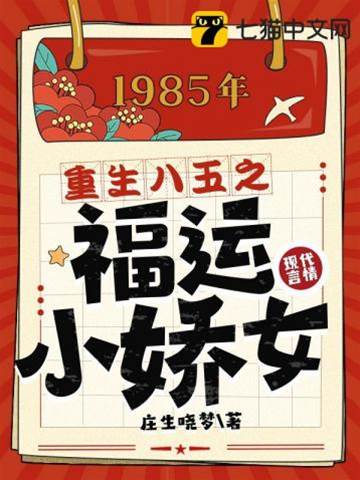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21891 -
連載552 章

妻女死祭,渣總在陪白月光孩子慶生
【重生+雙潔+偽禁忌+追妻火葬場】和名義上的小叔宮沉一夜荒唐后,林知意承受了八年的折磨。當她抱著女兒的骨灰自殺時,宮沉卻在為白月光的兒子舉辦盛大的生日宴會。再次睜眼,重活一世的她,決心讓宮沉付出代價!前世,她鄭重解釋,宮沉說她下藥爬床居心叵測,這一世,她就當眾和他劃清界限!前世,白月光剽竊她作品,宮沉說她嫉妒成性,這一世,她就腳踩白月光站上領獎臺!前世,她被誣陷針對,宮沉偏心袒護白月光,這一世,她就狂扇白月光的臉!宮沉總以為林知意會一如既往的深愛他。可當林知意頭也不回離開時,他卻徹底慌了。不可一世的宮沉紅著眼拉住她:“知意,別不要我,帶我一起走好嗎?”
101萬字8.33 184598 -
完結179 章

灼灼浪漫
大雨滂沱的夜晚,奚漫無助地蹲在奚家門口。 一把雨傘遮在她頭頂,沈溫清雋斯文,極盡溫柔地衝她伸出手:“漫漫不哭,三哥來接你回家。” 從此她被沈溫養在身邊,寵若珍寶。所有人都覺得,他們倆感情穩定,遲早結婚。 有次奚漫陪沈溫參加好友的婚禮,宴席上,朋友調侃:“沈溫,你和奚漫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沈溫喝着酒,漫不經心:“別胡說,我把漫漫當妹妹。” 奚漫扯出一抹得體的笑:“大家別誤會,我和三哥是兄妹情。” 她知道,沈溫的前女友要從國外回來了,他們很快會結婚。 宴席沒結束,奚漫中途離開。她默默收拾行李,搬離沈家。 晚上沈溫回家,看着空空蕩蕩的屋子裏再無半點奚漫的痕跡,他的心突然跟着空了。 —— 奚漫搬進了沈溫的死對頭簡灼白家。 簡家門口,她看向眼前桀驁冷痞的男人:“你說過,只要我搬進來,你就幫他做成那筆生意。” 簡灼白舌尖抵了下後槽牙,臉上情緒不明:“就這麼在意他,什麼都願意爲他做?” 奚漫不說話。 沈溫養她七年,這是她爲他做的最後一件事,從此恩怨兩清,互不相欠。 那時的奚漫根本想不到,她會因爲和簡灼白的這場約定,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丟在這裏。 —— 兄弟們連着好幾天沒見過簡灼白了,一起去他家裏找他。 客廳沙發上,簡灼白罕見地抵着位美人,他被嫉妒染紅了眼:“沈溫這樣抱過你沒有?” 奚漫輕輕搖頭。 “親過你沒有?” “沒有。”奚漫黏人地勾住他的脖子,“怎麼親,你教教我?” 衆兄弟:“!!!” 這不是沈溫家裏丟了的那隻小白兔嗎?外面沈溫找她都找瘋了,怎麼被灼哥藏在這兒??? ——後來奚漫才知道,她被沈溫從奚家門口接走的那個晚上,簡灼白也去了。 說起那晚,男人自嘲地笑,漆黑瞳底浸滿失意。 他凝神看着窗外的雨,聲音輕得幾乎要聽不見:“可惜,晚了一步。”
30.6萬字8.18 200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