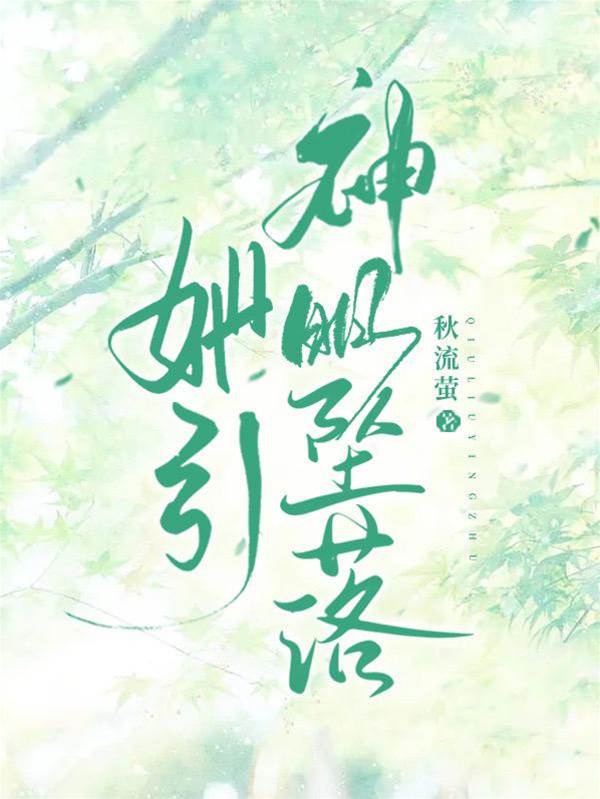《野性關係》 第14章 我不想讓你跟別人結婚
蘇蕎被燙出嚶嚀聲,開口的話都破破碎碎,“不……要在……這……”
後的男人作非但沒停,反倒更放肆了一些,他角噙著笑,聲音繾綣,“要還是不要?蕎蕎,你說清楚。”
蘇蕎知道傅言修心裏有氣。
剛才他明明是想給自己機會,反抗嚴敏,可卻選擇駁了他的麵子。
傅言修是誰?
傅家的家主,就算是傅家編外的人,也不能違抗他。
蘇蕎沒回答他的話,咬住,不想說,也說不出來。
可還是低估了傅言修的怒火。
深秋時節,蘇蕎就穿了一件薄衫,搭了一個羊絨披肩,可上的汗一層層,熱浪一浪高過一浪。
再後來,都咬破了,還是難掩稀碎的嚶嚀。
不遠傳來說笑聲和腳步聲,蘇蕎的子一僵,這塊地方沒遮沒掩,聲音本藏不住,後一抓傅言修的手。
討好地拉他的袖。
傅言修自然知道的顧忌,輕哼一聲,慢了下來。
等外邊的傭人走遠,聽不到聲音了,傅言修才掐蘇蕎的腰,匆匆結束。
男人,蘇蕎上一,整個人著石壁緩緩下落,在快要跌坐下去的時候,一雙大手將人撈進懷裏。
一手攬著的腰,一手幫整理,“怕?”
蘇蕎已經咬的麻木,但還是倔強地死死咬住,抬起一汪剪水的明眸,漉漉又反叛的瞪著他。
Advertisement
“怕就聽話一點。”傅言修抬手將的披肩搭好,敞開自己的大,將人裹住。
鼻尖抵著鼻尖,“我護著你,說好的。”
又傳來了腳步聲,蘇蕎本能地往傅言修的懷裏一鑽。
“媽,你怎麽給介紹孔又青?”是傅婷。
“嘖,死丫頭,你別說,你還惦記那個孔又青,那可不是好東西。”嚴敏責怪道。
“哼,誰不是好東西?”傅婷不服氣,“明明是蘇蕎賤。”
嚴敏瞪一眼,“什麽意思?”
傅婷將剛才打電話聽到的事說了一遍,因為好麵子,將孔又青無視自己的那段去。
“蘇蕎就是故意衝我炫耀,以為自己找了棵大樹。”傅婷越說越來勁,“我還聽孔又青說要給拉客人。”
嚴敏一愣,隨即笑了,“還有這種事?”
“啊,你說客人能是什麽客人?”傅婷說,“還說,保證讓對方滿意,惡心死了。”
蘇蕎將兩人的話聽到耳朵裏,心裏泛冷,沒想到兩人在背後說話,還真是一點顧忌都沒有。
這還是在傅家呢,要是在私底下,還不知道說什麽。
正在失神的空檔,男人的尋過來,直接咬了上去,的被就破了,被傅言修的牙齒一磕,痛直往心尖上鑽。
外邊的嚴敏點點頭,嚴肅地說:“行了,這個事你別摻和,想怎麽作是的事,反正——”
Advertisement
“嗯!”一聲人曖昧抑的哼聲,從假山後冒出來,打斷了母倆的對話。
傅婷嚇了一跳,嚴敏還算是鎮定,衝傅婷使了一個眼,然後走到假山那邊,往裏看,冷聲喝道:“什麽人,真是不統。”
說話間,傅婷已經打開手機的手電筒照過去,一個男人高大的影,懷裏影影綽綽的好像裹著一個人。
“在這裏行茍且,當傅家是——二哥?”傅婷看到男人回過頭來,在看清臉的時候,驚出聲,聲音都變了調。
傅言修的眸很冷,鷹隼一般,將傅婷和嚴敏盯了個心。
嚴敏最先反應過來,拍開傅婷的手,後者後知後覺,慌慌張張地將手機關掉。
四周再次暗下來,幾個人隻能模模糊糊看到彼此的存在,卻連表都看不到。
嚴敏笑嗬嗬地說:“言修,這是做什麽呀?在自己家呢。”
還用得著?
傅言修聲線很淡,“這是我的家,我想怎麽樣,還不至於對一個外人代。”
嚴敏一噎,已經跟傅三叔離婚這麽多年了,的的確確是個外人。
但知道是一回事,被人點到臉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天黑看不清,傅婷的慫人膽也壯了不,嘟嘟囔囔,“二哥,你真是的,都有趙三小姐了,還在這胡搞什麽?算怎麽回事啊?我要去告訴爺爺。”
Advertisement
一聽到傅婷要去告發,蘇蕎渾一僵,手指都蜷起來,揪著傅言修的襯不放。
男人到的張,抬手輕的背。
“你告一個試試。”傅言修的語氣不輕不重,可傅婷的後背瞬間起了一層冷汗。
張張想橫兩句,但還是訕訕地閉了。
要是敢試試,傅言修就能讓逝世。
“行了,你在這瞎說什麽。”嚴敏故意訓傅婷,無非就是給傅言修聽的,轉臉又好聲好氣地說,“是我們來的不是時候,言修,你繼續。”
說完,嚴敏拉著傅婷一溜煙跑了。
等人走遠了,蘇蕎的子都緩緩放鬆下來。
推開傅言修,男人卻不放手,低頭湊到耳邊說:“過河拆橋?”
蘇蕎真想啐他一口。
什麽過河拆橋,要不是他胡來,用得著這麽狼狽嗎?
“二哥難道不怕?”蘇蕎倔強地抬起頭,迎上傅言修的目,“你我就算沒有緣關係,但這關係也永遠見不了。”
就像今天這樣,傅言修雖然能護住,但永遠都是那隻裏的老鼠,不得見天日,永遠。
但能在傅言修的懷裏窩多久呢?
傅婷雖然毒,但說得對,傅言修,已經有趙思妍了。
“你想見?”傅言修問。
誰不想呢?
蘇蕎的心也是做的,說不在乎,不痛苦都是假的。
Advertisement
沉了一口氣,“二哥要跟趙家聯姻,我能見?還是說,你想讓我當小三?”
“你什麽時候這麽會給自己加戲了?”男人嗤笑一聲。
這一聲直接紮在蘇蕎的心尖上,覺一隻手直接掐住的嚨,聲音都發,“你們倆現在出雙對,早晚會結婚,那我不是小三是什麽?”
傅言修蹙眉,“關趙思妍什麽事?有沒,你還是你。”
對,反正從一開始,就是傅言修的附屬品,玩,一個合同而已。
有沒有趙思妍,本不會改變蘇蕎的地位,就是這麽不重要。
蘇蕎的眼眶一熱,心裏那種不甘,付出了這麽多年的喜歡,讓明知道答案,可還是問了一句。
“我要是不想讓你跟別人結婚呢?”
猜你喜歡
-
完結3328 章

先婚後愛:BOSS輕點寵
她以為離婚成功,收拾包袱瀟灑拜拜,誰知轉眼他就來敲門。第一次,他一臉淡定:“老婆,寶寶餓了!”第二次,他死皮賴臉:“老婆,我也餓了!”第三次,他直接撲倒:“老婆,好冷,來動一動!”前夫的奪情索愛,她無力反抗,步步驚情。“我們已經離婚了!”她終於忍無可忍。他決然的把小包子塞過來:“喏,一個不夠,再添兩個拖油瓶!”
591.3萬字8.46 320183 -
完結3045 章

天價萌妻:厲少的33日戀人
他是歐洲金融市場龍頭厲家三少爺厲爵風,而她隻是一個落魄千金,跑跑新聞的小狗仔顧小艾。他們本不該有交集,所以她包袱款款走得瀟灑。惡魔總裁大怒,“女人,想逃?先把我的心留下!”這是一場征服與反征服的遊戲,誰先動情誰輸,她輸不起,唯一能守住的隻有自己的心。
236.6萬字8 22983 -
連載1815 章

枕上歡:老公請輕點
唐慕橙在結婚前夜迎來了破產、劈腿的大“驚喜”。正走投無路時,男人從天而降,她成了他的契約妻。唐慕橙以為這不過是一場無聊遊戲,卻冇想到,婚後男人每天變著花樣的攻占著她的心,讓她沉淪在他的溫柔中無法自拔……
318.3萬字8 35116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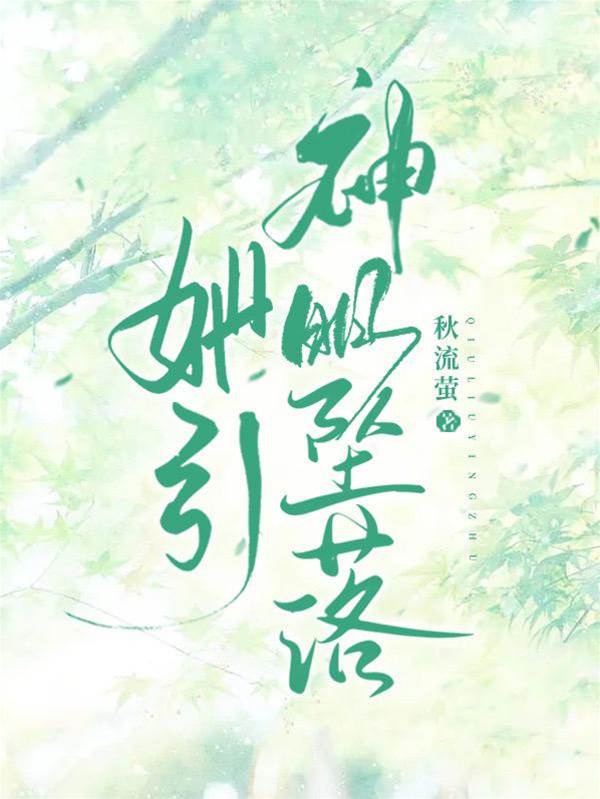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176 -
完結191 章

你有男閨蜜,就不要纏著我了
結婚前夕。女友:“我閨蜜結婚時住的酒店多高檔,吃的婚宴多貴,你再看看你,因為七八萬跟我討價還價,你還是個男人嗎?!”“雖然是你出的錢,但婚房是我們倆的,我爸媽可
33.3萬字8.18 26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