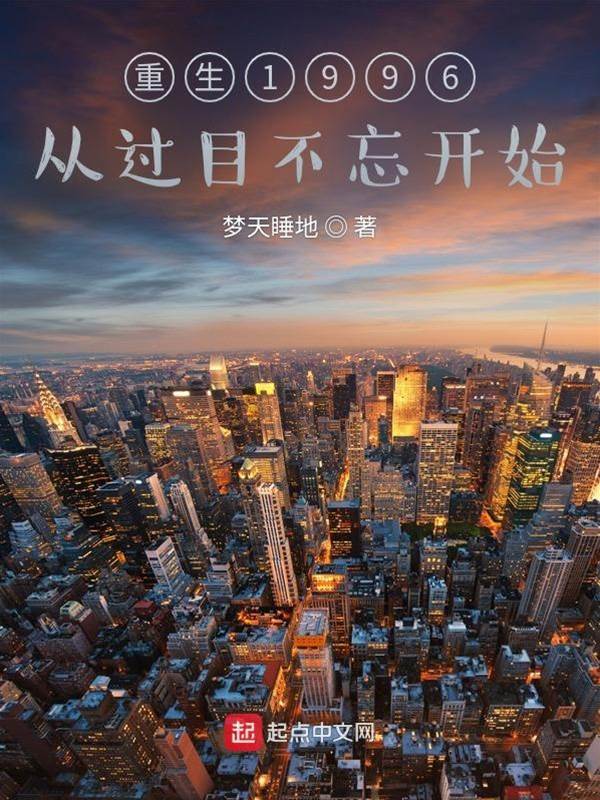《重活不是重生》 第一千一百七十八章 刮痧療法(上)
位於滇中轄區的哀牢山區紅河峽穀,依然保持有最完整的原始森林自然生態群落,每到秋冬季節,山穀間經常雲霧繚繞,日出時候的線普照在雲海上金黃飽滿,是專業攝影師的最。
嘎灑江水每到雨季就被染紅,因此,這裏也紅河,從高俯瞰第一灣壯觀大氣,宛如紅龍回首。哀牢山下的嘎灑小鎮幹淨整潔,風味食嚐不完,各種風人文題材富。那些不起眼的景,路邊的小溪,織布的、田間勞作的花腰傣,民族風濃鬱。
自從離開南煙集團公司之後,有多時間沒來縣份上走一走,看一看了?好不容易才來一趟紅河峽穀,祁景燾也不需要大忙人杜河師傅和蔣筱薔陪同,自己駕駛汽車,帶著陳雪菲在哀牢山區四溜達看風景。
陳雪菲難得和祁景燾單獨出來一次,心裏滋滋的,似乎……哀牢山區的紅河峽穀還是他們倆的定福地。也不顧懷六甲之,興致地陪同自家老公漫遊在麗迷人的哀牢山區,還饒有興致的一路看一路不停地拍照,似乎要將整個紅河峽穀的景都拍下來帶走似得。
道路修通了,一百八十多公裏的紅河峽穀似乎也不是那麽閉塞和漫長,祁景燾對於這片低熱峽穀的著名景點、村寨分布也是非常悉,總能夠找到最佳的景點和風景。
一路走,一路看,下午時分,他們來到一個做東鵝的集鎮歇腳。
東鵝已經是元縣轄區的集鎮,這裏盛產甘蔗和酸角,製糖業非常發達,餐飲也是非常有地方特,祁景燾下鄉那些日子來品嚐過好多次,自然要帶陳雪菲過來驗一番地方特食的滋味。
祁景燾輕車路地駕駛汽車來到一家悉的飯店門口,剛剛下車,就看到不遠有一些人圍在路邊,遠遠的便聽到人群裏傳來的議論聲:“唉,這老爺子也真可憐,這一暈,指不定還醒不醒得來哦。”
Advertisement
“是啊,是啊,這老爺子剛剛還好好的,怎麽說暈就暈了呢?”
“這家人也真是的,知道自家老人有病,怎麽還讓他出來,大太的,連我們常上山的人也不了,這下可好,唉……”
祁景燾好歹是滇中小神醫,聽說有人病倒,作為醫者本能,也不忙著去吃飯了,扶著已經顯懷的陳雪菲朝人群走去。
他早已經“看見”人群最裏麵,一個老人正躺在一棵大酸角樹下的泥土地上,臉通紅通紅得跟火燒了似的,眼瞼沉沉地閉著,花白眉皺一團,看著很痛苦很難的樣子。
老人原本著心口的手也有點鬆了,手指微微有些。他的邊,跪坐著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男人,滿臉焦急地搖晃著老人的喊著,“阿爸,阿爸,你堅持住啊,等會救護車就來了。”說話間,額頭上豆大的汗珠啪啦啪啦地往下掉,他現在是又氣又急,都變得六神無主了。
祁景燾安頓好陳雪菲,進圍觀人群的時候,一個年輕子已經跑到了老人邊蹲下,“這位大叔,我是醫生,能讓我幫你家老人看看嗎?”
那個年輕子也不等中年男人回答,出手指在老人頸間一搭。還好,還好,搏雖然又快又輕細,但總還在跳,問題是有些嚴重,但還有得救。再用手背敷到額頭上試了試溫度,年輕子微微愣了一下,臉紅這樣,看他像是在發燒,怎麽會沒有出汗呢?
“你幹什麽?”中年男人這才覺到邊多了個人,一臉張地問道。
年輕子沒來得及搭理他,拇指在病人的人中上用力按下,頭也不回地吩咐道:“我是附近白家醫館的白莫茵,你大家都散開,老人家很有可能是中暑了,這麽多人圍著連空氣都不流通了,病人就更好不了啦。”
Advertisement
“麻煩大家散開些,請大家快散開些!”中年男人就跟抓到一救命稻草似的,想也沒想衝圍觀的人群喊道。
圍觀的人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大家倒是依言散開了許多,但又都沒離開,後退分散一些距離,又站在不遠好奇地打量著中間那個老人的況。
祁景燾和陳雪菲也沒離開,那個主上前急救的白莫茵,他們兩個都認識,還是滇中千植堂培養出來的中醫師。白莫茵是彩雲中醫藥學院畢業生,也是東鵝本地人,流前來杜河主持的萬畝冰糖橙莊園當駐地醫生的中醫師之一。
說起來,白莫茵也算是祁景燾的親傳弟子,養生功六層修為,的現場診斷沒錯,應該有對應的急救手段,祁景燾也就沒必要上前幫忙,就這麽陪在陳雪菲邊看熱鬧。
“誰去阿嘎老板飯店裏拿碗淡鹽水來,要快。”
白莫茵在滇中千植堂工作學習過一年多時間,常規急癥還是非常拿得出手嘀,而且還屬於帶藝投師,以前也學習過一些中醫傳統急救方法。雖然還不太確定老人病的嚴重程度,但這個時候況急,既然遇上了,也隻能采取自己最悉的急救手段進行急救,“再要一碗清水,一把勺子,最好是瓷的,快點。”
“哦,哦。”中年男人答應著,連爬帶跑地去找醫生需要的這些東西,這是急救,耽擱不起時間。
不遠那家飯店老板顯然看見這邊發生的況,不等中年男子跑進門,聽到白莫茵吩咐聲音的阿嘎老板已經從櫥櫃裏取了兩隻碗和一把陶瓷勺子,再拎上幾瓶瓶裝水和一袋鹽跑了過來。
一個圍觀的年輕人趕接過阿嘎老板送來的東西,把一小撮鹽放在碗裏,倒上瓶裝水快速地用勺子攪拌均勻,遞了過去,“鹽水。”
Advertisement
白莫茵也不多說什麽,一手端著碗,一手握住老人的下顎,用力地往上一提又使勁地往下掰,趁著出一條的瞬間趕把鹽水灌了進去,灌了一大口,見水了出來,趕把碗往地上一擱,兩手用力地把下往上抬住,讓裏的鹽水倒灌進了嚨。
看到嚨部位明顯的吞咽了一下,白莫茵這才稍稍鬆了口氣,回頭又對中年人說道:“你幫我扶他坐起來。”
中年男人趕依言扶住老人,白莫茵吸了口氣,四指並攏,兩拇指分別擱在鎖骨窩的邊緣,四指在肩後,兩手一起用力,將中間裏一筋迅速而用力地向上提起,聽到悶悶的一聲輕響,再鬆開手,調整了一下繼續重複,提了五六下才放開了,手探到腋下,肘窩,虎口,一套行雲流水般的急救手法完之後才鬆開了。
“景燾,這位老大爹的病癥明顯是重度中暑,現在最正確的急救方法應該采用銀針刺療法治療啊,小白這是做什麽?你需不需要去給幫幫忙?”陳雪菲看著白莫茵的急救作,有些不解地問神自若站在一旁看熱鬧的祁景燾。陳雪菲也是天資聰慧之輩,邊人就是神醫,耳濡目染之下,對中醫急救常識也了解一些。
“民間理中暑的手法多種多樣,會針灸的人不是太多,看小白的樣子是沒帶針灸工,估計是準備采用刮痧療法,應該有好辦法,我們先看看,不行再說。”祁景燾不想幹擾白莫茵的急救過程,看采取的急救方法也正確,就輕聲對陳雪菲解釋道。
白莫茵回頭看向趕過來幫忙那位飯店老板,“阿嘎老板,能把這位老大爺抬去你飯店裏嗎,這兒有風,刮痧要出整個後背的,被風吹了不大好。”
Advertisement
“小白醫生,這就見外了,快抬過去吧!”山裏人質樸,還都是人,阿嘎老板也是熱心人,毫不顧忌病人進家飯店會不會有什麽不吉利,會不會有什麽不良後果,馬上就答應下來。
也不需要外人幫忙,白莫茵和那個中年人男人一人一頭,抬了老人就去飯店裏麵一間沒客人的隔間,將老人放在旁邊跟來幫忙的人用兩張四方桌擺的臨時床鋪上,阿嘎老板也遞來兩個靠墊當枕頭用。
有這麽多人出麵幫忙,中年男人這會兒也鎮定了不,按照白莫茵的指揮,快速地替老人褪去了上,扶著老人以坐姿坐好。
白莫茵則站在老人旁邊,將阿嘎老板拿過來的裝著清水的碗放在桌子上,一手拿了蘸水的陶瓷勺子從老人頸部沿著脊椎一點一點往下刮,隻一下,椎骨就出幾顆紫黑的斑點。
看來真的是中暑,還是重度的。確定了自己的判斷方向都沒有錯,白莫茵下手就更快更利落了,待勺子上的水幹了,就再沾一點繼續刮,在整脊柱位置上上下下、來來回--回地刮,直到刮出一整條紫得發黑的瘀斑,才換地方另刮,沿著肩胛骨中間的位置筆直地往下刮。
不一會兒,三條紫黑柱在老人削瘦的後背上凸顯著,看得中年男人和跟來看熱鬧的人眼皮一跳一跳的。
“白醫生……,這就是發痧啊?”中年男人還是有些見識的,這時候也恢複了一些,有思維了。
“對,這位老大爺就是起痧,起的還是泥鰍痧,現在出了就好。”白莫茵隨口答了一句,又在兩邊腰際刮了起來。刮痧最要的就是把的暑氣都散幹淨,要是還悶了一部分在裏頭,難保下回會不會又發出來。
跟過來看熱鬧的祁景燾和陳雪菲看著白莫茵的作,聽著“沙沙”的聲響,覺得時間特別難捱。用這種方治療重度中暑能行麽?陳雪菲幾次打算讓邊的大神醫出手幫忙,都被祁景燾拒絕了。
祁景燾對民間流傳的刮痧療法了解的還算比較全麵,這次看到白莫茵用刮痧治療中暑患者,觀察的特別仔細,邊看還給邊的陳雪菲介紹起刮痧療法的常識來了。
刮痧療法是中醫常用的一種簡易治療方法,流傳時間甚久。在我國民間多用於治療夏秋季時病,如中暑、外、腸胃道疾病等等。
有學者認為刮痧是從中醫推拿手法變化而來。據《保赤推拿法》載:“刮者,醫指挨兒皮,略加力而下也。”
元、明時期,有較多的有關刮痧療法記載,並稱之為“夏法”。及至清代,有關刮痧的描述更為詳細。郭誌邃《痧脹玉衡》曰:“刮痧法,背脊頸骨上下,又前脅肋兩背肩臂痧,用銅錢蘸香油刮之。”
吳尚先《理瀹駢文》載有如“痧腹痛,莫妙以瓷調羹蘸香油刮背,蓋五髒之係,鹹在於背,刮之則邪氣隨降,病自鬆解。”《串雅外編》、《七十二種痧證救治法》等醫籍中也有記載。
由於刮痧療法無需藥,見效也快,手法得當的話,治療效果稱得上是立竿見影。最關鍵的是刮痧的基本手法也簡單易學,在我國民間被廣泛應用,在我國南方地區更是廣為流行,許多老年人都能弄上兩手,隻不過各人的道行不同而已。
如同刮痧療法一樣,刮痧的用也十分簡單、方便。一般況下,隻要是邊緣比較圓的東西,如梳子、溏瓷杯蓋子、幣,圓形紐扣等,都可以用來刮痧。
猜你喜歡
-
完結1221 章

農女福妻有點嬌
孤兒姜荷重生了,有爹有娘,還附贈了小姐姐和嗷嗷待哺的弟弟。寶葫蘆在手,發家致富就是小意思,有田有錢還有家人,這日子美的不要不要的。她的田園生活,就少了個相公。某男幽幽的說:我不就是你相公?
206.3萬字8 203710 -
完結174 章

重生之嫡女不乖
前世,她太過懦弱、太過信任他人,被心上人和至親連手推入最難堪的境地,卻原來,所有的脈脈柔情和溫暖關懷,都不過是爲了她不菲的財産和那個不欲人知的秘密。 狠毒的舅母,將她生生毒死。 自黑暗之中醒來,她竟重生到了四年前, 那時,父母剛剛雙亡,她剛剛踏入伯爵府, 再一次,她站在了命運的轉折點前。 帶著濃濃恨意重生的她,化身爲一半佳人一半魔鬼的罌粟花,誓要向那些恣意踐踏她尊嚴的人,索回一切……
87.9萬字8 6609 -
完結7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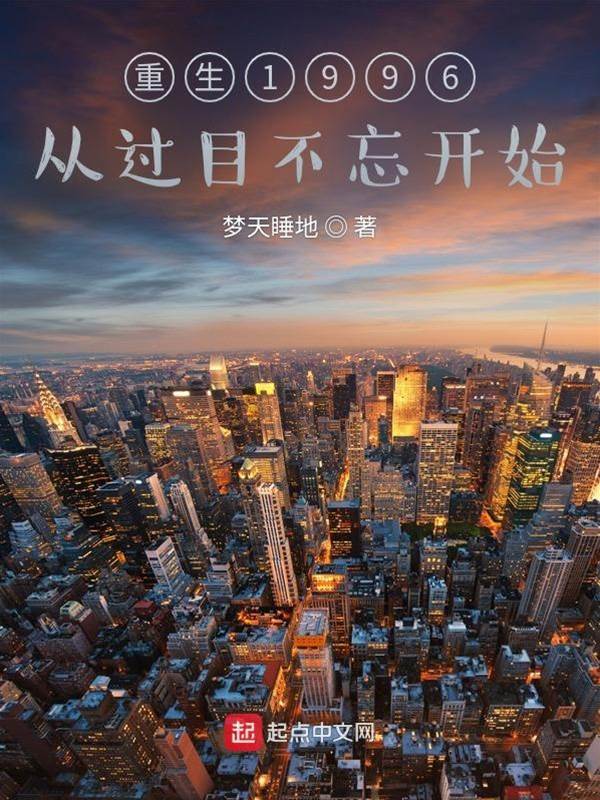
重生1996從過目不忘開始
一場車禍讓人到中年依舊一無所成的張瀟回到了1996年,回到了那個即將中考的日子。重活一生的張瀟不想再窩囊的活一輩子,開始努力奮斗,來彌補前世留下的無盡遺憾。
155.3萬字8 628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