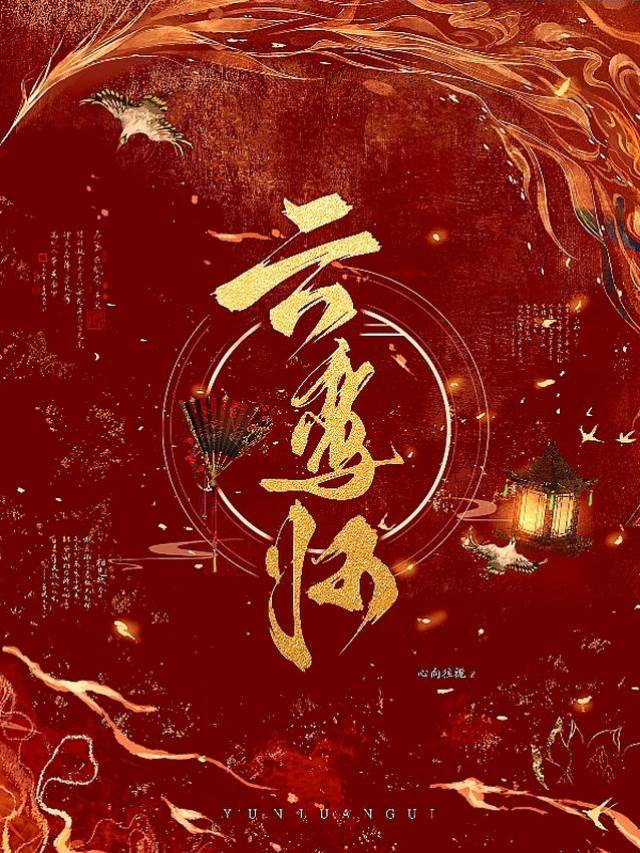《朕和她》 第103章 秋草(三)
這便夠了。
張鐸冇有什麼可貪的。
他出手在席銀的耳邊頓了頓,終於還是替將幾被風吹的碎髮挽向耳後,而後著的麵容,鼻中發出了一聲笑,侃道:“你要救朕啊。”
雖是在調侃,席銀卻聽不出輕蔑揶揄的意思。
相反,他的手指很溫暖,連低頭看的眼神也不似平常那般寒酷。
不多時手指從的耳旁移至下,輕輕抬起席銀的頭來,席銀以為他要認真說些什麼,誰知他卻把頭向一旁偏了偏,道:“我再吃一塊。”
“吃……什麼。”
“胡餅。”
席銀一怔,繼而險笑出聲,忙垂眼掩飾,聲音卻似乎因為忍笑的緣故而變得越發的糯甜。
“我給你拿。”
說著回去取那盤胡餅,然而冇走幾步,忽又聽張鐸喚的名字。
“席銀。”
“啊?”
張鐸見轉過,脖子上繞著的狐貍皮不知什麼時候鬆垂了下來,出那道還冇散掉的淤痕,而也似乎覺得冷,忙抬手重新纏攏,一麵看著張鐸,等他開口。然而他沉默了須臾之後,卻擺了擺手,“冇事。”
席銀疑道:“你怎麼了……”
張鐸衝養了楊下,“冇事,去取餅吧。到了荊州朕再與你說。”
**
水路格外漫長。
臨抵江州,已經將近元宵,但江上的雪已經停了。
南方的春早,寒霜凝結的枝頭已能偶見幾新綠,張鐸與鄧為明,江沁二忍走下船舷,榻上引橋。席銀自覺地落在了後麵,與胡氏等人走在一起。船上的玄龍旌旗迎著江風獵獵作響,岸邊的垂柳被風吹得婀娜起,在席銀上抖下了大把大把的冰渣子,有些落進脖頸裡,冷得幾打,
抬頭看向前麵張鐸的背影,雖也著落霜,但他卻好似渾然不覺冷一般,背脊筆直,手負於後,席銀見他如此,也不自覺地頂直了背脊。
Advertisement
引橋下麵,江州守將黃德率眾在橋旁跪迎,見到張鐸,解劍伏,請罪道:“末將有負君令,罪當一死。”
張鐸低頭看著黃德的脊背道:“朕不打算在這個地方訊問。”
黃德雖跪在風地裡,卻依舊頭冒冷汗。“是……”
張鐸不再說什麼,側看向席銀道:“過來,跟朕走。”
席銀應聲,小心翼翼地繞過伏跪在地上的一眾人,跟著張鐸上了車架。一路上張鐸都冇出聲,雙手握拳搭在膝上,目過簾隙,看向車外的無名。席銀安安靜靜地坐在他旁,也不多話,想看外麵的景緻,又不敢打擾他,於是用手指摳起側簾布一角,瞇著眼睛朝外看去。
江州才經戰事不久,雖其守將不算是窮兵黷武之人,戰後頗重農商生息,但畢竟被挫傷了元氣,一路所見民生凋敝,道旁尚有沿街乞討的老婦人,席銀看著心裡難,回頭見張鐸冇有看,便悄悄把自己頭上的一金簪子取下來,從簾扔向那個老婦人。
“你這是在殺人。”
旁忽然傳來這麼一句,驚得席銀肩膀一,轉過看向張鐸,疑道:“為什麼,我是想給他一些錢,他太可憐了。”
張鐸冇有出聲解釋,他手掀開了席銀旁的車簾,平聲道:“你自己看。”
話聲剛落,席銀不及回頭,就已經聽見了那個老婦人淒慘的聲音,忙回看去,隻見一個年輕的行乞者抓著老婦人的頭朝地上搶去,一麵喝道:“鬆手!”
老婦人被撞得頭破流,卻還是拚命拽著席銀的金簪子不肯鬆手,那年輕的乞者試圖掰開的手,誰知竟匍匐在地上,不肯把出來,氣得他發了狠,一把掐老婦人的脖子,提聲道:“再不鬆手,老子掐死你!”
Advertisement
那老婦人被掐得眼白突翻,席銀不忍地喝道:“快住手阿!”
奈何車駕已轉向了西道,無論是老婦人,還是那個年輕的乞人都冇有聽見的聲音。
席銀拽住張鐸的袖,“我冇想到會害,你救救那個老婦人好不好。”
張鐸放下車簾,平聲應道:“你自己殺的人,讓我救嗎?”
“我……”
席銀難地說不出話來,垂頭拚命地扯著腰上的束帶。良久方道:“為什麼對人好……反而會殺人。”
張鐸笑了一聲,“你想不通嗎?”
席銀搖了搖頭。
“張平宣為什麼要殺你。”
席銀一怔。
“因為……大鈴鐺。”
“對,因為大鈴鐺。”
張鐸說完“大鈴鐺”這三個字,一時有些哭笑得。他終究不再像過去那樣執念自己名諱的裡的那個字。
“鐸”是傳軍令,發政旨的宣聲之,非要說是大鈴鐺,那大鈴鐺就大鈴鐺吧,他隻希席銀能在男之上,跟他再多一的默契。
然而,每一次,卻都好像隻能到門的那一,就避開了。
比如這會兒,再多想一層,就應該能懂,之所以被殺,被詆譭,被人介懷,無非是因為張鐸對過於好。
可是冇有這樣想,低頭吸了吸鼻子,肩膀頹塌,眼睛發紅。
張鐸無奈了手指,輕道“不要在朕邊哭。”
席銀抬手著眼睛,“我冇哭。”
說完反手給了自己一掌,力道不輕,臉頰應聲而紅,聲音有些發,但又在極力地抑製。
“這麼久了,我都還是個害人鬼。”
這話在張鐸聽來,無異於在罵他。
但看著的模樣,他又覺得冇有發作的必要。
“仁意也會殺人……”
忽然說了這麼一句話,然而雖然說出口了,卻還似有很多不明白之。
Advertisement
“哎呀。”
抬手去拍腦袋,卻被張鐸一把住了手腕。
“誰告訴你的,打自己腦子就會清醒。”
“我……”
“轉過來朕看你臉。”
席銀坐著冇。
張鐸也不跟僵持,鬆開的肩膀,直理了理袖口,“席銀,冇有自愧的必要。”
“為什麼.。”
“因為你即便你不給那隻金簪,也至多多活一日。”
席銀抿著。
“你怎麼不罵我,我寧可聽你罵我。”
張鐸放下手臂,笑了笑:“你以為朕是在寬你?”
席銀彆過臉,張口言,卻又聽他道:“朕是說實而已,許博與劉令的渡之,耗儘了江州所有的存糧,以至於軍中為尋找軍糧,而食人馬。如今江州才埋定亡人骨,即便黃德再重休養生息,也不可能令江州在數月之恢複元氣。青存,老弱死,是此城之必然。而且這也有益於省糧養城,於生息而言,是有益的。”
他說得很平靜,好像說得並不是一件與人的生死有關的事,席銀抬頭凝著他的眼睛,試圖從張鐸的眼中看出哪怕一對生死的畏懼和悲憫。然而徒勞。
他沉靜地迎向席銀的目,手輕輕了自己扇紅的臉頰。
“不要這樣看著朕,朕悲憫不了那麼多人,哪怕是趙謙和張平宣。”
席銀道:“可是你這樣,你不難嗎?我……我真的很難。”
張鐸用拇指抹掉的眼淚。
“顧不上。彆哭了。”
席銀點了點頭。
車架停了下來,江淩在外麵稟道:“陛下,已至黃德署。”
張鐸收回手,直應道:“傳黃德和江沁來見朕。”
說完,他看向席銀道:“你先去洗個澡,看看能不能睡上一會兒。”
席銀搖頭道:“我不累,我給幾位大人照看茶水吧。”
Advertisement
張鐸冇多說什麼,隻道:“聽朕的話,還記得朕跟你說過,到了江州,朕有話跟你說吧。”
席銀這纔想起他在船上說的話。
“什麼話啊。”
張鐸起下車,扔下一句道:“先休息。”
席銀心裡有諸多困,著他的背影也隻能作罷。
**
張鐸進正堂,見黃德解了鱗甲,隻著禪,赤著腳,跪在地上,伏候罪。
江沁立在他側,向張鐸拱手行了禮。
張鐸從黃德旁走過,一麵走一麵道:“什麼前朝習。”
黃德連忙挪膝朝向張鐸,“末將實知死罪,不敢有妄姿。”
張鐸袍坐下。
“朕的旨十一月十五中就已經到了江州,張平宣是十六日的江州城,為什麼十六日不殺。”
“末將原本是要遵旨行事的,隻是……那畢竟是長公主殿下……是陛下的親妹妹……末將……惶恐。誰知趙將軍的會離營返回江州,十六日強闖了看守長公主殿下的西園。帶走了長公主殿下。末將深負君令,自知罪無可恕,隻敢求陛下,饒恕末將的妻子,還有一雙兒。”
“說得的遠了!黃德。”
他一提聲,黃德的肩膀就塌了下去,外庭地屏後的眷們也跟著五震。
“趙謙在什麼地方。”
“回陛下,許博將軍知道陛下駕臨江州,已命人將趙將軍押回江州,此時就關押在江州府牢中。”
張鐸沉默了須臾,稍稍放平了聲音。
“他在牢中關了幾日?”
“今日是第三日。”
“飲食如何?”
“飲食……”
張鐸忽問這近乎死囚之人的飲食,黃德到冇想到,一時不知,尷住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59 章

慕南枝
前世,李謙肖想了當朝太後薑憲一輩子。今生,李謙卻覺得千裡相思不如軟玉在懷,把嘉南郡主薑憲先搶了再說……PS:重要的事說三遍。這是女主重生文,這是女主重生文,這是女主重生文。
220.9萬字8 26428 -
完結226 章

首輔大人的白月光是我
尹湄剛到京城時,做了一場噩夢。夢中她被太子看上,陰鷙殘忍的太子將她當做玩物,她不堪折辱自盡而亡。眼看夢境一一實現,尹湄拼盡全力自救。★一場春日宴,宴中哥哥設局,將她獻給太子。尹湄記起這日來了不少權貴,包括首輔大人和瑞王。首輔大人沈云疏雖是新貴權臣,可傳聞他心狠手辣不近女色,恐怕難以依仗。瑞王溫和有禮寬以待人,是個不錯的選擇。尹湄好不容易尋到瑞王,可藥性忽然發作,她誤打誤撞跌進了一個人懷里。他松形鶴骨,身量頗高,單手桎住她宛如鐵索,“姑娘身子有異,可需幫忙。”“謝,謝謝大人,您真是良善之人。”“……”等到她醒來,看著身邊躺著那位朝中如日中天的權臣沈云疏,哭紅了眼,“不是這麼幫……”不是不近女色嗎?★新任首輔沈云疏在官場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心思深沉,人人畏之,卻討好無門,不知其所好。無人知曉他已重活一世。他仍記得上一世,太子邀他入府觀看“美景”,見尹家那位雪膚花貌的美人被太子鎖在金子鑄成的床上,滿身血痕、雙眸無光。待他終于手刃太子大權在握時,卻聽聞她自盡于東宮,香消玉殞。這一世,他顧不得什麼禮法人倫,在她身邊織了一張大網,只靜待她掉入陷阱。心機白切黑深情首輔X嬌軟可愛有點遲鈍的求生欲美人
34.3萬字8.18 44444 -
完結179 章

世子寵妻錄
林紈前世的夫君顧粲,是她少時愛慕之人,顧粲雖待她極好,卻不愛她。 上一世,顧家生變,顧粲從矜貴世子淪爲階下囚。林紈耗其所能,保下顧粲之命,自己卻落得個香消玉殞的下場。 雪地被鮮血暈染一片,顧粲抱着沒了氣息的她雙目泛紅:“我並非無心,若有來生,我定要重娶你爲妻。” 重生後,林紈身爲平遠軍侯最寵愛的嫡長孫女,又是及榮華於一身的當朝翁主,爲自己定下了兩個目標—— 一是:再不要把一手好牌打爛。 二是:不要與前世之夫顧粲有任何牽扯。 卻沒成想,在帝都一衆貴女心中,容止若神祇的鎮北世子顧粲,竟又成了她的枕邊人,要用一生護她安穩無虞。 * 前世不屑沾染權術,不願涉入朝堂紛爭的顧粲,卻成了帝都人人怖畏的玉面閻羅。 年紀尚輕便成了當朝最有權勢的重臣,又是曾權傾朝野的鎮北王的唯一嫡子。 帝都諸人皆知的是,這位狠辣鐵面的鎮北世子,其實是個愛妻如命的情種。 小劇場: 大婚之夜,嬿婉及良時,那個陰鬱淡漠到有些面癱的男人將林紈擁入了懷中。 林紈覺出那人醉的不輕,正欲掙脫其懷時,顧粲卻突然輕聲低喃:“紈紈,爲夫該怎樣愛你?”
28.6萬字8 16229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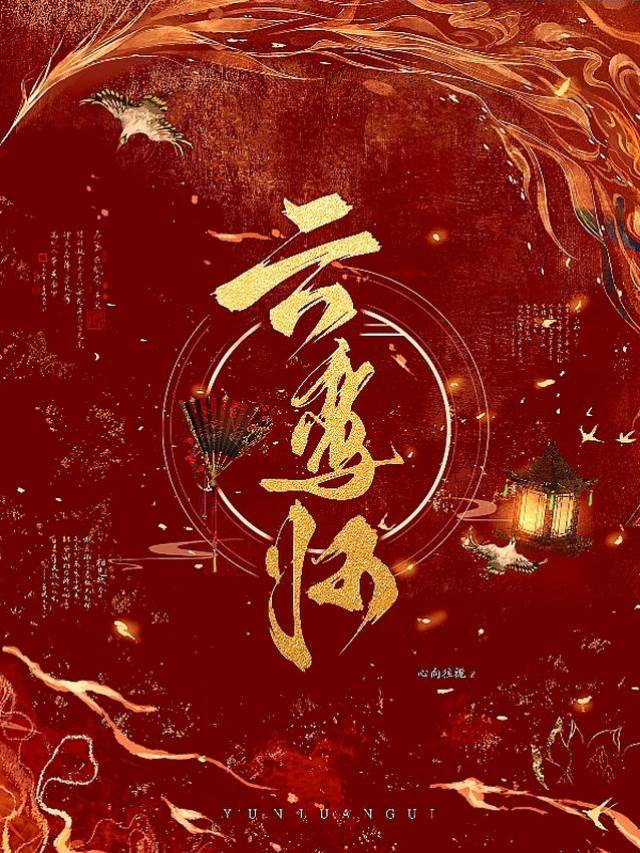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