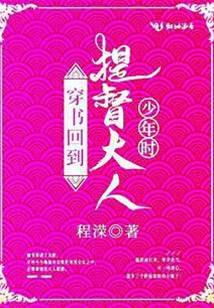《重生后成了權臣掌中珠》 第75章 恍悟
魏鸞這兩日過得不甚順心。
——因為前天清晨夫妻間的那番對話。
并非心狹隘之人, 當初嫁曲園, 周驪音說盛煜曾有心上人時,魏鸞便早早地說服自己,那只是段過往,無需過分在意。是以瞧見盛煜仍將那子的畫像藏在書房,哪怕心里有刺著般難,卻只想著, 若盛煜能放下舊, 便可事過無痕。
誰知盛煜至今仍惦記著那子, 在酒后吐實。
更過分的是,他直言不諱地說與那子相像!
這算怎麼回事!
沒法與從前的心上人廝守, 便寄托在這眉眼神似的枕邊人上?若果真如此, 當初盛煜在玄鏡司獄中維護魏嶠, 幫從庭州軍中帶回魏知非,婚之初并不悉時為撐腰、護周全,究竟是為了,還是為舊日的愫才照拂于?
他究竟把當做什麼?
那樣理直氣壯地說出來,是要安分當好替?
魏鸞但凡想到此,便覺口氣得能炸開!
活了十六年, 從未如此生氣過。
氣悶過后便是沮喪。
這份沮喪,比之當初周令淵迎娶章念桐時,濃烈了千倍萬倍。因那時竇未開,雖與周令淵相甚深,卻只視他為太子表哥, 沒有期待,便無過多的失可言。
但盛煜全然不同。
魏鸞初嫁曲園時對盛煜知之不深,抱著奉旨做好夫人、挽救魏家于危難的心思,謹慎行事,盡力周全,并未奢能與他有多深的分。后來被他維護、照顧,朝夕相后窺破他冷厲外表下的,激漸漸了意,亦不自覺為這男人所吸引。
所以相擁而眠,親吻濃,一切順理章。
而今卻發現,當初的照拂撐腰皆因另一個人而起,盛煜在床榻浴室時不自,在踏青游玩時溫濃,目落在上,心里其實還裝著旁人?
Advertisement
這覺無異于天翻地覆。
魏鸞再好的子,也難忍這般欺辱,大怒之下,當天便稟了盛老夫人,搬回娘家靜心。為免祖母為曲園的事平白擔憂,還編了個魏夫人染病的由頭。到敬國公府后,也沒敢立刻跟雙親說小夫妻的事,只說是想親人了,先陪著魏老夫人用飯說笑。
敬國公府人丁單薄,魏嶠夫婦膝下僅一雙兒,魏知非至今未娶,遠赴朔州長年不歸,魏鸞出閣后,更無小輩。長房倒是兩兒一,可惜老大魏知謙攜了妻兒在京外為,魏清瀾又遠嫁南邊,只剩魏知恭和妻子高氏,帶著小侄兒承歡老人膝下。
難得魏鸞回府,便格外顯得熱鬧。
如此闔府融融之樂,多沖淡了魏鸞心中沮喪。
當晚宿在閨中,更是舒服自在。
待清晨起來,魏鸞昨日霾籠罩的心緒總算好轉,與母親在后園散心時便委婉說了此事。
……
臨近端午佳節,敬國公府的后園里樹蔭濃翳,槭樹碧茂,剪碎的日影隙而,暖洋洋的。放鶴亭旁水波漾,兩只翎如霜雪的白鶴悠閑地在樹下漫步,魏鸞握著玉骨團扇,心不在焉地逗弄白鶴,說完這事時,眉間稍愁容。
魏夫人聽罷,更是驚愕。
“他當真如此狂妄輕慢?還是你錯會了他的意思?”
“怎可能錯會?長寧打探的消息不會有假,那幅畫就擺在南朱閣的書架上,他當初親口承認是婚后對我改觀,又在喝醉酒神智不清時說喜歡了很多年……酒后吐真言,母親知道的。興許他是真對我有意,但這其中摻雜了旁人,誰能忍?”
至于說狂妄輕慢,盛煜本就高傲。
婚之初,他是何等態度,魏鸞記得一清二楚,那十枚金豆來得多不容易,冷暖自知。
Advertisement
魏鸞心中憤懣,氣呼呼地拿團扇拍向旁邊的樹干。
白鶴驚,一溜煙跑開。
魏夫人過去攬住,溫安著,道:“沒事,我和你父親都在,若他實在欺人太甚,自會竭力護著你。咱們公府雖不如從前,卻絕不會看著你被欺負。”說罷,見魏鸞蹙著的眉頭稍稍舒展,才溫聲道:“你呢,打算如何應對?”
“昨日我想過,若他真心待我,我自會同樣待他。但這種摻了沙子的,我不要。即便這門婚事是皇上所賜,最差的境下,不過是如最初那樣,相敬如賓罷了。”
“是想后退?”
魏鸞咬了咬,沒出聲。
理智而言,是該后退的——盛煜對的并不純粹,若傻兮兮地腦袋一熱沉溺下去,到頭來苦的只會是。甚至,按前世的勢判斷,盛煜如今所向披靡,最后仍會登臨帝位。屆時帝王威重,若后宮添了旁人,這份又待如何?
當初選擇嫁給盛煜時,其實就知道往后會是怎樣的路。
只是如今夫妻漸洽,真的面對盛煜的心有所屬,終究心意難平。
心深,魏鸞仍介意枕邊人存有兩意。
若自私些想,其實該退回夫人的位置,收住真心。既不違背嫁曲園以保魏家的約定,亦不至于錯付后傷心傷。
如同當初周令淵迎娶章念桐后,雖知往后定會東宮做太子側妃,卻能收住意,縱周令淵滿口深,亦毫不曾昏頭沉溺。聽聞旁人遇到這樣的事,所想的也是君既無心我便休,沒了男人仍能過得逍遙痛快。
可事到了盛煜頭上,魏鸞發覺很難。
一旦想到兩人往后相敬如賓,不真心而同床共枕,盛煜心里裝了旁人,渾便覺難。
Advertisement
像是有鈍刀割在心頭。
魏鸞恍然發覺,或許比所以為的還要喜歡盛煜。
這愈發讓苦惱。
腦海里浮起男人的冷峻眉眼、頎長姿,乃至聲音神,魏鸞生氣得想揍他,又難以真的割舍,恨恨地咬著牙,憋了半天才道:“真到了無可挽回時,只能如此!不過我還沒想清楚,只是想找母親說說話,這會兒心里舒坦多了。”
這樣的糾結小兒姿態,迥異于從前的明麗張揚。
魏夫人心疼,摟著兒輕聲安,說魏鸞若覺得在曲園委屈,盡可住在公府。等腹中的氣消了,冷靜下來再做決斷,而后親自去廚房,做了桌魏鸞吃的飯菜,將兒哄得漸漸高興起來。
魏鸞住在閨中,陪著父母親,愈發不想回曲園了。
反正盛煜未必在乎。
便竭力拋開關乎盛煜的那點心思,抓住難得的闔府團聚時,討雙親歡心。誰知這邊余波未平,原本風平浪靜的長房竟也出了麻煩——魏峻夫婦昨晚收到了魏清瀾修的家書,心中道與夫君相看兩厭,再無半點意,已決意和離。
清晨魏鸞去魏老夫人那里時,伯母正同老夫人念叨此事。
說魏清瀾當初遠嫁,便十分不舍,去歲寄來的書信中,就屢屢抱怨夫妻不睦,只是那時魏嶠尚在獄中,敬國公府無暇他顧,能做的也有限。上回魏清瀾回京時,更是連著倒了好幾夜的苦水,所幸婚后尚未生育,如今既想和離,府中該當撐腰。
魏老夫人聽聞孫過得委屈,也連連嘆息。
末了,說魏清瀾若當真想得清楚,府里自會為做主。只是這事關乎重大,和離后再嫁畢竟麻煩些,勸魏清瀾想清楚再做決定。
這邊正商量著,外頭忽有仆婦來稟,說曲園的那位姑爺來了。
Advertisement
魏夫人聞言,下意識瞧向魏鸞。
魏鸞亦面意外。
一瞬間,那日清晨盛煜的可惡臉浮腦海,魏鸞幾乎想直呼不見。但祖母與伯母正為魏清瀾的婚事擔憂,哪還能再添,遂竭力克制脾氣,起溫聲道:“想是曲園里有些瑣事,母親不必擔心,我先去瞧瞧。”
“你……”魏夫人想著昨日的愁容,不甚放心。
魏鸞微微一笑,“母親放心,我有分寸。”
說罷,徑自往花廳里去。
……
花廳建在荷池邊上。
仲夏天熱,滿池荷葉早已亭亭,碧綠清圓。隔著滿池荷葉,過開的窗扇,可以瞧見廳里男人背影拔,正瞧著正中懸的那副林下白鶴圖。因魏嶠兄弟并不在府里,廳中亦無男主人相陪,唯有管事奉上香茶,仆婦在外伺候。
仿佛是聽見的腳步聲,盛煜回頭瞧過來。
魏鸞不由腳步微頓。
初回娘家時的憤懣不滿已被克制,此刻瞧見悉的影眉眼,魏鸞心里不知怎的,有種近鄉怯的畏懼。但盛煜忙那樣還親自登門,興許是有正經事要說,容不得耍子,竭力拋開雜念,抬步往廳里走。
盛煜便靜靜地注視著。
夏日單薄的紗隨風揚起,繡金的海棠紋被日映照,熠熠生輝。滿頭順如緞的青皆被挽起,花鈿裝點的發髻上簪了赤金釵,珠串潤,金釵輝彩,襯得那張白膩如玉的臉格外明麗。
修長的脖頸別無裝飾,寬松的領稍稍袒口的白皙,俞見姿修長,輕盈婉。
盛煜的目逡巡,自漸漸惹眼的前峰巒,到纖細有致的腰肢,再到如云翻卷的角,最后落回漂亮的眉眼。目所及,再無旁人,似是要將此刻的姿刻在心上,以前往朗州后的離別相思。
魏鸞卻沒這繾綣心思。
若不是克制著,甚至想揍他一頓出氣。
但這當然不可能。
緩緩行至廳前,命人皆在外候著,而后盈盈而,道:“夫君怎麼來了?”
“來看看你。”盛煜瞧神不對勁,“岳母還未好轉?”
“好些了。”魏鸞有點心虛地敷衍,對上盛煜泓邃察的目,怕他真的問病癥用藥,趕將話題扯開,“夫君特地過來,是有話要叮囑?”
這話說得,即便沒話叮囑,他數日沒見妻子,難道不能來岳丈府上?
盛煜勾了勾,猛然臂將按在懷里。
這擁抱來得太突然,半點都不避諱在外伺候的仆婦侍,魏鸞猝不及防,整個人被他在前,被男人的氣息包圍。錯愕之下,兩只手臂不聽使喚地下意識環在他腰上,等反應過來想推開時,便聽頭頂他低聲道:“我得出京城一趟,歸期未定。”
簡短的一句話,將魏鸞賭氣的心思盡數攪。
詫然抬頭,“什麼時候?”
“待會就走。”
這麼快嗎?魏鸞著他,眉間霎時浮起擔憂。
即使不在朝堂,也知道盛煜近來是忙著跟章家較勁。京城外天高海闊,卻也天高皇帝遠,玄鏡司的布防也不似京城嚴,盛煜這會兒出去辦事……自知無法阻攔,忘了松開環在他腰間的手臂,“在外面千萬留意,當心章家找你算賬。”
“知道。”盛煜淡聲,在眉間啄了下,“等我回來。”
生了隔閡后,這作過于親昵,魏鸞往后躲了躲。
盛煜反被激起興致,腳步稍轉,拿寬厚的肩背擋住廳外目,將魏鸞牢牢困在懷里,而后俯首,強行親在上,不滿道:“躲什麼呢?”
“有人。”
“不怕。”盛煜說著,又親了兩下,甚至企圖撬開齒,臨走前攫取香。
魏鸞被迫朝后仰著,這樣親昵的擁抱親吻里,能到盛煜的溫,察覺他雙臂用力抱住時的眷不舍。咫尺距離,目對視時,亦能看到盛煜眼底的倒影——這目懷抱曾令沉溺,步步深陷,如今卻令疑慮,踟躕不前。
搖擺之間,折磨了許多日夜的那個念頭,終于呼嘯而出。
在盛煜親吻稍頓時,魏鸞抬手,拿指尖擋在他的。
“夫君看清楚我是誰,別抱錯了人。”
這話說得蹊蹺。
那雙流盼如波的眼眸里,似乎還有賭氣的意味?
盛煜心頭有疑一閃而過,因惦記著正事,并未能深想。被的指腹著,盛煜意猶未盡,忍不住含住指尖唆了唆。在魏鸞紅著臉慌回手指時,淡聲笑道:“白晝夜里,我抱的自然只有你。”
說罷,正道:“這趟出京后,京城里興許會有異,你便留在府里出門,讓岳父他們也盡量別出城。若宮里召你,也可推拒,實在推免不過,須跟皇上說一聲,有備無患。切記,塵埃落定前,絕不可掉以輕心。”
這話說得鄭重,能被他為異的,定非小事。
魏鸞頷首,“我記住了,夫君放心。”
盛煜既已囑咐了要事,瞧著外面的日頭,知道不能耽擱太久,捧著腦袋,再度吻過去,肆意攫取。直待魏鸞覺得腔里的氣息都快被攫走,手輕輕捶他時,才松開手。怕再逗留會貪難舍,不發一語,徑直轉出廳。
剩魏鸞站在原地,腦海犯懵。
待回過神,盛煜已過了架在荷池上的曲折廊道。
三兩步追到廳前,又叮囑道:“千萬當心!”
盛煜駐足回頭,朝揚了揚腕間的那串佛珠,角亦勾起笑意,“等我回來。”
而后出了敬國公府,縱馬直奔城門。
挑選的人手已分散幾撥,悄無聲息地出了城,盛煜擺著在京郊辦事的架勢,出了城門十數里,與趙峻頭后,各自飛馬趕往朗州。仲夏的風鋪面而過,道旁綠樹遮天蔽日,盛煜將此行朗州的事再琢磨了一遍,傍晚用飯時心神稍弛,不由想起留在京城的魏鸞。
想起臨別的用力親吻,眷懷抱。
亦想起魏鸞那句古怪的話。
甚至當時的躲閃。
看那神姿態,像是在跟他賭氣似的。
盛煜覺得奇怪,晚間趕路時,忍不住細細琢磨,往前倒推舊事。
而后,在某個瞬間,他終于恍然大悟。
猜你喜歡
-
完結282 章
傲嬌醫妃
她是醫學界的天才,異世重生。兇險萬分的神秘空間,低調纔是王道,她選擇扮豬吃老虎翻身逆襲。他評價她:“你看起來人畜無害,實則骨子裡盡是毀滅因子!”她無辜地眨著澄澈流光的眸子,“謝王爺誇獎,只是小女子我素來安分守己,王爺可莫要聽信了讒言毀妾身清譽!”錯惹未婚夫,情招多情王爺,闊氣太子與帥氣將軍黏上來……美男雲集,
74.4萬字8 78136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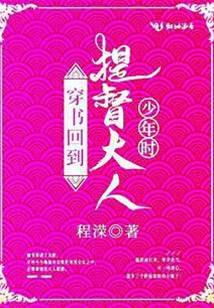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041 -
完結221 章

太子侍妾
簡介: 【雙潔?謀權?成長】 沁婉被倒賣多次,天生短命,意外成為九皇子侍婢,因為出生不好,一直沒有名份。九皇子金枝玉葉,卻生性薄情,有一日,旁人問起他的侍俾何如。 他說:“她身份低微,不可能給她名份。” 沁婉一直銘記於心。又一日,旁人又問他侍婢何如。 他說:“她伺候得妥當,可以做個通房。” 沁婉依舊銘記於心。再有一日,旁人再問他的通房何如。 他說:“她是我心中所向,我想給她太子妃之位。” 沁婉這次沒記在心裏,因為她不願了。......後來,聽說涼薄寡性,英勇蓋世的九皇子,如今的東宮太子 卻跪在侍婢的腳下苦苦哀求。願用鳳印換取沁婉的疼愛,隻求相守一生。她沁婉哭過,怨過,狠過,嚐過生離死別,生不如死,體驗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是沒醜過!後來,她隻想要寶馬香車,卻有一個人不僅給了她寶馬香車,連人帶著花團錦簇都給了她。
40.6萬字8.18 768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