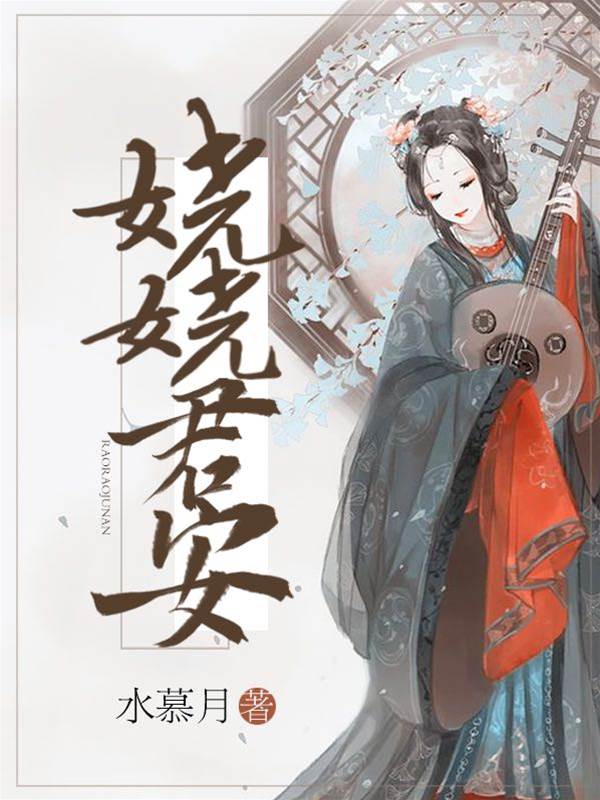《小豆蔻》 第三十五章
得了這聲夸贊, 明檀笑得眉眼彎彎。極有興致地拉著江緒在屋轉悠, 還一地仔細介紹。
江緒這才發現,不過半日,啟安堂依著他這位小王妃的喜好,已然大變了樣。
待介紹完, 明檀小心翼翼問了聲:“阿檀擅作主張布置了屋子, 夫君可有不喜, 可有不適?”
是不適的。
可明檀拉著他輕晃撒,手的, 還不安分地在他掌心搔。他不擅、也從未如此應對子, 說出的話便也聲聲違心。
“無妨。”
“你喜歡便好。”
明檀聞言, 笑容又擴了幾分,心里頭很是滿足。
然的滿足不是白來, 在夜里也要以另外的形式補償回去。
晚上折騰了兩回, 明檀香汗淋漓, 累到快要散架,趴趴地窩在江緒懷中,腦中還迷迷糊糊想著:習武之人力實非尋常, 夫君話雖不多, 夜卻如此熱,難不夫妻之間日日都需如此?那委實也太辛苦了些。
事實上, 明檀對辛苦的認知還有些偏差。因宮謝恩已經推遲一日, 不能再推, 江緒刻意收斂了不。若要盡興, 怕是沒法穿著親王妃品級的禮服好生撐過一日了。
次日從江緒懷中醒來,明檀渾都還酸疼,了眼,想要換個姿勢平躺,卻發現箍在腰間的手收得很。
沒法兒大幅作,好在可以仰頭近距離觀賞到夫君俊無儔的面龐。
不得不承認,的夫君生得真是一等一的俊朗!從前京中子都說,舒二公子玉樹臨風一表人才,瞧著,舒二公子確然是俊的,可比起家夫君,好像略顯溫潤了些,了幾分沙場男兒的凜然氣概。
Advertisement
出手指,了下江緒的臉,見他沒反應,又加了手指,并在一塊兒了,還往上撥了撥他的眼睫。
江緒睡眠極淺,早就醒了。正當他準備拉下明檀那只作的手時,明檀忽然往上蹭了蹭,在他下上輕輕地親了一口,小腦袋又往他脖頸間蹭,還十分依賴地環住了他的腰。
的溫溫涼涼,像過篩蒸出的甜酪,細膩。江緒稍頓,一時竟也不知該不該轉醒。
古人所言,溫鄉,英雄冢。
他忽而覺得,確有幾分道理。
在榻上躺到辰初,兩人一道被婢喚醒。
整裝梳洗了番,巳正時分,兩人又坐上王府平日一年都難得用上一回的馬車,一道宮了。
了宮門,兩人分走兩道,江緒去書房見康帝,明檀則是被侍領著,去壽康宮拜見太后。
思及當初太后也想為賜婚,明檀心中自有幾分怕被為難的忐忑。不過這幾分忐忑并未掛在臉上,與江緒分別后,便拿出了親王妃該有的端莊派頭,目不斜視,從容有致。
當今太后與當今圣上并非親生母子。
圣上乃先帝元后所出,而壽康宮宿太后乃先帝繼后,自個兒還有兩個親生兒子。
往事雖不可追,但稍微用腦子想想都知道,有出自兩位皇后的三個嫡子,皇位之易定然不是表面可見的和平承繼。
再加上先帝元后早逝,元后母家也遠不敵繼后母家樹大深。想來,若非圣上出生之時便正位東宮,早早培養了堅定嫡長的東宮一派勢力,當年在與宿太后的抗衡之中,怕是很難討到好。
而宿太后在爭位落敗后,還能安居壽康宮,無人敢輕慢相待,也定然不是什麼只愿長伴青燈古佛的善茬兒。
Advertisement
思及此時,明檀已被領到壽康宮門口。有老嬤嬤出來與侍接,引明檀:“定北王妃,請。”
明檀點點頭,暗自深吸口氣。
素聞太后近年一心向佛,壽康宮倒也確實有幾分向佛之人的樸素古意,一路往里,沒見著什麼雕梁畫棟,也沒見著什麼金銀玉,只繚繞著經久不散的淡淡香火氣息,讓人聞之不由心定。
“臣妾參見太后娘娘,參見皇后娘娘,愿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康健,萬福金安。”
一路而來嬤嬤都未提醒,皇后娘娘竟也在此。好在明檀眼尖,余瞥見上首端坐的幾位子中,除手握念珠一看便知是太后的婦人外,還有一位年輕子著深紅牡丹描金紋錦,頭戴九朝簪——此等裝扮,除皇后外,不作他想。
“起,賜座。”
宿太后的聲音十分溫和,聽來頗覺親切,不過現下明檀可不敢覺得這位太后娘娘有多親切。
又不是傻子,如果不是太后示意,引路嬤嬤又怎會不提醒,殿中除太后娘娘外還有他人。尤其是皇后,方才若不眼尖,落了皇后的禮,難保皇后心中不快。
“太后娘娘您瞧,臣妾說的,可有半分差池?”章皇后笑意盈盈,“定北王妃端方有禮,最是賢淑貞靜不過。”
太后慈祥地點了點頭,滿臉憐道:“是個好的,哀家瞧著,和緒兒極為相配。”
話音甫落,便有立在側的嬤嬤上前,給明檀送上紫檀木盒所盛的見面之禮。
明檀起,垂首接了,又恭謹福禮,謝太后恩。
殿中坐有五,除太后皇后之外,從敘話中,明檀還猜出了著蝶戲百花六幅的,是太后幺,溫惠長公主;著淡青繡蘭花紋樣宮的,是玉貴妃被發配冷宮后,如今宮中最為寵的蘭妃娘娘;另有位年輕明麗的姑娘——
Advertisement
“嘁,無聊。”
明檀還未猜出這位姑娘的份,便見這位姑娘上下打量著,忽地輕嗤了聲。
“念慈,不得無禮!”溫惠長公主出言斥責。
太后掃了眼,只溫聲打太極道:“念慈便是這個子,想什麼便說什麼,你也不必過于苛責。緒兒這王妃是個好的,哪里會同一個小姑娘計較。”
明檀:“……”
也是個小姑娘呢。
蘭妃許是知道,這不是該開口的場合,垂眸撇弄著茶蓋,安安靜靜的,不怎麼出聲。倒是皇后接過話茬,給明檀介紹了翟念慈。
翟念慈是溫惠長公主的兒,也就是宿太后的外孫,很是得宿太后喜,宿太后還給了一個“永樂縣主”的封號。既如此,見人就懟也不是沒有底氣了。
明檀沒打算和這種三五年都見不上一面的多做計較,但不打算計較,這永樂縣主卻不知是犯了什麼病,盯著懟個不停。
一會兒說“這些年京中貴難道都如王妃一般?真是好生無趣”,一會兒又說“王妃瞧著便是半分不懂沙場廝殺,與定北王殿下怎會有話題可聊”。
明檀含笑聽了半晌,忽而反問了句:“臣妾這些年在京中,甚聽聞永樂縣主之名,想來縣主從前并不久居京城?”
翟念慈懶懶地,本不答的話。
還是皇后解圍道:“念慈隨父北征,確實是甚回京。”
哦,懂了。
家世顯赫版明楚。
還有隨父北征。夫君可不就是定北之王,這位永樂縣主許是在隨父北征的這些年,與夫君有幾分淵源也說不定。
且這位永樂縣主話里話外的意思都是在說,這種生慣養的閨閣小姐配不上定北王殿下,那這不就等于在說,自己很配得上?
Advertisement
搞清楚敵意癥結,明檀也就不怕對癥下藥了。
斯斯文文地品了口茶,溫婉笑道:“縣主不讓須眉、英姿颯爽,真是讓臣妾好生佩服,不過京中閨秀素來都是以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為典范,學著如何端莊賢淑,學著如何克己復禮,學著如何下,如何持家,以穩夫家后方,倒也算不得無趣。
“且殿下平日在軍營之中,有的是將領與他聊兵聊將,回到府中,想來更需要的是一方清凈之地,做妻子的,能噓寒問暖多送碗湯,說會兒家常閑話,想來更能讓殿下心熨帖。”
“……”
翟念慈被梗了梗,半晌沒說出反駁之言。
這定北王妃可不就是在指著鼻子說沒教養不守禮呢嗎?偏生還不能駁什麼,畢竟人家都搬出了太后與皇后擋在前頭。
更讓心梗的是,這定北王妃話里話外都在說,定北王殿下并不想和自己的妻子聊什麼調兵遣將,回家有的是閨房之樂,你自以為是多管閑事。
而另一邊,書房,康帝拿著批好的折子敲了敲桌,饒有興致地問了聲:“新婚如何?娶了王妃,你這也總算是,家了。”
江緒負手,不以為意地應道:“不如何,不過是有些繁瑣。”
“……”
“誰問你繁不繁瑣了?”
江緒又用一種“那陛下是在問什麼”的眼神靜靜著他。
康帝有些無言。
罷了,左不過是他自個兒想留明亭遠,權宜下的婚,且就他那子,指他個婚就突然開竅,也不知道是在為難誰。
康帝想了想,又道:“聽聞你這王妃,在京中閨秀里素有幾分名聲,怎麼說也是正兒八經娶回家的媳婦兒,不可薄待了。”
江緒“嗯”了聲。
昨日那番折騰便花了五千兩,他也沒說什麼,想來不算薄待。不過依設想修葺王府,還得再花上近十萬兩,太過鋪張,回去之后,還是得責令一二。
康帝不知江緒在想什麼,見他沒當回事似的,以為他不怎麼想提新婚新婦,便轉了話頭,說起了近日朝堂之事。
時近午時,康帝與江緒才一道出了書房,江緒不愿在宮中留膳,便徑直去了壽康宮接明檀。
他行至壽康宮時,正見明檀跟在皇后等人后頭,一道從殿出來。
和那位永樂縣主走在一塊兒,不知在說什麼,忽地形不穩閃了閃,似乎是在臺階上撇了下腳,接著便是秀眉微蹙,輕嘶出聲。
江緒想都沒想,上前將攔腰抱起。
翟念慈:“……?”
在自個兒殿里聽到這消息的康帝也迷了一瞬。
猜你喜歡
-
完結1723 章
異瞳狂妃:邪帝,太兇猛!
她是21世紀第一殺手,一雙異瞳,傲視天穹。 一朝穿越,淪為將軍府廢材傻女,當這雙絕世異瞳在這世間重新睜開,風雲變幻,乾坤顛覆,天命逆改! 她手撕渣男,腳踩白蓮,坐擁神寵,掌控神器,秒天炸地,走上巔峰! 隻是…一個不小心,被一隻傲嬌又毒舌的妖孽纏上。 日日虐心(腹黑),夜夜虐身(強寵),虐完還要求負責? 做夢!
152.1萬字8 61464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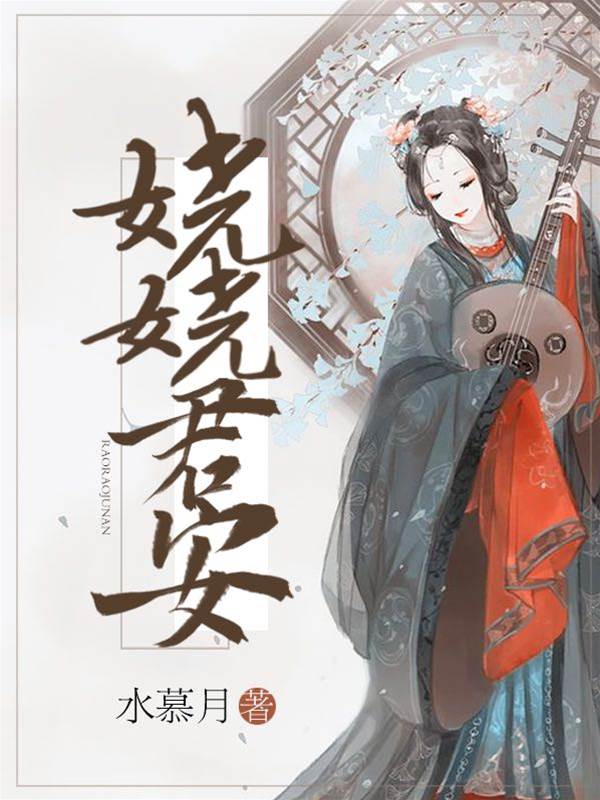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180 -
完結368 章

誰敢打擾我搞事業
穿越而來的容凝一睜眼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沖喜的新媳婦婆家花十文錢買了她回來沖喜,順便做牛做馬誰曾想,這喜沖的太大病入膏肓的新郎官連夜從床上爬起來跑了婆家要退錢,娘家不退錢容凝看著自己像踢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恨得牙癢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容凝咬咬牙一個人去討生活好不容易混的風生水起,那個連夜跑了的混賬竟然回來了還想和她談談情,說說愛容凝豎了個中指「滾!老娘現在對男人沒興趣,只想搞事業!」某男人不知廉恥的抱著她:「真巧,我小名就叫事業!」
38.5萬字8.18 144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