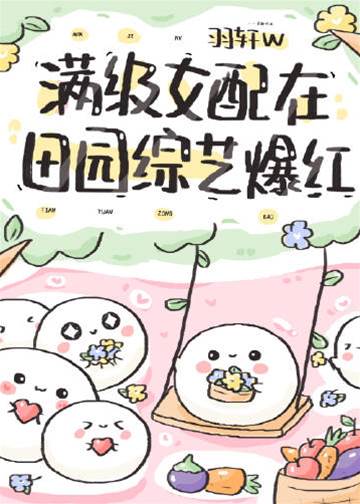《一生一世,江南老》 第三十章 水墨河山影(3)
玻璃柜前的,回頭看沈策,疑他為何不說了。
他給了遲來的答復:“刀鞘都不在了,不可查。”
不自把手上玻璃,好可惜:“所以這就是沈家的老祖宗嗎?”
“不是,他無后。”
忽然被干了周一般,一剎一生,腦海中紛……
沈策又說:“他是沈家族譜上沒有的人。”
“為什麼?”
“他死前告四方,自己并非沈家子弟,”他說,“這兩把兵擺在這里,是鎮守此。古有將星之說,凡帶將星的人,都會守一方水土蒼生,沈家認為它們會愿意替主人守這里。”
竟然不是真正的沈氏族人……
繞著那刀劍的展柜,走了半圈,離刀更近:“都走到封王這一步了,竟然無后。”
“將星大多如此,守一方水土百姓,但殺孽一生難消。歷史上,名將鮮有善終,”沈策見意難平,安說,“好在救人的功德更大,后世多有福報。”
如他自己的遭遇,是屬于執念不忘,自尋苦果。
因果回,眾生平等。人人都要忘卻前塵,唯獨他不肯,自然要懲戒。偏他上一世還是將,經歷非尋常人可比,一直活不下來也正常。
“難道就無解嗎?”讀史,一直對此不平,“我是說現世。”
僅僅是后世福報,那前世過于可憐了。
沈策說:“命理上,‘將星’和‘華蓋’常出現在同一人上。命有將星的人,文武兼備,位高權重,是國之棟梁。命有華蓋的人,才學傲人,命多孤寡,最好的解法是為僧為道。”
“出家?”
“你也可以當作是避世居。”
他不管哪一世都是將星華蓋,華蓋影響,常為過房之子,有贅孤寡的命數。
Advertisement
倒像在給講自己的命盤。
沈策離開了那個展柜。
對那把刀不舍了一眼,跟上沈策的腳步。沈策似乎不打算讓多看這里,起碼今夜不用細看。“你還沒說他什麼?”
“誰?”他好似不懂。
“刀的主人。”追問不舍。
“不可查,一個族譜上都沒有的人。”
“那你怎麼知道這些刀劍的名字?”連主人的名字都不可查。
他但笑不語。
通常這種笑容是在告訴,剛說的多半是假。
唯獨這一回,愿意相信他說的是真的,環繞著刀劍的故事。
二樓有兩個孩子在收拾,見他們來了,其中一個笑著說:“都準備好了。”
言罷,自行離開。
二樓多一半是直通天花板的書柜,其中真本、善本和手抄本有數十萬冊,不止和沈家有關,還是數代收集的古籍,包括不手稿孤本。這樓里的東西從未公示過,戰年代,一部分藏書因為轟炸被燒毀了,頗為可惜。
書架這邊,開著機和空調。
臨東的一間房,擺著書桌和茶座,供人休息。
墻壁上有人掛好了一張占滿墻壁的宣紙,筆墨也備好了,猜,他帶自己來想寫字?
沈策說:“兩個沈家約定過,要十年一祭祖。十年前是你表外公為主,這一次是我們牽頭。我這次會把私家藏品捐出一部分。不止是我們,沈家的世,也會一同做捐贈。”
離上次祭祖竟十年了。
“那兩把刀劍也要捐嗎?”的心早已鞘,把它們的影子收到了心底,舍不得。
他靜了一霎。二樓的燈仿佛也暗了。
“它們也許更愿意守著這里。”他說。
他背過,提筆蘸墨,先將黃河、長江勾畫,再點長安、、柴桑和建康。
Advertisement
“這一次捐贈以沈家藏品為主,大多在漢之后、隋之前。”
筆鋒帶墨,落在紙上,為勾出了那一幅早消失在時空長河中的年代:“漢地中部是我族起源,常它中土、中華,或華夏。”
立在宣紙前的男人,畫的是曾經在軍營、王府常年懸掛的天下版圖。
“漢之后,中土分合不息。沈氏壯大時,天下五分……”
他的筆鋒略頓——
而有兩地盤踞雄兵不可掠侵,北有長安周生,南有柴桑沈策。
……
最初柴桑地在幾個小國當中,如一孤懸的陸地小島,距都城山遙水遠。而因為它是重鎮,自然被幾勢力覬覦,今日是你的,后日是他的,本該富庶的土地遭人掠奪一空。所以沈策和年的昭昭,見慣了哀鴻滿路,殍遍野。
從軍定天下,是他自的志向。
沈策之前,兵權極其分散。沈策自十五歲立下奇功,帶最初沈家軍五千人,一路往西南征伐,用盡手段將兵權集中,到二十三歲,一統南部。
自此,南北格局分明。
“那時南北對峙,互不侵犯。北部最大的敵人,是更北的然。”所以駐守長安的小南辰王每每出兵,都會先知會柴桑,沈策自會按兵不。
“而南部的敵人在西,是吐谷渾,還有更遠的笈多王朝及屬國。”所以當他要出兵,也會先和長安達默契。
這一張圖,有重鎮、古地名,還有江水河流。
沈策是領兵的人,將高山湖泊,河山地貌都藏于心,落在紙上,比只有一個地名更富。他會畫出微小的山脈綿延、盆地湖泊,每個重鎮都要繪小小的一個城池。
“然、吐谷渾,還有南北兩國,還一個?”追問。笈多王朝是印度,不算在。
Advertisement
“還有西南夷部族,如此五分。”
點頭。
“但很快北部分裂了兩國,繼而六分。”
小南辰王死后,北部很快分裂為兩國,日日對戰,消耗彼此。而沈策本想趁此機會,渡江一戰,把疆土往北推到黃河流域,定天下、平戰……
時也,命也。
一副水墨河山的影子在眼前展開。
沈策說的都是古地名,有的聽過,有的沒有,跟著他辨認河山。
他著這一副草草完的中土地理之圖:“漢尚武。而漢之后,依舊名將如云,兵權常制皇權,改朝換代頻繁,這里畫的只是一時的天下。”
有時短短數年,就會是另一番景象。
細看去,他對南境畫的更細:“你更悉南部的地形?”
他承認了:“祭祖在初夏,有沒有興趣,陪我畫一幅長江以南的河山圖?”
像清明上河圖?或千里江山圖?
“從哪里開始?到哪里?”
“從柴桑到普陀。”
好奇他怎麼知道自己會畫,應該是媽媽說的,于是欣然同意:“好,你來主筆。”
沈策功底比深了不知多,又悉這一段歷史,從他幾筆勾出的山脈江河、山石樹影,已經迫不及待看到一副長卷的河山圖了。
昭昭的手指在柴桑附近,往下走,找到了臺州的位置。
“臨海郡,”念著古時的名字,“和那個江臨王有關嗎?”
都帶著一個臨。
后人未答。
昭昭回頭,見樹影婆娑,枝葉于他后的窗外搖曳,伴沙沙雨聲。
看這圖過于神,連落雨都沒發現。昭昭想關窗,怕風吹雨進來,打掛在墻上的紙。手腕被他帶過去,沈策換了支筆,背對著雨,在蘸朱砂墨。
以為他要以此標注都城。
Advertisement
眉心有涼意。
眼前是他握筆的手指,近到看得清他清晰的掌紋……
“辟邪。”他說。
的筆尖,在眉心上停留了數秒。
昭昭像被魘住了,竟以為這是溫熱的,不是朱砂墨,更像……溫熱的。他即刻用拇指掉了,一次抹不干凈,沾了一旁的茶水,抹了兩次終于干凈。都沒來得及看一眼。
沈策沉默洗筆。
過去他常給昭昭點朱砂,新年辟邪。
自從封王,就沒再做過。因為書案上的那朱紅筆,是他勾選斬首犯人的筆,他嫌自己的手再給點朱砂不吉利。某日聽笈多王朝來的僧人講經后,不依不饒,要他照時一般為自己畫朱砂,被他沉臉訓斥了一番,把惹得紅了眼,雖憋著沒哭,卻消失了一日。
后來和迦山的方丈閑聊,才知另一種意義,在笈多王朝這吉祥痣,新婚日,男人會在儀式后親手為人點上……
再看向那水墨草繪的天下,像看到一憧憧影子,如后折著燈的原木屏風,從山到水,到影帳紗……心口稍窒,慢慢地舒緩,再看雨,更大了。
沈策在收拾筆,他穿著白襯衫的側影,消瘦的臉,和后的雨幕融了一幅畫。也許是他講了太多的歷史,讓聯想到江上的白將軍……
“哥,你說我們都有前世嗎?”
他的手在最后一支筆上,停著。
“如果有,你上一世,”是信回的,和他聊完刀劍的主人,更信了,“應該是個將軍。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的那種。”
他的手指沿著筆桿慢慢挲著,微笑抬眼:“在你眼里,我這麼好?”
當然。
夜雨打著樹葉,能看到枝頭在風里晃。
閃電突然撕開夜空,沈策在雷聲落下時,移開了視線。他拿起搭在一旁的西裝外,從窗邊回到跟前,像在醞釀一句極難說出口的話。有預。
開口,卻是再平常不過的:“晚上自己睡,怕不怕?”
“……你想說的不是這句。”直覺拆穿。
他一笑。
電閃雷鳴俱在,風雨吵鬧,兩人之間卻是靜,沒有語言流的靜。
他不給機會探尋追問,看了一眼窗外:“半夜過去陪你。”
“早上被人看到怎麼辦?”
他想想:“天亮前走。”
“……那你還睡不睡了?”
他摟的肩,向外走:“看著你睡。”
猜你喜歡
-
完結1762 章
国民男神是女生:恶魔,住隔壁
三年前,帝盟解體,遊戲天才莫北,低調隱退。三年後,她女扮男裝,埋名回歸,從被人唾棄到重登神壇,引來了全民沸騰他俊美禁慾,粉絲無數,電競圈無人不識。入隊一開始他對她說“安分點,不要有非分之想。”後來她身份暴露,他從桌前抬眸,緩身站起“遊戲裡結完婚就想始亂終棄嗯”
192.6萬字8 20995 -
完結16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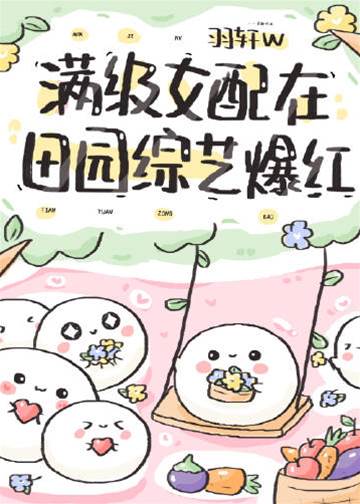
滿級女配在田園綜藝爆紅
滿級快穿大佬洛秋穿回來了。死后進入快穿之旅她才知道,自己的世界是一本小說。這是一本男頻娛樂圈爽文,男主一路升級打怪,紅顏相伴走上人生巔峰。而她,是倒貼男主反被嘲,被全網黑下場凄慘的炮灰女配。彼時洛秋剛剛進入一個復古懷舊田園生活綜藝,綜藝直播…
58.6萬字8 7292 -
完結522 章

軍婚甜蜜蜜:俏軍嫂在八零賺麻了
剛實現財富自由,準備好好享受人生的白富美左婧妍,被一場車禍撞到八零年,開局有點不妙!她成了作天作地,尖懶饞滑,滿大院都避之不及的潑婦,軍人老公天天盼著和她離婚!
81.9萬字8 177403 -
連載370 章

顧總別虐了,鐘秘書她不干了
為了當年的那驚鴻一眼,鐘意甘愿做了顧時宴三年的地下情人。 白天,她是他身邊的得力干將,替他擋酒,喝酒喝到胃出血。 晚上,她是滿足他生理需求的工具人。 整整六年,鐘意眼里只裝得進他一個人,原以為她一定會感動他,他們會走到結婚、生子的路上。 可忽然查出胃癌,她只有不到半年的生命,她才瞬間清醒過來。 跟著顧時宴的這三年,他從未對自己有過關心,從未有過愛意,甚至還要另娶他人。 心死之下,鐘意斷情絕愛,不
87.2萬字8.18 40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