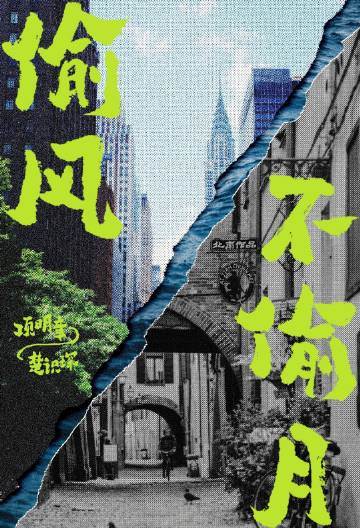《沖喜[重生]》 132
倒是葉云亭聽完沉默下來,著他神遲疑,遲遲沒有開口。
“怎麼了嗎?”葉妄撓了撓頭,他尚且不知道國公府這些日子里發生的事,滿臉都是藏不住的小得意:“父親母親肯定不會同意我留在北疆,不過沒關系,反正他們也不能來北疆抓我回去,我就留在這里了。大哥你可不能趕我!”
葉云亭嘆了口氣,言又止。一時不知道該如何同他開口。
倒是李歧上前來,拍了拍他的肩膀,道:“他不小了,遲早要知道的,若是這點打擊都不住,還談何從軍?”
“?”葉妄聽的滿頭霧水,但也知道必定是發生了什麼他不知道的事,面上的喜淡下來:“可是國公府出事了?”
“……嗯,你去云容之后,國公府出了些事。”
葉云亭也知道李歧說得沒錯,葉妄遲早要知道,也要學會承擔起一個男人的責任。葉知禮顯然已經將他們母子當了棄子,葉妄便是回了國公府,日子也未必好過。要想立足,他只能靠自己。
想清楚之后,葉云亭便將他出事后,國公府所發生的的事細細說與他聽。
連帶著殷紅葉曾經如何低聲下氣地求他幫忙,都沒有一分。
殷紅葉雖然不算個好人,對葉妄來說,卻絕對是個好母親。有些事,他應該知曉。
“你寫一封平安信,我人送去上京。至于是留在北疆,還是回上京,你好好考慮再做決定不遲。”
國公府靠不住,母子兩人等同于相依為命,若是葉妄在戰場上出了事,殷紅葉也就沒了依靠與指。葉妄與他母親好,不可能不考慮這一點。
Advertisement
若是國公府還是從前的模樣,他還能任,但現在,作出決定前,他不得不考慮后果。
“我知道了。”葉妄攥了拳頭,聲音艱:“我先寫信回上京跟母親報平安,其余的……我會好好考慮。”
說完,他腳步沉重地轉離開,背影單薄。
忽然得知的消息太多,他腦子還有些懵。直到回了房,將葉云亭的話一遍遍回想,才真切地到了荒謬和割裂。
從前那個溫文儒雅、對母親包容呵護、對他寵有加的父親,竟全是假象。因為忌憚母親的家世,便將妾室養在外面,甚至還有個比他還要大的兒子。
而母親為了他針對大哥那麼久,竟然全是父親的謀劃,不過是為了給他真正屬意的繼承人讓路。
這太可笑了。
難道他與大哥就不是父親的兒子麼?
他關上門,捂著臉大笑,聲音沙啞,明的水滴自指滴落……
*
晚飯時,葉妄沒有出來。
葉云亭想著他此時的心,只婢給他送了糕點過去。
與他不同,葉妄是真的孺慕戴葉知禮這個父親,因此在得知殘酷的真相時,才會更加的難以接。
而他早就已經習慣并接了葉知禮的冷漠和虛偽。
晚飯過后,李歧見他一臉擔憂,嘖了一聲,牽著人到了葉妄門前,道:“你在這看著,我去幫你開解開解他。”
“???”葉云亭剛想問他要怎麼開解,就見李歧上前,一腳踹開了閉的房門。
葉云亭:……
坐在地上的葉妄用袖胡了眼睛,爬起來茫然地看著闖進來的人,眼眶紅彤彤,顯然哭過。
Advertisement
“還躲在屋里哭?”李歧雙手抱懷,嗤笑一聲。
“我、我沒哭……”葉妄臉上燒得慌,囁嚅著反駁,但頂著通紅的眼睛,卻實在沒什麼說服力。
“沒哭你躲在屋里干什麼?”李歧冷笑道:“我若是你,要麼現在就回上京,將那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打一頓,然后帶著母親離開國公府另謀生路;要麼就去戰場上掙夠功勛再回去,堂堂正正地提出分家。”
“躲在屋里哭是能你好過一些,還是能葉知禮到懲罰?”
“都不能。”葉妄被他說的無地自容,迷茫的眼神也漸漸堅定起來:“我明白了。”
見他還不是無可救藥,李歧神緩和了一些:“現在知道要怎麼選了?”
“我要留在北疆,”葉妄朝他深深一揖:“我想加玄甲軍。”
他不甘心就這麼回上京,然后灰溜溜地帶著母親從國公府離開。母親一生驕傲要強,他怎麼舍得讓跟著自己的委屈?
“看來還沒哭糊涂。”李歧輕嗤一聲:“不過我麾下玄甲軍可都是憑本事進的,你先去姜述手底下待著,可別三天都撐不住就哭著鼻子要回來。”
“我絕不會給大哥和王爺丟臉。”葉妄抹了一把臉,神堅定道。
“明日我人來領你去軍營。今晚先把飯吃了。”李歧嫌棄道:“你不吃飯就罷了,連累你大哥跟著擔憂,也吃不好。”
葉妄這才注意到,葉云亭就在門口看著。他不好意思地垂下頭,囁嚅道:“大哥擔心了。”
“你想明白就好。”葉云亭走近,拍了拍他肩膀。接著想起李歧曾說過,他手底下的將領中,就姜述訓人最狠最下手,目又不由帶上了一憐:“今晚好好休息吧。”
Advertisement
等去了軍營,恐怕睡個好覺都是奢侈了。
葉妄不明所以,點了點頭,送他們離開后,吃了婢送來的糕點,便去洗漱休息,準備養足了神明日去軍營。
另一頭。
李歧與葉云亭并肩回了自己屋里。
屋里四角燒著暖爐,暖意融融。李歧殷勤地替他將披風解開掛好,催促他去沐浴。
葉云亭一臉莫名:“天還沒黑。”
“洗完便黑了。”李歧攬著他往浴房的方向走,湊在他耳邊低低道:“或者我同你一起洗……”
“……”葉云亭耳朵有點紅,但還是鎮定道:“浴桶只能容一個人。”也沒有浴池,所以永安王想要共浴的小心思恐怕要落空。
“我明日人來換。”李歧臉不虞,心想這都督府果然破舊,竟連個大些的浴桶都沒有。
共浴的小心思被迫作罷,李歧只能等葉云亭沐浴后,自己再進去。
等他洗漱完出來,外頭的天已經黑了。
屋里燃著點點燭火,安神香清淡的氣味漂浮在帶著暖意的空氣中。
葉云亭只穿了一中,站在床邊,指著里側的包裹疑道:“這是什麼?”怎麼還藏在床上?
李歧朝他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
“……?”葉云亭直覺不對,將那包沉甸甸的東西撈出來放在桌上,也不多問了,一副要就寢休息的模樣。
但李歧可不會讓他輕易揭過,這包裹里的東西,可就是等著晚上要用的。他揚起角,拎著包裹走到榻邊坐下,笑容里染上了旁的意味:“這可是我今日特意去給你買的。”
他一邊說,一邊手指翻飛,將那包得嚴嚴實實的包裹緩緩拆開。
Advertisement
“我昨晚喝醉了酒好糊弄,今晚可沒喝。”
“……”
他說話間,溫熱氣息噴在葉云亭耳側,讓他白皙的脖頸一點點泛起了紅。心里如同揣了一只不斷蹦跶的兔子,跳得又快又急。
葉云亭攥了攥手指,心想都已經親這麼久了,他們又彼此心悅,遲早都要有第一回 的……他深吸一口氣,擺正了心態,努力克服的緒,去看那沉甸甸的包裹:“……這里面都是脂膏?”
就算要圓房,倒也不必買這麼多?
這要用到何年何月去?
“嗯。”李歧終于拆到了最里層,他解開了系帶,目攝住葉云亭,無意識地了干的,聲音低啞道:“那掌柜說這里面的都是新貨,我們可以一個個試……”
反正今晚還有一整夜的時間,他還特意代了五更,明日就是天大的事,也不許旁人來打擾。
聽他如此說,葉云亭心中也悄悄期待起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40 章
三嫁鹹魚
林清羽十八歲那年嫁入侯門沖喜,成為病秧子小侯爺的男妻。新婚之夜,小侯爺懶洋洋地側躺在喜床上,說︰“美人,說實話我真不想宅鬥,隻想混吃等死,當一條鹹魚。”一年後,小侯爺病重,拉著林清羽的手嘆氣︰“老婆,我要涼了,但我覺得我還能繼續穿。為了日後你我好相認,我們定一個暗號吧。”小侯爺死後,林清羽做好了一輩子守寡的準備,不料隻守了小半年,戰功赫赫的大將軍居然登門提親了。林清羽
42.5萬字8 13571 -
完結126 章
禁宮男後
他百般折磨那個狗奴才,逼他扮作女子,雌伏身下,為的不過是給慘死的白月光報仇。一朝白月光歸來,誤會解開,他狠心踹開他,卻未曾想早已動心。當真相浮出水麵,他才得知狗奴才纔是他苦苦找尋的白月光。可這時,狗奴才身邊已有良人陪伴,還徹底忘了他……
27.3萬字8 6719 -
完結114 章

貌合神離
你有朱砂痣,我有白月光。陰鬱神經病金主攻 喬幸與金主溫長榮結婚四年。 四年裏,溫長榮喝得爛醉,喬幸去接,溫長榮摘了路邊的野花,喬幸去善後,若是溫長榮將野花帶到家裏來,喬幸還要把戰場打掃幹淨。 後來,溫長榮讓他搬出去住,喬幸亦毫無怨言照辦。 人人都說溫長榮真是養了條好狗,溫長榮不言全作默認,喬幸微笑點頭說謝謝誇獎。 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會這樣走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溫長榮的朱砂痣回來了,喬幸的白月光也回來了。
32.8萬字8 9088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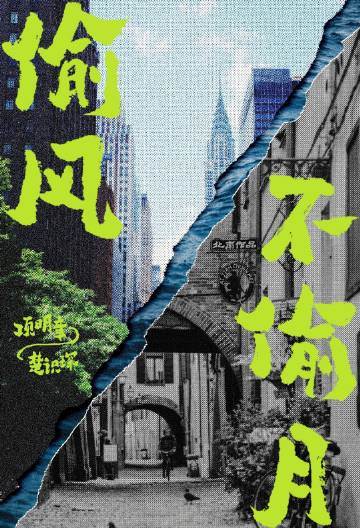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1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