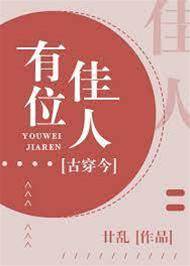《斬尾》 30
“小甜得……”姒瀧用骨杖挑了一下年的下,嗤笑:“去,去你們的箏姐姐來……還有,多點人過來……”
年著姒瀧的骨杖往下一撥,眼里飽含深意,說:“好……奴這就去……讓人來服侍您,和您的朋友……”又看了姜荔一眼。
姒瀧笑著罵道:“賤坯子……快滾!”
這是一個倡寮。
姒瀧背靠在墊上,溫暖的火焰燃燒著,他角含笑,一副漫不經心的愜意模樣。他一邊觀看著場中樂奴的表演,一邊用手輕打著拍子。姜荔被帶到這個奇怪的地方,不明白姒瀧的想法,但也并非一無無知——以前族中,也有此類做皮生意的腌臜帳子,只是姜荔不興趣,從未去過……姒瀧拽著姜荔的肩,一下子把他拉到下來,咬著耳朵說:
“放松點……哥哥是帶你來快活的……”
姜荔:“……”
此時,一群挨挨的年,嬉笑著涌了過來。和剛才那個年一樣,他們的皮都比較細,上的發剃得很干凈,還帶著些香氣。和外邊的男子比較起來,不太相同。年們年紀都很輕,滿臉青,正是雌雄未辨的年歲,有的面上還涂了一層薄薄的脂。
這白尾是想做什麼?姜荔心想。忽然,姒瀧連拍了幾下掌,那些個年,就紛紛嬉笑著跪了下來,圍繞在姜荔邊。有的去他的,有的去按他的肩,有的去敲他的上臂,有的給他喂酒,姜荔全上下,都被一群帶著脂香氣的年圍住了,無數雙手,落到他的上來,搶著服侍他的各個部分。
姜荔驚住了,他猛地回自己的,那個捶的年便撲了個空;后肩的年卻笑著靠了上來,一溫熱的氣息靠在姜荔背上;手臂忽然被兩個年拉住,一左一右,按著酸痛的。姒瀧見狀,壞笑一下,猛地推了其中一個年的背一下,讓他一下子趴到了荔的膛上,姒瀧道:“還愣著干什麼?還不快給我好好伺候這位爺!”
Advertisement
“是~”年們笑著了上來。
被這麼多人圍著,姜荔非常地不自在。他一下子推開了趴在他上的那個弱年,遞到邊的酒杯也被猛地打落。只聽見接連響起的幾聲“哎喲”聲,姜荔上迸發出幾道風刃,一下子把年們都吹開,趴倒在了地上。
“走開!”
年們有的腦袋磕上了地板,有的后腰挨上了矮桌,哎喲哎呦地呼著痛,面面相覷,又不敢再靠上前來。樂奴們熱鬧的樂聲也停止了,場面一下子尷尬下來,年只得將求救的目向了姒瀧。
原來,貴族之中,多有將此種未長的年,飼養調教,當作玩的。只是多是奴隸,而且年一旦長大,失去了那副雌雄莫辨的態,也就失去了寵。
見姜荔一臉不虞,姒瀧揮了揮手,讓人退下,只留了個安靜的,給他們兩人倒酒。“算了,都是些下賤奴隸,不要也罷——嘗嘗這酒,聽說是從姜族運來的,你看是不是?”姒瀧笑著說。
留下的一個青年,一臉清淡,將酒杯遞到姜荔前,便深深地低下了瘦弱的脖子。姜荔見杯中那碧,一悉的香味襲來,一愣,竟也未再拒絕,張口喝下了那杯姜酒。
一辛辣的味道涌頭,果然是,記憶中的滋味……
芳香濃烈,醇厚甘,帶有一苦味,吞咽,又在齒間,留下長久的香氣。
苦酒,姜荔心中的記憶被,而酒杯迅速又被填滿,銀的杯中,閃著碧綠的,如綠玉一般。見姜荔安靜下來,姒瀧給年使了個眼,讓他好 好伺候好姜荔,便又敲了敲骨杖,讓竹鼓樂再度響起,只是換了首清靜些的曲子。
Advertisement
悠揚的管弦聲中,荔的心仿佛也放松了下來……讓人迷醉的火和熏香,讓他逐漸回到了久違的姜族草原。草原上那些黃的小花,是如何被摘取下來,釀制翠的醇酒,他再也清楚不過。而現在,這悉的味道,竟然遠隔千里,再次回到了他的舌尖。
荔不關心那些歌舞,也不想聽那些奏樂,只是覺得,如此放縱而肆意的氛圍,似乎也化了他的神經。青年一杯一杯地替他倒著酒,沉默著,讓他也忘記了還有這人的存在,只一杯杯,將那些讓人喪心志的,澆苦心愁腸之中。一個穿淡藍的子,抱著琴盒緩緩步來,聽姒瀧喚,似乎是做箏娘。箏娘打開琴盒,將瑤箏放在案上,素手撥弦,叮叮咚咚的琴聲就響了起來。
而聽了一會奏樂,酒興上頭的姒瀧竟自己趕走了伴奏的樂奴,抱著琵琶,開始了自彈自唱。
姒瀧今日換了一奢華清貴的,銀線如月一般。散落在鬢角兩邊的碎發,用珍珠結了長長的小辮子,貴氣風流。眉間依然是鮮明的紅蛇印記,卻洗去了塵土,留下了艷。王孫公子,優游貴樂,生于綺紈錦緞之間,從不知稼穡生計之難,那又是為了什麼,值得他如此餐風飲、櫛風沐雨,流離在外?
姒瀧角含笑,手指撥了撥琵琶的弦,一段樂音流淌而出。轉軸撥弦、運指如飛,琵琶被他抱在懷中,一首悠揚婉約的曲子,如流水般傾瀉而出,縈繞耳際,將一切背景、人都模糊。人們不由得沉浸在樂聲之中。姒瀧抬起頭來,目沉沉,眼神在姜荔上落了一下,又落向遠。和著琵琶樂曲,他輕聲唱道:
Advertisement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歡樂或哀嘆,都在一曲之中。
好像有無盡的哀愁,也好像有無邊的歡樂,行人且行且,且放且縱,是執著,亦是追求。人間三生四季五味,一念之間,只生死二字。樂聲放縱、琵琶急促,笑中有淚,喜里帶哀。一曲彈盡,三百歲已過。
姜荔一杯一杯喝著酒,腹中如火燒一般,酒侵襲了理智,讓他腦筋脹痛、思維遲鈍。神志如同漂浮于水面之上的鵝羽,飄飄、浮浮沉沉。他失手打翻了一杯姜酒,伏倒在矮桌之上,酒浸了襟,順著桌面淌了下來。不知何時,姒瀧也停止了發瘋一般的彈奏和歌唱,不再拉著人飲酒、跳舞,而是瘋累了,躺在地上,頭枕著姜荔的大 。
“別喝了……你醉了……”姒瀧拉著姜荔的袖,是把他的酒杯扯落,酒撒了一地,香氣四溢,他說:“可憐的小荔枝… …別喝了……”
“我看你才醉了……”姜荔眼角發紅,目游離,青年又給他倒了一杯酒,他順手將酒倒在了姒瀧上,笑了。
“好你個壞心思的……”姒瀧笑了,漉漉的手指了一下姜荔的臉,“難為你了……”
“了不苦吧……他們、他們一個黑無常、一個白無常……哪里知道疼人了?”
姜荔一笑,打掉了姒瀧的手,他頭重腳輕,坐也坐不穩,指責道:“你又算個什麼好東西?”
“是是……”姒瀧吃吃笑著,“我的確不是東西……”
姜荔冷哼一聲,他揪著姒瀧的領,想把他拖起來,喝醉了的人 卻如死豬一般沉重。姜荔也四肢無力,只得把姒瀧又扔到了地上。即使酒醉之刻,姒瀧上扔背著那個長條狀的品,與他一的裝扮不符。姜荔有些好奇,隨手了那個東西一下。
Advertisement
姒瀧卻猛地躲開了,他抱著那布包,坐了起來,突然冷冷地說:“別。”
姜荔也喝多了,指著姒瀧的鼻子,罵道:“你以為、以為——我稀罕?”
“自然是不稀罕的……”姒瀧靠了過來,鼻尖在姜荔臉上輕輕劃過,臉上帶笑,仿佛剛才的冷漠是幻覺。姒瀧的眼中卻很冷靜,他說:“不要稀罕任何人……姜荔……”
姒瀧拖著有些站不穩的姜荔,回了住。他自己也喝了不酒,走起路來七扭八扭,好在沒摔倒,一路磕磕地,回到了住附近。人還未到,等在樹下的姒洹,就聞到了一陣濃重的酒氣。
猜你喜歡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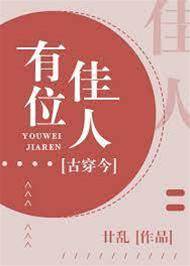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241 -
完結107 章

終于不再愛你
“這一生命運多舛,兜兜轉轉到頭來愛的只剩自己。”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簡雨曾固執、撕心裂肺的愛著一個男人,流云匆忙的二十年,終于有一天,他放下了。 邢青鋒終于明白,當一個人真正心死時,可以拋棄一切頭也不回,再也不會出現。 前期渣到死后期悔青腸攻x前期溫柔后期抑郁受
15.9萬字8.18 10167 -
完結263 章

完了,少將彎了[星際]
當少年發現自己來到未來星際世界的時候,他是有點小懵逼的。 嗯,懵逼程度請參考原始人穿越到現代社會。 現在他成了這個原始人。 還好抱上一個超級粗的金大腿,膚白貌美大長腿的高冷星際少將閣下帶你裝逼帶你飛。 可是大腿想要把你丟在領地星球裏混吃等死做紈絝,還得履行為家族開枝散葉的義務做種豬怎麼辦? “不、用、了……我,喜歡男人。” 絕對是純直的少年挖了一個坑,然後用了自己一輩子去埋。 嗯,這其實就是一個披著星際皮的霸道元帥(少將一路晉級)愛上我的狗血文。 又名《全宇宙都認為是我這個被掰彎的直男掰彎了他們的男神閣下》 每天上班都要在戰艦上被少將閣下強行塞狗糧的部下們一邊強勢圍觀一邊冷笑。 撩了少將大人你還想跑?呵呵。
107.6萬字8 73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