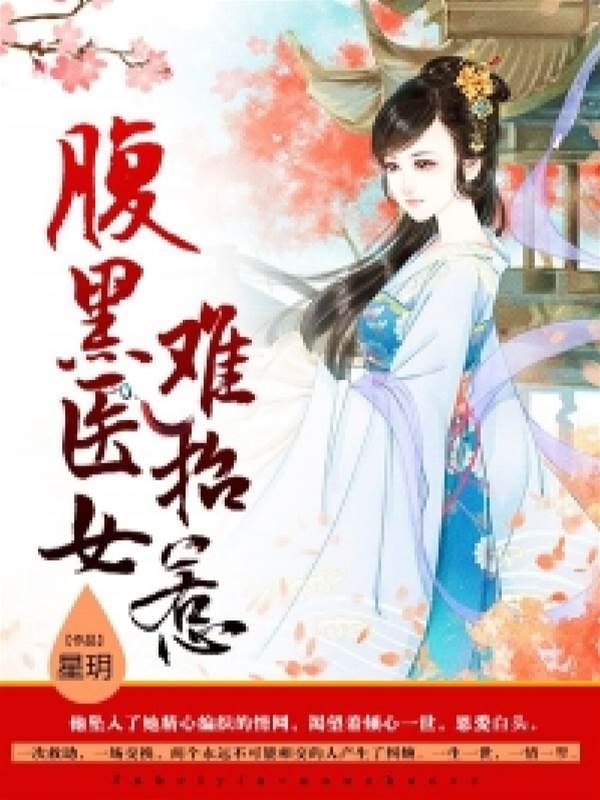《吾家嬌妻》 第063章
? ·
姜令菀低頭,瞧著陸琮這胳膊橫在的前,箍得疼得慌。
怕被人瞧見的樣子,趕側過頭偎在他的懷里,聞了一會兒他上好聞的味兒,之后才頓時覺得不對勁,忙眨了眨眼,用力掙扎了幾下:“陸琮!”
他就這麼把提上馬背,什麼樣子?這名聲還要不要了?
生得小,自是跟個小仔兒似得被他輕輕松松攬在懷里。陸琮低頭瞧了一眼,見發惱,嗔怒的聲兒聽得人也格外的舒坦,仿佛是糯的棗泥糕,直甜到人兒心坎里去,遂趕開口道:“別,當心摔下去。”
姜令菀最惜自己這條命,可今日若是換做旁人,是打死都不會從的,誰這人是陸琮呢,況就不一樣了。知道這陸琮是個有分寸的人,應當不會做出這等魯莽之事,可今兒無端端將提上馬背,卻是事實。姜令菀下意識了手臂,生怕摔下去,心里卻擔憂著:若是這事兒被爹娘知道了,也不曉得該如何訓斥。
姜令菀撇撇,饒是戴著帷帽,這迎面刮來的寒風也讓臉頰作疼,這天兒實在是太冷了。
一直到了沒人的地兒,陸琮才停了下來,然后下馬,抬手將抱下來。
姜令菀坐在馬背上,一雙大眼睛過帷帽隙著陸琮,之后沒理會陸琮的手臂,自顧自下來。去年生辰的時候,特意讓爹爹給請了騎馬的師父,生得聰慧,自是學什麼都快,何況這騎馬本就是興趣的,目下這下馬的姿勢標準嫻,倒是頗有一番英氣。
陸琮瞧著,眼神也出些許贊許。
姜令菀站在陸琮的跟前,整理了一下裳,抬眼一瞧,發覺陸琮這廝個子生得極高,這小板,充其量只到他的心口,也難怪在力上也實力懸殊了。不過不擔心,年紀還小,還會長個兒呢。姜令菀朝著四周了,瞧著二人站在這河邊的空曠的草地上,四周沒人,便一把摘下頭上的帷帽,問道:“琮表哥這是做什麼?”
Advertisement
他就是再想,哪有大街上直接擄人的道理?
而且最令氣惱的是他這人力氣太大,又是個魯的,雖是無意的,可這麼長一段路,前正在長大的兩被箍得發疼。生得細皮,興許這會兒都有淤青了,可陸琮在這兒呢,也不好意思。
陸琮瞧一張俏臉滿是慍怒,頭上梳著的兩個花苞髻也有些了,這才面不自然道:“你裳臟了。”
姜令菀原先心里早就給他想好答案了,可以說是想念了,也可以說是那日瞧著和薛崢親近,他誤會是男子,心里頭吃味兒了,卻不料他說出來的是這個答案。頓時氣不打一來,作勢上馬,道:“陸琮,你太討厭了!我服臟不臟,干你什麼事兒。”連小姑娘都不會哄的男人,活該娶不到媳婦兒。
陸琮哪里能讓上馬,趕按住的手,道:“璨璨,別胡鬧。”
姜令菀將自個兒的手了回來,眸瞪得渾圓:“誰胡鬧了?你當著府中姑娘和丫鬟的面把我擄了來,這才是胡鬧。若是我名聲壞了,看你怎麼賠!”
陸琮無奈,這小包長了小姑娘,除卻瘦了些漂亮了些,這脾氣仿佛也見長。他將右手握拳,虛虛放在邊,輕咳一聲:“你裳后面……”
姜令菀擰著眉,氣惱的回頭了,瞧著自己屁上那攤紅的痕跡,一下子傻眼了。
一張俏生生的臉頰“騰”的紅了,又抬頭了陸琮的臉,曉得他這會兒心里在想什麼,遂趕道:“這……我尚未行經,怎麼可能……”
話說了一半,趕住。
這等姑娘家私之事,就是同四姐姐講的時候,四姐姐都一副的模樣,再大大咧咧,也不能和一個男子說這個啊。而且并不是沒經驗的,這月事有沒有來,又不是木頭,自個兒有覺的,況且……再如何兇猛,這冬日裳厚,若是滲到斗篷上,那估著半條命都去了。
Advertisement
不是傻子,自然想著方才玲瓏齋一事,便曉得定是姜令蕙搞的鬼。
就是存心想讓出洋相。
若是方才不注意,陸琮未出現,指不定這會兒有多丟人吶。
姜令菀自認不是個無理取鬧的,這會兒知道原因,趕低頭裝鵪鶉,氣焰一下子矮了一大截兒,弱弱道:“謝謝琮表哥,我……我想回去了。”
昔日活潑纏人的小包變了俏俏的小姑娘,陸琮有些不大習慣,可目下瞧著一張小臉,臉頰還是有些的,就算再如何變,子擺在那兒,總歸是這個人。他微微頷首,道:“我送你回去。”
姜令菀點點頭:“嗯。”
陸琮抬手去牽馬,忽然想到了什麼,手微微一松,那馬兒便“哧溜”一下跑遠了。
姜令菀再次傻眼了:“琮表哥……”哭喪著一張俏臉,眼神依賴的著陸琮,道,“……這馬跑走了,咱們怎麼回去?”
陸琮沒做過這種事兒,目下有些心虛,之后若無其事道:“這馬子野。罷了,咱們走吧。”
姜令菀了他一眼,頓時明白了。好啊,敢還當是傻子來著,這馬可是認識的,同陸琮極有默契,哪里如他口中所言是“子野”?可目下瞧著他這番稚舉止,心里仿佛一點兒都不討厭,還歡喜來著。
姜令菀裝作不知,低頭彎了彎。
之后抿,像小媳婦兒似的跟著陸琮往回走。可一想著自個兒屁上的這攤紅印記,便耷拉著小臉,抬手將這上的斗篷扔了。
陸琮趕忙制止。姜令菀嘟囔了一句:“我不要穿。”
陸琮曉得氣的子,什麼事都得順著的心里來,是個不愿將就的,可這會兒天氣冷,若是將寒的斗篷了,這小板保準著涼。陸琮將上的披風解了下來,系在的上,道:“這樣總了吧?”
Advertisement
陸琮的披風比的斗篷大上許多,自然遮住將后面的悉數遮住。
抬了抬,勉勉強強同意:“好吧。”
陸琮是個沉悶子,原先姜令菀想著自己才不主說話,非得他承認錯誤了才理他,可目下憋得慌,走了一段路之后就有些忍不住,小聲道:“琮表哥這些年……過得如何?”
陸琮對于姑娘家沒經驗,正愁不知該說些什麼,如今聽主問起來了,才松了一口氣,之后答道:“還,不打仗的時候就練武看兵書,這日子過得快,這一眨眼四五年就過去了。”他側過頭瞧了一眼邊的小姑娘,道,“變得太快,我都認不出你來了。璨璨,你可是在生我的氣?”
被中了心事,姜令菀趕矯的嘟囔道:“我有什麼氣好生的?”
陸琮是個不善言辭的,目下年輕,沒經歷過同小姑娘相,自是有些拘謹。若是往日,小包生氣了,他只管拿些好吃的哄一哄,立馬就開心了。可這會兒,人家是姑娘家。陸琮垂了垂眼,說道:“沒生氣就好。今日之事,待會兒我會向姨夫姨母解釋,不會讓他們責罰你。”
曉得今兒他是好意,是個是非分明的人,遂趕道:“沒關系,若是我娘問起來,我只管說是我自個兒想琮表哥了。”
聞言,陸琮停下步子向,眼睛亮亮的:“你想我?”
姜令菀翕了翕,沒吭聲兒。曉得這個年紀的陸琮,對于打仗興許有一番見地,可對于同姑娘家相,可還是個生手。上輩子同陸琮剛親那會兒,陸琮是個不知男之事的,房花燭夜試了好幾回都沒進去,他急,害臊,蹭著蹭著才終于事兒了。別瞧著陸琮面上神淡然,仿佛什麼事兒都難不倒他似的,可實際上他只不過是學得比旁人快些,目下還是個青的大男孩呢。
Advertisement
譬如如今這句話,若是換做別的男子,那便是輕佻放之言,可陸琮一雙眸子亮亮的,仿佛有些驚喜。
輕咳一聲,心里罵了一句呆子,之后垂下眼道:“太久了,都忘了。”
陸琮聽著,許久沒說話,之后才道:“我還記著,有機會教你騎馬來著,方才見你騎嫻,可是專程請了師父?”
姜令菀有一搭沒一搭的接話:“嗯,去年生辰的時候我讓爹爹給我請了師父。”
陸琮眉眼溫和:“你學得倒是快。”
姜令菀暗下嘀咕:可不是因為生得聰明、腦子好使嗎?只是上卻謙虛道:“師父教得好,而且也嚴格,好幾回我都累得不想學了,可師父說這騎馬得吃吃苦頭才。”
這個陸琮自然知道。瞧著細胳膊細的,學起馬來肯定了不苦頭,目下只一年,這騎便已經不錯了,也算得上有天賦了。
陸琮忽然想起了什麼,從懷里掏出一塊寶藍汗巾,里頭包著碎兩半的劍墜,道:“這劍墜上回摔碎了。”
姜令菀瞧著他這副模樣,倒是沒生氣,道:“那日你是為了就祐哥兒,我得謝你才是,這劍墜……也不值幾個錢,碎了就碎了吧。”當初買的時候,不過八十兩銀子,如今陸琮戴了六七年了,整日舞刀弄槍的,還能完好無損,已經很不容易了。
陸琮卻道:“璨璨,目下我的劍墜碎了,你得給我買個新的。”
姜令菀瞧了他一眼,直接往前面走,心里嘟囔:又不是賣劍墜的。
可走了幾步,陸琮卻像堵墻似得擋在的面前,一下子撞到了的鼻尖兒。吃痛蹙了蹙眉,陸琮趕出手了的鼻子,言辭溫和了些:“好不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455 章

神醫王妃超難寵
她是古醫世家嫡系傳人,穿越成了他的沖喜王妃,盡心盡力救了他的命后,他心中的白蓮花出現,直接遞給她一封和離書。古代的棄婦不好當,但她從此腰桿挺直了,也不抱狗男人大腿了,直接走上了人生巔峰。皇帝跑來獻殷勤,世子爺十六抬大轎娶她進門,富商抱金山銀山送給她……某日,他出現在她面前,冷著臉:“知道錯了嗎?知道錯了,就……”回來吧。她笑著道:“下個月初八,我成親,王爺來喝杯喜酒吧,我給孩子找了位有錢的后爹。”
270萬字8.33 334573 -
完結1511 章

鎮國駙馬爺
沉迷三國殺的季平安玩游戲玩到昏迷,一覺醒來,卻穿越到了大宇王朝,還一不小心成了大宇王朝的最大軟腳贅婿,當朝駙馬爺,還順便激活了一個三國英魂系統,只要有金子,就能夠召喚三國里面的所有武將謀臣,梟雄美人,從此以后,季平安走上了一條為金子不擇手段的道路!“叮!”“恭喜宿主成功召喚趙云英魂!”“叮!”“恭喜宿主召喚馬謖英魂!”召著召著,從一個贅婿駙馬爺卻成了大宇王朝的鎮國駙馬爺!
258萬字8 49285 -
完結2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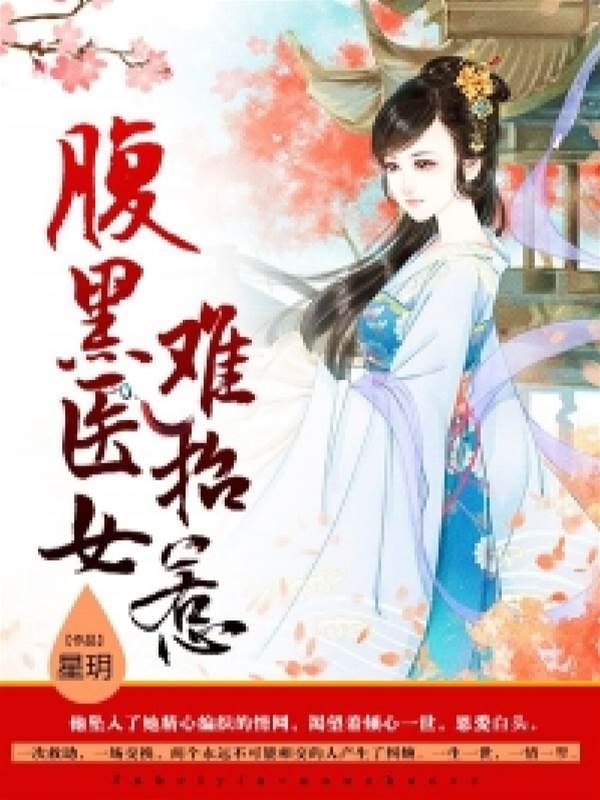
腹黑醫女難招惹
她本是現代世界的醫學天才,一場意外將她帶至異世,變成了位“名醫圣手”。 他是眾人皆羨的天之驕子,一次救助,一場交換,兩個永遠不可能相交的人產生了糾纏。 一生一世,一情一孼。 他墜入了她精心編織的情網,渴望著傾心一世,恩愛白頭。 已變身高手的某女卻一聲冷哼,“先追得上我再說!”
42.7萬字8 11668 -
完結492 章

皇室百年得龍鳳胎,王妃被團寵了
她是鬼麵毒醫,一朝穿成將軍府不受寵的真千金,皇家宴會被算計跟戰神王爺捉奸在床,皇帝下旨賜婚。新婚夜她強勢染指王爺,被發現不是清白之身,更被曝出有私生女。全京城都在等著看她笑話,結果南嬌生下百年難遇的龍鳳胎,皇室放話往死裏寵!白蓮花酸溜溜,她是草包,晉王遲早休妻。南嬌搖身一變成了醫毒雙絕的醫聖,狠狠打了渣渣們的臉。某王爺寵溺地將人抱在懷裏:“本王隻做娘子的裙下臣。”
85.5萬字8.18 1659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