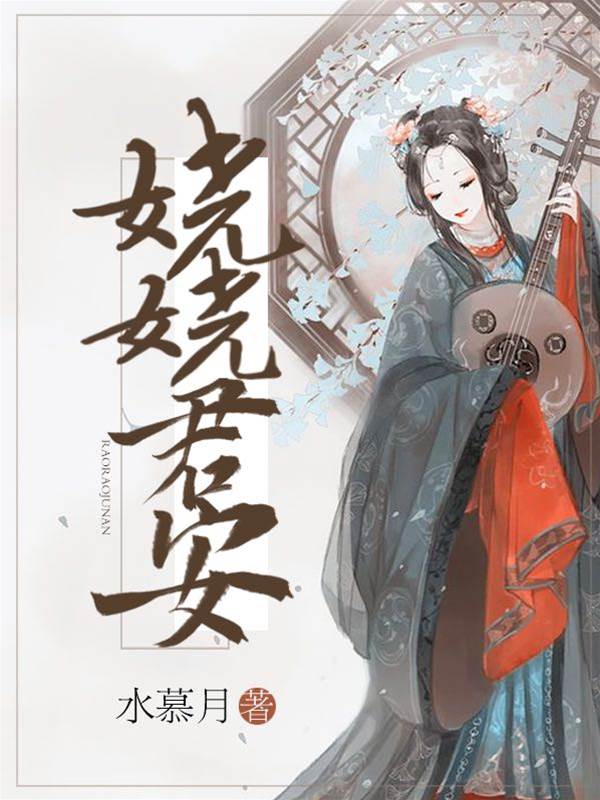《失憶后被權臣嬌養了》 第40章 回家
此次姜鶯出門依舊戴著帷帽, 剛剛到百安樓雅座尚未來得及下。這回出門,與姚景謙兄妹二人先在城中逛了逛,不知不覺逛至百安樓便上來用晚膳。
百安樓菜極好, 姜鶯和夫君來過一兩次。將喜歡吃的一一報上名,又問:“表哥表妹不若再看看, 我不知你們喜歡吃什麼。”
姚景謙對吃的不講究,姚清淑更是好說話。三人環桌而坐, 姜鶯坐在中間,姚景謙眉目含笑:“表妹點什麼我就吃什麼。”
他這麼一說姜鶯倒不好意思起來,他們是客, 竟還遷就自己。不過這種發自心的真誠是演不出來的, 姜鶯不免對二人生出幾分親近。
菜上至一半, 姚清淑拉住姜鶯手親昵道:“表姐我們許久不見, 不如今晚你和我睡?我給你說說以前的事。”
姜鶯有點猶豫。其實對過去的事很好奇, 但又舍不得夫君。
姚景謙自然知道擔心什麼,不過他遲早要帶走姜鶯,還是想多些時間相。況且以前他不在臨安便罷了, 姜鶯一個姑娘, 一直呆在王府不合適。
“表妹以前和小淑關系極好,經常躲一個被窩說悄悄話呢。讓表妹把以前的事說與你聽,想必對病癥也有好。”
他聲音溫和娓娓道來, 完全讓人招架不住。其實到這里姜鶯已經搖了,姚景謙又乘勝追擊:“此番來臨安我們住在廣福客棧, 那里臨近江邊,聽說今晚放煙花,表妹不想去看看?”
一聽煙花,姜鶯臉上閃過一驚喜。這個年紀的姑娘都喜歡煙花, 道:“那一會我先回府問問夫君。”
王舒珩在隔壁一聽姜鶯聲音就出來了,不過偶遇守在門口的田七雄,了解事來龍去脈這才耽擱了時間。
Advertisement
出乎他的意料,不過昨日才接到姚家書信,姚景謙今日就到了。王舒珩瞪一眼田七雄,似責怪,又似生氣。
他大步來到姜鶯后,故作咳嗽,道:“要問我什麼?”
悉的聲音乍起,姜鶯轉,意外了聲:“夫君?夫君怎麼在這兒?”
王舒珩沒有立刻回答,目落在姚景謙上。
明晃晃的線襯得他眸子鋒利,猶如帶的刀刃,神雖淡然,但察人心似乎一眼就將人看穿。
說起來,他與姚景謙還有些淵源。年初回京他去看明海濟,說起朝中文臣,明海濟還說過翰林院新來的姚編修天賦一般但為人勤勉,努力幾年大有可為。
當時,王舒珩便留意過此人。姚景謙,泉州州同嫡長子,子溫和舌綻蓮花,能被明海濟肯定,學問人品肯定不差。
他明目張膽打量的時候,姚景謙并沒有退卻,而是抬頭無畏地迎上王舒珩眼睛。二人視線隔空鋒,暗中火花旁人自是不知。
還是姚景謙起朝他拜了拜,說:“久仰沅王大名,聽聞殿下帶兵連收北疆南境,護我大梁安寧,今日相遇實乃我之幸。”說罷又招呼妹妹姚清淑起,“小淑,來見過沅王。”
王舒珩神雖寡淡,但還算客氣,回道:“幸會。”
寒暄完,誰也沒提姜鶯的事,空氣中涌著莫名緒,還是姜鶯打破沉默:“夫君,你怎麼到這里來了?”
這聲夫君讓王舒珩很是用,他抓了抓姜鶯小手,說:“和人有約,沒想到會在這兒上你。”
話音剛落,隔壁明泓明萱兄妹也來了,明泓正奇怪何事讓王舒珩離開那麼久,一見對方抓住姑娘的手,第一反應是自己眼瞎了。
Advertisement
明泓再三確認,到這里氣氛已經很尷尬了。不明泓,明萱差點也以為自己看錯了。
這姑娘拐著彎想法子來臨安,就想見見王舒珩。來之前便想著,雖然沅王不喜歡,但也不喜歡其他子,因為祖父的關系兩家親近,自己主些總該有機會的。
長這麼大,明萱就沒見誰與王舒珩如此親近過,當即呼吸一滯,袖子底下手指絞在一塊。
偏偏姜鶯一無所知,指著明泓明萱問:“夫君,他們是誰?”
夫君?明家兄妹皆是一愣,卻見王舒珩似是已經習慣了般,介紹說:“汴京明家三公子,五姑娘,是王府故。”
姜鶯哦一聲,正打算上前招呼一聲,才反應過來自己還帶著帷帽。不等姚景謙制止,已經摘下,甜甜沖眾人一笑。
那一笑如春,燦爛至極,晃得人移不開眼。即便在汴京見過數不清高門貴的明萱也必須承認,這位疑似沅王妃的姑娘確實生的好看。
既然遇上,就沒有分開用晚膳的道理,兩撥人只得在一張桌子前坐下。
不過姜鶯周圍有姚景謙和姚清淑,兩人好似左右護法挨著姜鶯,王舒珩只得坐到姜鶯對面,明泓和明萱坐在他側。
落座后相對無言,子之間對敵的覺是相通的。姜鶯目一直有意無意打量明萱的時候,明萱也在打量,總覺得這個明萱的姑娘距離夫君也太近了。
姜鶯心暗自泛酸,菜上齊了。原本出門心好好的,姜鶯這會莫名不太開心。
隨便吃著面前的菜,姚景謙忽然湊近,小聲說:“我記得出門時鶯鶯說,這頓你請?”
姜鶯一怔,點頭:“那當然,絕不讓表哥表妹花錢。”
Advertisement
“那你再不多吃些,可就便宜那姑娘了。”姚景謙眼神意有所指,姜鶯當即明白過來。
一想到夫君和明萱之前認識,姜鶯心里就不是滋味。但既然請客,那自然要多吃些,更何況姜鶯確實了。想到此,姜鶯瞬間覺得胃口好了許多。
菜品都是姜鶯點的,大快朵頤的時候,沒注意王舒珩眸漸深,盯著姚景謙,似乎要將對方盯出一個窟窿。
姚景謙并不畏懼,反而朝他微微一笑,繼續低頭和姜鶯說著什麼。
兩人絮絮低語,完全不關心旁人。王舒珩面上一如既往的平靜,手指若無其事地折著兩只木箸。不知怎的,只聽咔嚓一聲,木箸竟斷了兩截。
這清脆的一聲很是突兀,惹得人人抬頭來。姜鶯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懵懂道:“怎麼了,夫君?”
乖巧依舊,王舒珩也不好說什麼,道:“無事。”
姚景謙將一切看在眼里,氣定神閑說:“沒什麼事,鶯鶯快點吃,醉花鴨涼了味道不好。”說罷招手喚來小廝,“給殿下換一雙木箸,要牢固一點的。”
經過此番,飯桌上火藥味似乎更濃。不多時小廝重新送上一副銀箸,王舒珩好不容易下滿心火氣。
偏偏這時,姚景謙看窗外似乎有什麼好玩的,正要說給姜鶯聽,王舒珩率先住他,慢條斯理道:“年初回京早聽聞姚修編名,本王敬你一杯。”
百安樓的酒烈,王舒珩常年行軍自是不在話下,姚景謙一介文臣便有些吃不消了。一杯下肚面頰泛紅,反觀王舒珩倒跟沒事人一樣。
他接著說:“姚修編年方二十,可訂親了?”
兩人互相試探,姚景謙也不虛,一眼姜鶯,遲疑道:“應該快了。”
Advertisement
側姜鶯已然沉醉在滿桌珍饈,聞言抬頭,說:“那我要有表嫂了?表哥訂親的人是誰?”
姚清淑的臉不是太好,倒是姚景謙微微一愣,又恢復笑意,故作神:“到時鶯鶯便知道了。”
王舒珩哪會給人得意的機會,趁熱打鐵道:“表哥的喜酒莫要忘了王府,到時本王一定帶鶯鶯前往慶賀。”
不得不說,王舒珩這聲“表哥”殺傷力極大。話音才落,姚景謙神就繃不住了,姚清淑直接拉臉,倒是一無所知的明氏兄妹茫然。
沅王與疑似王妃的表哥關系似乎不怎麼好。
其實明氏兄妹有一肚子的疑問,前不久圣上在汴京還大張旗鼓地挑選沅王妃,怎麼這會王妃就定下了。也不曾聽聞沅王府三書六禮,明正娶哪家姑娘。
不過即便問題再多,明氏兄妹這會也不敢問,因為桌上氣氛實在詭異,儼然不是問這些的時候。
姜鶯對夫君和表哥的鋒毫不知,百安樓東西好吃又確實了,幾乎每樣菜都嘗過一筷子,只有那道乾果四品還沒。那道菜距離姜鶯太遠,今兒人多不好起去夾。
正猶豫的時候,只見王舒珩不聲地抬起那盤乾果四品放到姜鶯跟前,說:“聽聞姚編修喜好書法,百安樓恰好有一副名作,不如隨本王去品一品?”
“姚某正有此意。”
王舒珩和姚景謙先后出了雅座,姜鶯便坐不住了。早就看這位明家五姑娘不對勁,方才看他的夫君八次。明萱自以為無人發現,實際上姜鶯眼毒著呢。
不過也不能明目張膽地問人家你是不是喜歡我的夫君,只得胳膊肘姚清淑,小聲道:“表妹,你覺不覺得那位明姑娘想勾我的夫君?”
自從白沙鎮回來,姜鶯學到不東西,這子勾人便是其中一項。
姚清淑看哥哥隨沅王出門都快急死了,對方位高權重,爵不知姚景謙多等級,怕哥哥會吃虧。更何況,聽姜鶯一口一個夫君著,姚清淑心神不寧。
不知如何解釋,來臨安的路上姚景謙便待了,貿然告訴姜鶯沅王非的夫君,只怕會引起雙方信任崩塌,須得徐徐圖之,最好由沅王本人告訴姜鶯這件事。
另一頭,王舒珩和姚景謙出了雅座,來到后院一亭榭。此安靜,正是說話的地方。
四下無人,姚景謙也不客氣了,恭敬一拜,道:“這段時日承蒙殿下照顧鶯鶯,某既已到臨安,姜府的事也不該再麻煩殿下。煩請殿下與鶯鶯說明事實真相,某激不盡。”
麻煩?
王舒珩細細品這兩個字。剛開始他確實覺得姜鶯麻煩,哭,不就撒,還黏人。以至于一開始,他為怎麼和姜鶯相苦惱了很長一段時間。
但不知何時,他喜歡被姜鶯麻煩。真誠熱烈,看他的時候眼里有,親近的時候大膽青,王舒珩十分確定,他不想放姜鶯走。
如此,他曬笑,明知故問:“真相?什麼真相?鶯鶯在王府好好的,姚修編可帶不走。”
姚景謙一聽,心知事麻煩了。這是他一路最擔心的,沅王不放人,他還能搶不?
“殿下,某與鶯鶯青梅竹馬自小互生愫,鶯鶯純質,眼下雖失了記憶但某可以確定,對殿下并無兒之。不過傷,才屢屢冒犯殿下。”
此時明月初升,掛在樹梢格外明亮。王舒珩負手而立,逐字逐句道:“鶯鶯純質,姚修編喜歡,本王也喜歡。姚修編并非鶯鶯肚中蛔蟲,也無看人心之眼,如何知道對本王不存男之?”
二人皆是進士出,論口才不分上下。朝堂外,王舒珩其實很與人爭辯什麼,他喜歡用行說話。頭一次與人爭辯,竟是為了姜鶯。
幾番對峙,姚景謙有些急了,拔高聲音道:“殿下莫非忘了您與姜府的關系?說起來,殿下算是鶯鶯的姐夫,若執意如此,殿下居高位自然無所畏懼,就沒想過世人如何議論鶯鶯,如何看待姜府嗎?”
“姐夫?”王舒珩哼笑一聲,“本王與姜芷從來沒有親,何來姐夫一說?本王年方二十有四,家中無妻無妾,平數十萬敵寇都不在話下,還護不住一個姜鶯?”
“姚修編,念你與鶯鶯誼本王不為難,也不怕夸下海口,等料理完姜府一事,自會八抬大轎迎過門。再冥頑不靈,休怪本王無。”
這些話姚景謙只覺字字千斤,劈頭蓋臉砸下,差點讓姚景謙找不著北。
猜你喜歡
-
完結1723 章
異瞳狂妃:邪帝,太兇猛!
她是21世紀第一殺手,一雙異瞳,傲視天穹。 一朝穿越,淪為將軍府廢材傻女,當這雙絕世異瞳在這世間重新睜開,風雲變幻,乾坤顛覆,天命逆改! 她手撕渣男,腳踩白蓮,坐擁神寵,掌控神器,秒天炸地,走上巔峰! 隻是…一個不小心,被一隻傲嬌又毒舌的妖孽纏上。 日日虐心(腹黑),夜夜虐身(強寵),虐完還要求負責? 做夢!
152.1萬字8 6143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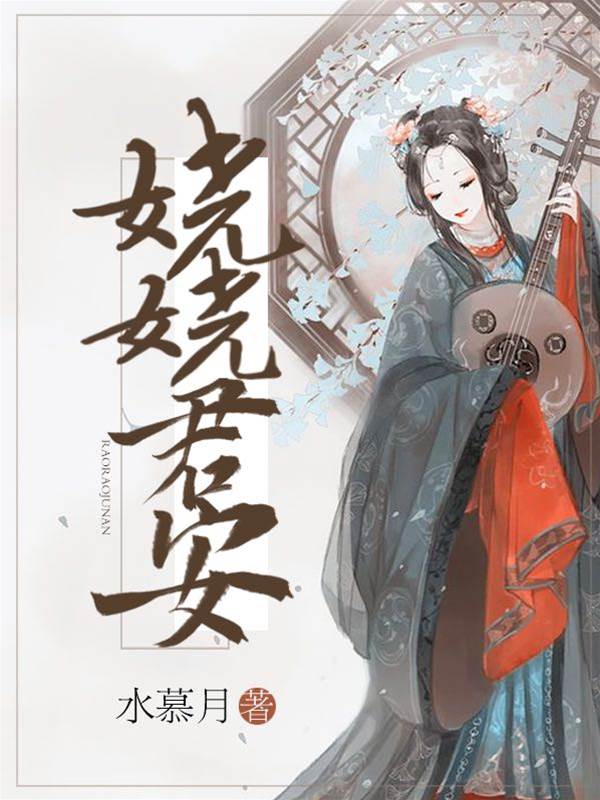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001 -
完結368 章

誰敢打擾我搞事業
穿越而來的容凝一睜眼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沖喜的新媳婦婆家花十文錢買了她回來沖喜,順便做牛做馬誰曾想,這喜沖的太大病入膏肓的新郎官連夜從床上爬起來跑了婆家要退錢,娘家不退錢容凝看著自己像踢皮球一般被踢來踢去恨得牙癢癢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容凝咬咬牙一個人去討生活好不容易混的風生水起,那個連夜跑了的混賬竟然回來了還想和她談談情,說說愛容凝豎了個中指「滾!老娘現在對男人沒興趣,只想搞事業!」某男人不知廉恥的抱著她:「真巧,我小名就叫事業!」
38.5萬字8.18 144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