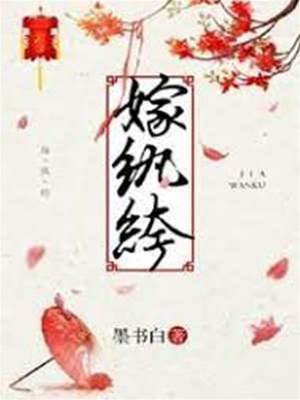《側妃上位記》 第61章 名冊
“茯苓姑姑這是作甚?”
茯苓遞給的不是旁,而是一份名單。
——貴妃這麼多年在宮中積攢的人脈。
周韞立即站起來,繃著子看向茯苓,心中倏地竄出一抹不安?
茯苓姑姑為何此時將這份名單給?
尚在賢王府,說句不好聽的,這份名單對此時的有用,卻也沒那麼大的用。
茯苓只是抿,出一抹笑:
“姑娘不必擔心,茯苓還有些事尚未做,不會去做傻事的。”
周韞聞言,卻沒覺得毫放松,甚至于,心中狠狠一沉。
尚有事未做?
是何事?
姑姑究竟安排了什麼?
想問,可姑姑沒和說,必定是覺得知曉了,對沒甚好。
周韞堪堪啟,就被茯苓打斷:
“姑娘莫要問了,到時,姑娘總會知曉的。”
茯苓徐徐低頭,視線落在周韞小腹上,眸稍。
是周府的家生子,自起就在伺候娘娘,一生無子,周韞常宮,待周韞也如待子般。
如今周韞有孕,娘娘臨終前,最惋惜的,就是未曾看著姑娘的孩子降世。
堪堪聲:
“姑娘,您現如今,最重要的還是保重子。”
只要姑娘無事,才對得起娘娘的一番苦心啊!
周韞聽出話音中的意,倏地掐手心,心中涌上一苦悶,抬手了把眼淚,深深呼出一口氣:“茯苓姑姑,待宮中事了,你同我回王府吧?”
茯苓一怔,在周韞期待的視線下,遂后,終究是搖了搖頭。
待完娘娘代的事后,如何還曾伺候姑娘?
退了一步,跪在地上,埋頭,說:
“姑娘,奴婢伺候娘娘一輩子,也累了,待事后……”
只想去陪娘娘。
Advertisement
習慣了如此。
改不了了。
話音未盡,可周韞卻知曉想要說的是何話。
倏地,周韞眸子有些紅,可茯苓臉平靜,明擺著心意已決,絕非周韞一言一語可以搖。
茯苓抬眸看了姑娘一眼,忽地想起那日太子領明德進宮時,娘娘和說的話。
……
明德開了藥方后,就被太子領走,夜甚濃郁,雎椒殿的燭燈明明暗暗。
宮人端著藥,掀開簾子進殿,茯苓接過,打發宮人離開。
在遞給貴妃時,看向榻上的子,遲疑:
“娘娘,這明德當真可信嗎?”
明德雖說可以治好娘娘,但他是太子領進宮的人,如何可信?
珍貴妃掩,抑著咳嗽了一聲,虛弱地笑了笑,接過藥碗:“可信與不可信又如何,總歸這藥,的確會本宮好上些許。”
低斂著眸子,遮住那輕諷。
明德可信?
可以治好?
珍貴妃比任何人都知曉自己子是何狀況。
太子想要作甚,比何人都要清楚。
茯苓狐疑地看向娘娘,真的會如娘娘所說那般嗎?
珍貴妃闔眸,端過藥碗一飲而盡。
稍頓,將藥碗遞給茯苓,才似有若無地輕輕呢喃了一聲:“明德……”
閉了閉眼睛,明德忽然在京中名聲大振,背后必定有推手。
至于推手是何人,如今明眼人皆知。
可太子勢大,對、對韞兒來說,卻非是何好事。
自將韞兒嫁賢王府,就注定了和賢王府是站在一條船的人了。
圣上雖不信鬼神一說,更不信有人神通廣大,能預知未來。
可這人心,卻非一不變。
若明德再預知了幾件事,難免會圣上心生搖。
珍貴妃不愿去賭,自要早早將明德除掉。
Advertisement
可如何除呢?
一個后妃,如何不聲地手前朝之事?
之前沒有辦法,可如今,太子卻是將明德帶到眼前,親自送了一個機會。
殿寂靜良久,好半晌,珍貴妃似嘆了一口氣,抬手了自己的臉頰,眸中有些恍惚。
茯苓聽見靜,抬起頭,見到這幕,倏地想起什麼,臉一白。
手中的藥碗倏然落地,砰一聲皆是碎片。
驚恐地看著地上藥的殘,紅著眼拼命搖頭,堪堪出聲:“……娘娘?……您告訴奴婢,不是奴婢想的那般——”
倏地噤聲,因為貴妃闔上了眸子。
茯苓頹廢地后退了一步。
是了。
太子怎會那般好心?
東宮書房中那一堵書架后,藏了多不堪被人知曉的?
他覬覦了那麼多年……
珍貴妃遂頓,對著茯苓無聲地搖了搖頭。
“這些事,莫要對韞兒提起了。”
“看似天不怕地不怕,其實膽子甚小,那年從東宮跑出來,愣是做了一個月的噩夢。”
“如今,有孕,經不得緒過分波。”
說話輕輕的,似乎沒甚大不了的,只一心為了周韞考慮。
茯苓卻氣極,眸子殷紅,倏地跪在貴妃榻前,哭著求:“娘娘!您別這樣……”
“若姑娘知曉您這般,姑娘心中必定愧疚不安,奴婢求您了!”
珍貴妃卻閉著眼,只咳嗽著艱難地說了一句:
“本、宮大限將至,總該做些什麼……”
太子既將手進了雎椒殿,自是要付出些東西!
當年,他生母都不敢對這般張狂。
懶得去管圣上這些子嗣,倒太子這些年越發輕狂了。
珍貴妃了手心。
茯苓跪在旁邊,痛哭不止。
Advertisement
知曉,娘娘待太子,一直些許愧疚。
不為其他,當年銘王戰死沙場,先皇后雖不堪重病倒,其實卻無大礙。
那時,娘娘剛進宮,圣上早就傾心娘娘,娘娘遂一進宮,就是四妃之一。
當年圣上和娘娘誼正濃,遂娘娘進宮后,先皇后的子就越發不堪,不到半年,就無故病逝了。
先皇后一去,圣上就封娘娘為后。
可當時朝中尚未安定,又有銘王府殘余勢力,和皇后母族在其中阻撓。
足足數月后,圣上終是退了一步。
娘娘自此為皇貴妃,圣上又特賜“珍”為封號。
因此事,娘娘心中一直有狐疑,待太子也多了些許愧疚。
若非后來娘娘小產,娘娘又何至于變得如此?
許久,珍貴妃呵斥住茯苓:
“別哭了。”
有甚好哭的。
總歸,這子早就破敗不堪。
抑地咳著,眸子甚亮,盯著茯苓,只堪堪艱難說了一句話:“你記住……”
話盡,茯苓堪堪抬首,眸子中盡是呆滯。
……
茯苓退出去,周韞著那份名單,眸明明暗暗,須臾,只覺甚是疲乏。
片刻后,時春推門進來,臉些許不好:
“主子,剛宮人送來消息,孟昭儀王妃在秋涼宮留宿。”
周韞倏地睜開眸子。
孟昭儀和莊宜穗?
這二人何時牽扯到了一起?
周韞至今還記得,年宴時,孟昭儀諷刺莊宜穗的那句話。
如今不過一月有余,莊宜穗竟能忘了那時的難堪?
周韞手心,咬聲:
“究竟要作甚?”
輕著小腹,心中未必不明白莊宜穗的目的。
周韞余忽地瞥見手邊的名冊,眸子中掠過一狠。
是們先人太甚!
Advertisement
許久,周韞陷思忖,須臾后,招手時秋走近,附耳低語了幾句。
若非必要,不想和莊宜穗對上。
如今,朝中形不穩,王爺尚需要莊府助力。
和莊宜穗相識太久。
那些世家子中,有這般蠢的子了。
雖不喜莊宜穗,但也不得不承認,讓莊宜穗現如今占著王妃的位置,總比旁人占著要好。
可這一切的前提是,莊宜穗不來招惹。
翌日,周韞早早醒來。
這些日子,皆未休息好,臉上常常泛著白。
周韞剛披上大氅走出偏殿,迎面就撞見了莊宜穗,和其后的秋時。
掐手心,對這二人厭煩到極點。
周韞被扶著走近,沒行禮,輕瞇了眸子,問:
“今日姐姐倒是來得早。”
莊宜穗稍一頓,才說:“昨日本妃子些許不適,幸有母妃留宿,今日才得以來得這般早。”
周韞心中輕嗤。
什麼子不適?不過留宿宮中的一個借口罷了。
但,周韞心中也不解,莊宜穗為何要留在宮中?
在宮中并無人脈,又能有何手段對付自己?
周韞沒再和說話,直接轉進了正殿。
在其后,秋時眸暗了暗。
明明站在莊宜穗旁邊,不信周韞沒看見,可偏生如此,周韞連搭理一句都沒有,仿若眼中本沒有一般。
不聲地收回視線,貴妃已去,周韞倒是毫不曾收斂。
不過這般也好。
有貴妃護著,這般子無甚,可如今沒了貴妃,還依舊這般……呵!
周韞走后,秋時和莊宜穗四周安靜了一瞬。
秋時才斂眸,輕聲說了一句:
“姐姐,機會擺在這里,做與不做,且皆看姐姐如何選擇了。”
莊宜穗眸孔一,些許猶豫閃過。
這時,雎椒殿走近一眾妃嬪,其中一位宮裝子看見這邊,停了下來。
秋時和莊宜穗說了一句,就朝子走去。
莊宜穗覷了一眼,收回視線,后的氿雅低聲說:“這麗昭義待側妃倒是親近。”
麗昭義是側妃的親姨母。
莊宜穗眸子中閃過輕諷,所謂親近,不過是如今秋時為賢王側妃,兩人利益相同、互幫互助罷了。
氿雅只說這一句,就輕聲催促:
“主子,側妃說得有理,如今側妃一心撲在貴妃去世上,傷心之余必定分不出旁的心思,張崇等人也不在側妃邊護著,想要對側妃下手,此時是最好的時機!”
“而且,就算事跡敗,不是還有側妃和……”稍頓,才低聲吐出最后幾個字:“太子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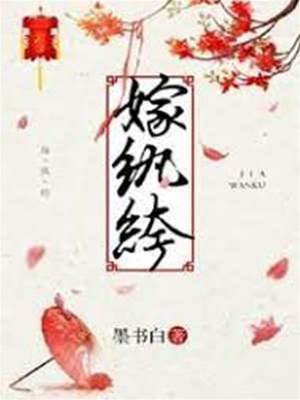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689 -
完結375 章

寵妃有道:戰神王爺不好惹
別人穿越都是王爺皇子寵上天,打臉虐渣看心情。 她卻因為一張“破紙”被人馬不停蹄的追殺! WTF? 好吧,命衰不要緊,抱個金主,云雪瑤相信她一樣能走上人生巔峰! 不想竟遇上了滿腹陰詭的冷酷王爺! 云雪瑤老天爺,我只想要美少年!
88.5萬字8 16407 -
完結396 章

嫁給反派后天天想和離
穿成惡毒女配之后,姜翎為了不被反派相公虐殺,出現慘案,開始走上了一條逆襲之路。相公有病?沒事,她藥理在心,技術在身,治病救人不在話下。家里貧窮?沒事,她廚藝高超,開鋪子,賺銀子,生活美滋滋。姜翎看著自己的小金庫開始籌謀跑路,這大反派可不好伺候。誰知?“娘子,為夫最近身子有些虛,寫不了休書。”不是說好的?耍詐!!!秦子墨:進了我家的門,還想跑,休想。
71.2萬字8 180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