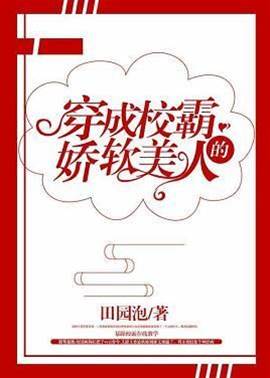《我愛你,我裝的》 第54章 我愛你 [VIP]
寧思音醒得晚, 下樓時和正上樓的蔣昭野見。蔣昭野對也不知到底是敬還是不敬,往旁邊讓開路,手卻往兜里一塞, 酷酷地站著, 并不同打招呼。
寧思音迷迷瞪瞪, 沒注意他沒問好,習慣回了句:“早, 乖孫。”
蔣昭野:“……”
蔣昭野可能天生跟寧思音犯沖,每回見都得噎一肚子氣, 眼不見為凈他干脆躲了出去。他覺得自己現在多了,已經不屑于跟置那些無聊的氣。
但自從上回寧思音被拆穿是“假冒”的, 再看就說不出的古怪。蔣昭野搞不懂這古怪源自何,這會站在幾層臺階下面抬頭,背著走廊的燈,松松懶懶的樣子和側頸上的紅痕一塊撞進他眼睛里。蔣昭野忽然覺出那不是滋味的滋味。
直到這時他才遲鈍地醒悟過來,這個人從一開始就沒想跟他結婚,什麼狗屁的爭風吃醋、委曲求全, 演那些戲不是為了嫁給他, 全都是為了攪黃婚約好不嫁給他。
怪不得拿花瓶砸他的時候下手那麼毒……虧他還因為下藥的事對有點疚。
靠!
他心里百轉千回,寧思音打著呵欠慢悠悠從他旁邊走了下去。
蔣昭野一句話沒跟說, 卻莫名又憋一肚子氣。
西偏廳的玻璃窗正對著薔薇花園,下午避,蔣措最常在那里喝茶,藤椅旁安置了狗狗用涼席和鸚鵡站架。
旺仔和鐵蛋每天像左右兩個護法, 寸步不離守著他。寧思音吃了飯正要過去, 上蔣明誠。
他剛祭拜過回來, 穿一黑, 領子開著幾顆扣子,合上車門走進來。
“睡醒了?”
“不好意思,這幾天工作太多沒休息好,早上睡過頭了。”寧思音盡量讓自己的解釋聽起來嚴肅正經,畢竟睡過頭的理由太放浪。
Advertisement
蔣明誠倒也沒拆穿,停在面前,將話題岔開。
“聽說你把嚴秉堅請回來了。”
“你消息蠻靈通啊。”
“見個朋友,聊了幾句。現在大家都在夸你寬宏豁達,任人唯賢。你每一次的選擇,總是讓我很意外。”
寧思音不確定是不是自己現在太多疑,覺得他話里有話。
“抬舉我了。這是我爺爺的心愿,我知道看在他的份上不計較。”
蔣明誠看片刻,目很耐人尋味,“有件事想跟你確認一下。”
不清他路數,寧思音沒作聲。蔣明誠忽地向走近,寧思音微微繃,他停在一個超過安全距離的位置,聲音低下去,從遠看起來像兩人在語。
“我聽聞,你和嚴智之間,不止他陷害你那麼簡單。你在知道自己的世之前,曾經和他做過一筆易,‘假扮寧思音’,對嗎?”
寧思音抬起眼睛,出一個大大方方的笑:“這個知道的人不。你想確認什麼?”
他意味不明一笑:“既然是角扮演,沒道理把自己賠進去。你當時選擇我三叔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蔣明誠知道自己問對了關鍵,他看到寧思音眼里的溫度,在這個問題之后一點一點消失。
盡管那個模板似的笑容依然掛在角,盈盈可人。
眼前這個人,是蔣家看起來最好相與的人,永遠紳士風度,永遠如沐春風。
但寧思音沒忘,表象之下他的心思多深沉,只為了制造機會,挑選送一只天生弱難養活的狗。
放在宮斗劇中,他可能是安陵容的升級版,有著沈眉莊式最讓你不設防的溫,和藏在細微之防不勝防的險心機。
寧思音不喜歡兩面三刀、深不可測的人。這種人讓覺得可怕。
Advertisement
還是蔣措好。
“演戲當然要找個好看的男主角。這是個看臉的社會。”
這個理由似乎沒能搪塞蔣明誠。他的笑容愈發有深意,又順勢拋出一個最致命的問題。
“那麼戲已經演完了,你打算什麼時候謝幕?”
寧思音愣住。
正在這時,啪——
偏廳里清脆一聲。跟著鐵蛋扯嗓門的尖:“救駕!救駕!”
寧思音立刻往西偏廳趕去:“怎麼了?”
推開門,卻見蔣措好端端坐在藤椅上,只是腳邊一攤碎片。
“沒事。”他慢悠悠道,“不小心打翻了杯子。”
寧思音放下心,傭人進來收拾,一邊把他從椅子上拉起來。“你小心,別又劃傷了。”
蔣措順從地被拉到后,仿佛真有那麼弱,一個茶杯的碎片都能傷到他。
等傭人收拾完,驚的鐵蛋逃難回來,被寧思音捉住彈了一下腦袋。
“你怎麼這麼喜歡一驚一乍。差點被你嚇死。”
蔣措瞥了眼在手里力掙扎還是被措了的鸚鵡,淡然收回視線。
可憐鐵蛋的知識面涉獵還不夠廣,無法為自己辯駁。
蔣昭野回來一趟便要走,被蔣伯堯耳提面命教訓一通,讓他多到蔣乾州跟前盡孝。蔣昭野被強制留在家里,跟蔣明誠一道被迫了別人秀恩的觀眾。
寧思音和蔣措平時并不膩乎,但小夫妻新婚將滿一年,即便不有意秀,在人前自有一種逐漸同步的默契,和誰都不進去的空間。
公司有嚴秉堅坐鎮,寧思音的擔子輕了,在家待的時間便多了。兩人偶爾一起遛狗,偶爾去花園采摘鮮花,偶爾一起坐在偏廳喝茶、下寧思音怎麼都贏不了的五子棋。
全家的傭人都說,三爺跟三可好了,現在三爺眼里只有三。
Advertisement
蔣昭野越看越窩火。
以前寧思音“喜歡”他的時候,他看見就煩,打死也不娶。現在知道寧思音本就不喜歡他,不愿意嫁給他,他心里又不舒坦了。
最近他爹又總找他麻煩,非要他進公司鍛煉,蔣昭野對公司一點興趣都沒有,每天被著做他不喜歡的事。
可謂煩上加煩。
這天晚上朋友喊他出去喝酒,他換了服剛走到門口,被蔣伯堯撞上,臭罵一通,他滾回家老實待著。
蔣昭野郁悶死了,拎了幾瓶酒去蔣明誠屋里找他四哥喝酒。
煩惱最適合下酒,很快蔣昭野就醉了,什麼心事都竹筒倒豆子似的倒給了蔣明誠。
“得不到的才會。當初是誰寧愿跟全世界作對,也誓死不娶。現在后悔了?”
蔣昭野悶著頭,甕聲甕氣地說:“誰后悔了。我就是看不慣!這個人里沒一句真話,以前還在我面前哭……”嘰里咕嚕半晌,不小心說出心聲。“我哪兒比三爺爺差?跟我取消婚約改嫁三爺爺,還讓我,我他媽不要面子嗎?”
“你真喜歡?”
蔣昭野一下炸了:“誰喜歡!我才不喜歡!”
臺有風,他醉眼昏花,沒看見蔣明誠臉上的深。
蔣明誠拍了下他的頭,狀似安。
“戲還沒唱完。別灰心,你還有機會。”
傍晚,寧思音正跟二喝茶,從玻璃瞧見蔣伯堯跟蔣曜征站在院子里。隔得遠,聽不見兩人聊的什麼,但應該不是什麼愉快的事,蔣伯堯臉不甚好看,最后拂袖走了。
寧思音正瞧熱鬧,旁邊二聽不出什麼緒地說:“大哥想提曜征上去,去年就提過,被你二哥攔著沒。現在你二哥出事,他就又了心思。”
Advertisement
主聊起,寧思音不介意多問兩句,也好奇。
“為什麼?”
“鄭家在燕城背景深厚,這些年私底下可是幫了他不。他想借鄭家的勢,鄭家想扶持自己的婿,可不一拍即合。”
蔣曜征有個強大的岳家,聽說近幾年呼聲很高,逐漸有與蔣伯堯分庭抗禮之勢。但蔣伯堯畢竟是大房長子,名正言順,幾乎是所有人默認的繼承人。雖然之前在撮合跟蔣昭野的事上,手段不太流,但確實是個手腕厲害的生意人,論能力,夠格接蔣乾州的班。
蔣乾州要想越過他提拔外孫,他肯定不肯。
“曜征看起來不像是爭權奪利的人。”
據寧思音所知,蔣曜征是家里的老大,小的時候蔣伯堯很疼他,舅甥之間有很深的。蔣曜征平日看起來對這個舅舅也很敬重。
二意味不明地輕哼:“你來蔣家這麼久,還沒看明白嗎,人不會把野心寫在臉上。曜征背后有他媽,還有鄭家支持,你以為明誠在這個時候回來,是為了什麼。”
寧思音挑眉。
只能說,豪門族爭起家產來,親父子也未必信得過。
他們家人丁,反倒避免了這種六親反目的窩里斗。
蔣家家主之位雖說已經是蔣乾州囊中之,但老爺子畢竟還活著。按理說,蔣伯堯跟蔣曜征就算要爭,也不急于這一時。別說蔣乾州距離繼位,到底還差最后一步,就算真繼位了,他年過七旬卻未聽說有什麼大病,按照蔣家這個長壽基因,能像老爺子一樣再活二十年也未必。
但不曉得為什麼,兩人之間好似已到劍拔弩張的地步,蔣曜征迫不及待拉攏人心的消息,連寧思音都有所耳聞。
那天中午吃飯時,湯總監不知從哪個狐朋狗友那里聽來的小道消息,一坐下便問寧思音:“蔣家出事了。”
寧思音跟嚴秉堅同時抬頭。
“什麼事?”
經歷過嚴智謀財、二爺被捕,現在發生什麼事,寧思音都不覺得離奇。
第一個想到蔣措,那個懶烏還在家休養,家里要是出什麼事,他……
“你大哥……誒不對,大侄子……大孫子,蔣曜征。”湯總監很有當眾八卦的自覺,聲音到鬼鬼祟祟的低,“聽說牽扯到了一樁人命案子。”
寧思音心都提起一半,聞言啪地一下落回去,給他一個自行會的白眼,“這麼會賺噱頭,你怎麼不去公關部上班。標題黨。我還以為誰上我們家里放火了。”
自己都沒發覺,如今用“我們家”來指代蔣家十分自如。
嚴秉堅看了一眼。
“那誰敢,上蔣家放火,不得滿門抄斬啊。”湯總監說,“蔣曜征的太太是鄭庭庭吧,聽說前年出了一場車禍,撞死了一個孕婦,但你們蔣家只手遮天,把這件事給蓋住了,人家丈夫四求告無門,還被蔣曜征帶人打廢了一條胳膊。人家在網上控訴求助還被刪帖,熱度,現在網友非常憤慨,看樣子是激起民怨了。”
前年?
那時寧思音還未回國,沒聽說過。
事件八存在,細節卻未必沒有經過添油加醋。別的不說,蔣曜征帶人打廢人一條胳膊?——換蔣昭野也許更可信一點。
不過現在流行網絡辦案,許多正義在現實中得不到張,經由網絡發酵、在廣大民意督促下,就有機會得到有關部門重視,求得說法。
如果真如湯總監所說,激起了民怨,一味掩蓋只會適得其反。
民眾對資本、對強權有天然的同仇敵愾,上這種事很容易被煽緒,不管最后真相如何,蔣曜征這次確實攤上麻煩了。
只顧著八卦,湯總監飯沒吃上兩口,中途又被人走,一臉痛心地說:“我的小排啊……嚴總你替我吃了吧。”
嚴秉堅對他的小排并不興趣,倒是不時看一眼寧思音,醞釀措辭。
寧思音心不在焉琢磨蔣曜征的事,沒察覺。
吃好離開餐廳,嚴秉堅走在后,等幾位員工說說笑笑拐過彎下樓,四周沒人,才出聲住。
寧思音回頭:“嗯?”
空中走廊相隔不遠便是景觀樹,繁茂枝葉遙遙過來,從頭上投下一片涼蔭。
嚴秉堅站在三步之外,停了停,說:“如果你結婚只是為了順從寧老的意愿,現在你自由了,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猜你喜歡
-
完結1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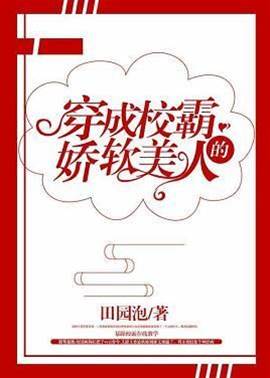
穿成大佬的嬌軟美人
作品簡介: 按照古代賢妻良母、三從四德傳統美德培養出來的小白花蘇綿綿穿越變成了一個女高中生,偶遇大佬同桌。 暴躁大佬在線教學 大佬:「你到底會什麼!」 蘇綿綿:「QAQ略,略通琴棋書畫……」 大佬:「你上的是理科班。」 —————— 剛剛穿越過來沒多久的蘇綿綿面對現代化的魔鬼教學陷入了沉思。 大佬同桌慷慨大方,「要抄不?」 從小就循規蹈矩的蘇綿綿臉紅紅的點頭,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出格表演。然後全校倒數第一抄了倒數第二的試卷。 後來,羞愧於自己成績的蘇綿綿拿著那個零蛋試卷找大佬假冒簽名。 大佬:「我有什麼好處?」 蘇綿綿拿出了自己覺得唯一擅長的東西,「我給你跳支舞吧。」 ———————— 以前,別人說起陸橫,那可真是人如其名,又狠又橫。現在,大家對其嗤之以鼻孔。 呸,不要臉的玩意。
34.1萬字8 9596 -
連載403 章

時光與你皆傾城
一場錯愛,她忍受四年牢獄之災。四年後,她浴火重生,美得淩厲,發誓要讓他百倍奉還。隨著時間推移,真相一層層析出,當初的背叛,是刻意,還是誤會?他帶給她的,到底是救贖,還是更甚的沉淪……
73.7萬字8 8598 -
完結375 章

怪他過分沉淪
傳聞,蔣蘊做了葉雋三年的金絲雀。傳聞,她十九歲就跟了葉雋,被他調教的又乖又嬌軟。傳聞,葉雋隻是拿她當替身,替的是與葉家門當戶對的白家小姐。傳聞,白小姐回來了,蔣蘊等不到色衰就愛馳了,被葉雋當街從車裏踹了出來。不過,傳聞總歸是傳聞,不能說與現實一模一樣,那是半點都不沾邊。後來,有八卦雜誌拍到葉家不可一世的大少爺,深夜酒吧買醉,哭著問路過的每一個人,“她為什麼不要我啊?”蔣蘊她是菟絲花還是曼陀羅,葉雋最清楚。誰讓他這輩子隻栽過一回,就栽在蔣蘊身上呢。【心機小尤物VS複仇路上的工具人】
70.7萬字8 28299 -
完結153 章

後腰紋身
盛傳頂級貴公子淩譽心有白月光,但從他第一眼見到慕凝開始,就被她絕美清冷的麵龐勾得心癢癢,世間女子千萬,唯有她哪都長在他的審美點上,男人的征服欲作祟,他誓將她純美下的冷漠撕碎。某日,淩譽右掌支著腦袋,睡袍半敞,慵慵懶懶側躺在床上,指尖細細臨摹著女人後腰上妖治的紋身,力度溫柔至極。他問:“凝兒,這是什麼花?”她說:“忘川彼岸花。”男人勾住她的細腰,把她禁錮在懷裏,臉埋進她的頸窩,輕聲低喃:“慕凝,凝兒……你是我的!”他的凝兒像極了一個潘多拉盒子……PS:“白月光”隻是一個小過渡,男主很愛女主。
26.7萬字8 21017 -
完結430 章

人前人後
縱使千瘡百孔,被人唾棄。
69.9萬字8.18 84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