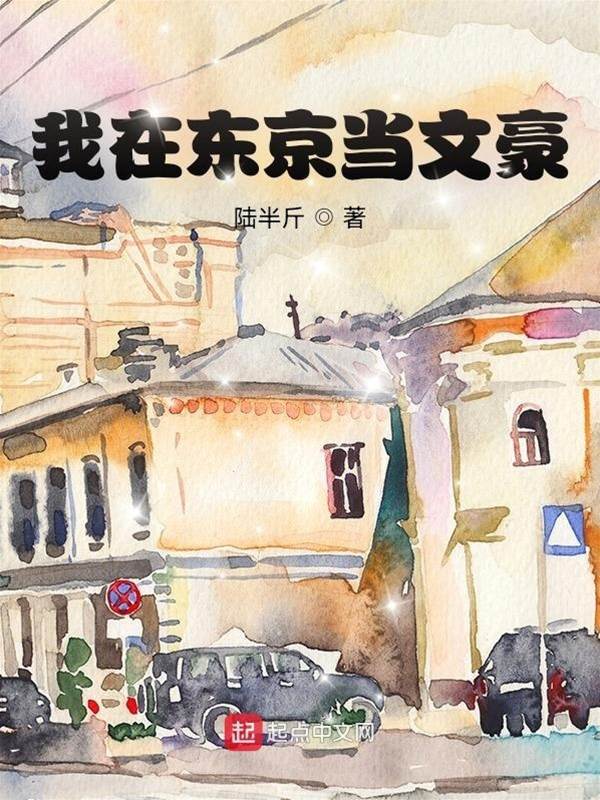《女商(大清藥丸)》 第144章
“好啦, 現在沒別人,可以哭了。”
上海水道眾多,汊綿延。在某個不太繁忙的小河道中央, 靜靜漂著一艘小船。
船艙狹小, 蘇敏直不起, 只能盤膝坐著,朝著對面, 大大方方出雙臂。
等了一會兒, 林玉嬋并沒有投懷送抱,邊帶著的笑意, 頭偏到一邊, 手里玩一垂下來的麻繩。
“說正事。”鼻音濃濃的。
的眼眶紅紅,臉上淚痕點點, 鼻尖也是紅的, 睫漉漉地墜著, 小脯一起一伏,好似剛被人欺負過的委屈樣。
蘇敏定睛凝視好一會兒, 語氣卻微微失:“已經哭過了。”
林玉嬋眼眶一酸, 卻又忍不住扯角, 帶著重鼻音, 說:“還可以再哭一次……嗚……”
一想到那死氣沉沉的空屋,墻角的石榴皮, 一下又繃不住, 順理章地讓蘇敏攬在懷里,用力呼吸他前的淡淡皂味, 平復著緒的余韻。
蘇敏取條手帕,包了食指, 慢慢給拭眼角淚痕。
在衙門口等待許久,他估時間,客氣打發走兩個被放鴿子的“友商”,場面話說過,沒什麼怨言。
隨即博雅的趙經理跑來,連聲告罪,忿忿地敘述了黃老頭的混賬事。
蘇敏心想,果然。
當初聽林玉嬋敘述的時候,他就約覺得,此人老而不穩,不會那麼配合。
不過他也沒攔著,沒料到有些人的道德底線居然那麼底。
現在說什麼也晚了。他便問起林姑娘,趙懷生卻發愣:“啊啊,不知道,也許回虹口了吧。說要告一天假。”
蘇敏簡直無語。這經理怎麼當的!一個哭唧唧小姑娘不怕路上遇麻煩?
Advertisement
人家的公司,他也不好置喙。他想,要是他贏了對賭協議,頭一件事就是把手下的兩個秀才兵都開掉。
想了想,覺得多半會來訴個苦。
于是估走去義興的路線,自己慢慢沿路尋回去。果不其然,沒走多久,迎面就來了個蔫頭耷腦的姑娘,正抹眼淚呢。
不過,并沒有像他想的那樣,上來就梨花帶雨泣不聲,他準備的一肚子哄人的話也沒派上用場。
但他察覺到,或許有一些私的話要說。于是讓上船。
---------------------------
“放開點。”蘇敏聲道,“大點聲也沒人聽見。”
林玉嬋撲哧一個笑,又耷拉眉,囔著鼻子,小聲說:“你可以笑話我。別忍著。”
蘇敏將摟得了一。
他在社會里打拼許多年,見的奇葩人事加起來也能寫本書。黃老頭這種利益熏心的角,倒也不是最惡心的一個。
一樣米養百樣人。有些人就是覺得,在社會的舞臺上,自己天生就該是唯一的主角。別人的、事業、利益、夢想……都不過是這舞臺上的道。都該為自己的野心讓路。
哪怕有人雪中送炭,治好了他的經年頑疾,不計報酬地把他從泥濘的底層里拉上來,他也不會真的恩,只會覺得是自己運氣好,天生貴人相助的命。
這種人善于偽裝,輕易看不他真面目。
只能說,常在河邊走,哪有不鞋。生意場更是人渣聚集的地方。上了,只能自認倒霉,及時止損。
他笑話、教訓又有何用?聰明人自會從挫折中學習,用不著旁人虛假意的敲打。
他只是問:“打算怎麼辦?”
Advertisement
小姑娘偎在他臂彎,乖巧溫順,輕的氣息帶著熱度,一一縷吹著他的手。
但眼里的是冷的。說:“黃老頭在小刀會名單上,如今卻算計我,和我毀約。按規矩,該是什麼罪責?”
蘇敏低頭看一眼,微微笑了。
心里莫名的淡淡自豪:他中意的姑娘,才不是遇事只知哭鼻子的小慫包。
“你也知道,洪門組織紀律很差的,”他學著的用詞,無奈地說,“小刀會骨灰都飛沒了,過去那些孤魂野鬼不歸我管……”
“那他也是欺負咱們‘湖廣同鄉會’員。”邏輯分明,立刻換論點,堅決道,“我那一元錢不能白給。”
蘇敏想了想,也用公事公辦的語氣說:“我可以傳話,讓和咱們‘同鄉會’沾親帶故的商家,都知曉那個老混蛋的事跡。以后若遇上他,沒人會跟他再做易。只能做到這些。可以嗎?”
林玉嬋盤算片刻,覺得可以接。
黃老頭喪盡天良,毀約賣房賣孫,不就是想東山再起,重新暴富嗎?那就讓商界抵制他,讓他人人喊打,開張不起來。
對這種毫無廉恥的賭徒商人來說,這可比“捆起來打一頓”要痛苦得多。
當然啦,暗地里盤算,要是這老頭以后真讓撞見,花錢悄悄請人打一頓,不走天地會的賬。義興的大哥們手閑已久,應該很樂意賺這個外快。
林玉嬋心明朗了些,從蘇敏懷里掙出來,門路從小柜子里找出一盒涼果,打開蓋子,自己丟一個進,盒子推到他面前。
“嗯,還有一件事。”呼吸帶果香,輕快地說,“或許不在天地會業務范圍,但是我想打聽一下……”
蘇敏神肅然,細心聽著。
Advertisement
他一句話沒說,但眼中亮懾人,好似冬日冰封的湖面,明澈而冷清,里面映著清晰的孩的影。
倒把看得有點不好意思:“……嗯,上海縣城里,有幾個販人的市場?都在哪?”
蘇敏微微詫異,手拈了一枚杏脯,沒吃。
“確實不在天地會的業務范圍。”他疑,“你……”
他很快明白了的意圖,輕輕搖頭。
“阿妹,算了。上海那麼大。費力不討好。”
“好啦,你也算勸過了,仁至義盡。”林玉嬋料到他的反應,堅持道,“你開價。只要我出得起這費用,我就一定要把找回來。”
說完,為表誠意,輕輕欠,在他臉上輕輕一點。
然后迅速。低下頭,小臉微醺。
秋風刮過水面,掀起一層層漣漪。小船左右輕晃。
蘇敏屏住一口氣,耳泛起可疑的紅,鼻尖掠過杏脯的香氣。
這哪是錢易,這是要他錢雙收啊!
雖然但是,難得這麼主一回,又是為了別人……
他收斂心神,不聲,轉過半邊臉,眼神示意。
“這是同意了?”林玉嬋大睜雙眼,眼眶紅紅的還帶淚痕,無辜而直白地問:“再親一下能打折嗎?”
“不能,”蘇敏立刻找回狀態,輕輕白一眼,順手把橙黃的杏脯塞到里,“而且,這事有風險,工費會貴一點。我再警告一遍,你得不償失。”
立刻問:“多錢?”
蘇敏眉目舒展,和地看著,微笑。
“你能出多?”
林玉嬋馬上急了,咬著杏脯含含糊糊:“不準坐地起價!”
蘇敏彎起角。現在可算是把那傷心的緒甩到腦后,眼里滿滿都是斗志。
Advertisement
他拉起的手,輕輕捋著一細手指,在邊一下下的,斟酌著措辭。
“一個價位有一個價位的玩法。”他最后說,“你愿意出多些,風險就小些。”
林玉嬋小聲:“不騙你,我……剛收了許多棉花,手頭有點。”
蘇敏輕輕吻了吻手背。
“上次在當鋪里收的那幾件首飾,還留著吧?”
他思維跳躍太快,林玉嬋一怔,“嗯”了一聲。
“今晚五點,換男裝,跟我出門。”
---------------------------
秋冬之,天黑得迅速。林玉嬋恍惚記得,昨日海關鐘聲敲響時,天還是亮的,太尚且掛在天邊樹梢;今日海關五點鐘聲照舊,天上一層云,卻已經染上了淡淡的灰。
福州路一帶院落參差,白日里是條尋常巷陌,到了晚間反而人多起來。一排暖融融的紅燈籠掛在飛揚的屋檐下,漸次點燃,煥發出朦朧曖昧的。
不同流派的竹戲曲之聲從各個窗戶里飄出,合一曲聒噪的大燉。
水里的老鼠大大,忽地竄進一家亮燈的堂子,撞出一屋子人驚。
一條小小破門簾,一個濃妝子半躺在竹椅上,慢慢著大煙,特特出一雙包在珠鞋里的尖尖小腳,輕輕搖晃著,十足的逗引模樣。
穿著俗艷的紫,滿頭廉價首飾。握著大煙槍的那雙手,盡管戴了手套,但還是能看到,手腕上爬著紅的疣痂,見之令人頭皮發麻。
門框上掛著小旗,上面有某名家題字:“南市花魁第一蓮”。
花魁生意冷清,偶爾有人被那雙玉足吸引,掀簾探頭一看,又啐一口,搖頭走開。
忽然,一輛裝飾著鮮花彩緞的馬車張揚駛來。一群游手好閑的青年男子,追著那馬車歡呼:“今年的花魁來啦!媛媛姑娘來了!姑娘笑一個!媛媛姑娘我慕你老久了!……”
忽然有人慘一聲,一個紈绔離得太近,被馬車掛住袖,啪的摔在地上,肚子地,雙手吊起,被拖了好幾步。
余人大駭,趕:“停車停車!”
小車廂的窗簾終于掀開,一個滿頭珠翠的艷妝子探出頭來,好奇地往車下看一眼。
眾閑撇下那掛在車上的倒霉蛋,縱聲歡呼,爭相往車窗里扔東西:銅板、銀元、寫在香箋上的艷詩,什麼都有。
“媛媛姑娘!媛媛姑娘看看我!”
被掛住服的那人幸無大礙,自己掙扎著爬起來,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媛媛姑娘忍俊不,掩著櫻桃小口,轉頭對著車廂里的什麼人,細聲罵了一句方言:“儂看伊戇腦個樣子,也想吊膀子呀!”
閑們哄堂大笑,更加瘋狂地追逐駛遠的馬車。
破門簾翕,先前那大煙的紫“花魁”憤怒地起來。只見那價格不菲的白凈珠鞋上,被馬車子濺了七八個泥點。
紫子突然跳下竹椅,指著那遠去的馬車破口大罵。
“臭婊`子,不就是仗著年紀鮮,風得意個卵!早晚你和我一樣!……”
躍出門簾,整張面孔一覽無余。盡管五秀,卻平白有乖戾之氣。盡管敷了厚厚的鉛,也遮不住底下一個個那潰爛發紅的膿瘡,
幾個閑厭惡地躲開,有人踢了一腳。立刻尖利大。
“殺人啦!欠錢不還啊!……”
幾個黑大漢聞聲從門臉里躥出來。閑嚇了一跳,隨后拱手賠笑:“我跟這位姑娘鬧著玩呢。”
大漢見被欺負的只是舊時花魁,并非當紅新寵,也懶得管,罵罵咧咧回去繼續打牌大煙。
罵聲又起:“沒良心的皮五辣子!老娘當初沒養你們!你們這些趨炎附勢的小癟,趁早給我死在狐貍床上!”
……………………
林玉嬋遠遠看著那個滿口話的紫`,難以置信。
“真的是……去年那個紫玉姑娘?”
那寫著“第一蓮”的小旗還記得,是花魁大賽的獎品,不會有錯。
只是這張臉已經判若兩人。一雙腳還尚且有些眼。
兩年不到的景,這雙曾被萬人追捧、被外國教士看中、費盡口舌要照相留念的兩寸八小腳,如今再也給招不來任何客人。
偎紅倚翠的歡樂場,向來是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的地方。
蘇敏捻著手中錢袋,警告地看一眼,冷淡提示:“看。想。”
他有點后悔把這姑娘帶上福州路了。萬一大發愿心,要幫這條路上的鶯花盡皆贖,那他最好趕跟撇清關系。
猜你喜歡
-
完結384 章

曹操之女
穿越長到三歲之前,盼盼一直以為自己是沒爹的孩子。 當有一天,一個自稱她爹的男人出現,盼盼下巴都要掉了,鼎鼎大名的奸雄曹操是她爹?!!! 她娘是下堂妻!!!她,她是婚生子呢?還是婚外子?
142.9萬字7.67 25064 -
完結556 章

全家去逃荒,她從懷裏掏出一口泉
特種兵兵王孟青羅解救人質時被壞人一枚炸彈給炸飛上了天。 一睜眼發現自己穿在古代農女孟青蘿身上,還是拖家帶口的逃荒路上。 天道巴巴是想坑死她嗎? 不慌,不慌,空間在身,銀針在手。 養兩個包子,還在話下? 傳說中“短命鬼”燕王世子快馬加鞭追出京城,攔在孟青羅馬車麵前耍賴:阿蘿,要走也要帶上我。 滾! 我會給阿蘿端茶捏背洗腳暖床…… 馬車廂內齊刷刷的伸出兩個小腦袋:幼稚! 以為耍賴他們
102.1萬字8.18 107383 -
連載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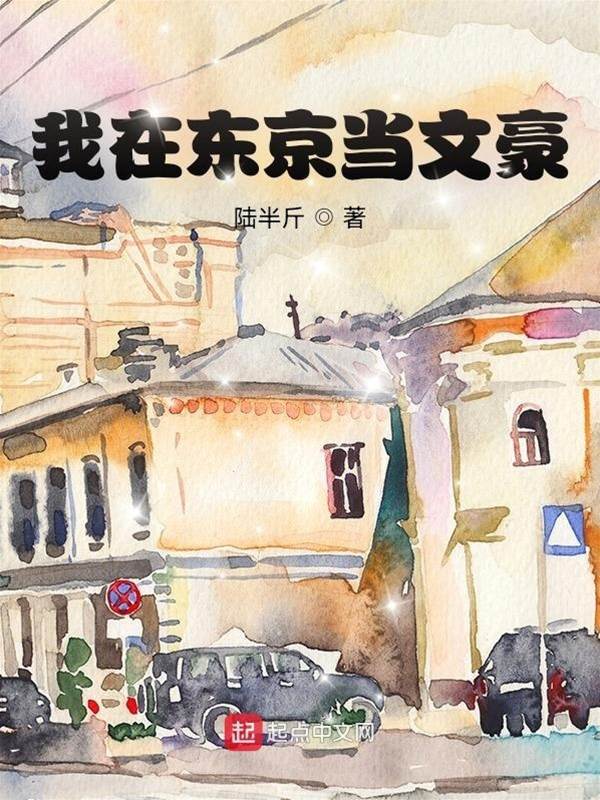
我在東京當文豪
這個霓虹似乎不太一樣,泡沫被戳破之後,一切都呈現出下劃線。 原本那些本該出現的作家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些筆者在無力的批判這個世界…… 這個霓虹需要一個文豪,一個思想標桿…… 穿越到這個世界的陳初成爲了一位居酒屋內的夥計北島駒,看著孑然一身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北島駒決定用他所具有的優勢去賺錢,於是一本叫做暮景的鏡小說撬開了新潮的大門,而後這本書被賦予了一個唯美的名字:雪國。 之後,北島駒這個名字成爲了各類文學刊物上的常客。 所有的人都會說:看吧,這個時候,我們有了我們精神的歸屬……
41.5萬字8.18 14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