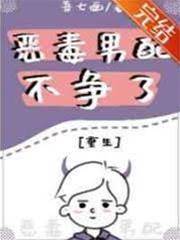《同居契約》 第43章
轎車拐上泥濘小路的時候, 坐在副駕駛上的聶長生才在輕微的搖晃之中醒了過來,他打了個呵欠, 抬眼見窗外掠過一大片丟慌了的冷綠田野,遠幾頭悠閑的大水牛或站或躺, 背上依稀還停駐著一兩只白的鳥兒。
主駕駛上的莊凌霄哼了一聲, 顯然對行駛的這段黃泥路非常不滿意。
狹小的車廂里只有輕音樂在微弱地流淌著, 聶長生借著后車鏡, 看到了原本吵吵鬧鬧的兩個年已經東倒西歪地躺在后座里,龔卿的懷里還抱著小白,小白顯然沒因為旅途的枯燥而沉睡夢里,它的小尾有一下沒一下地甩著, 顯示此刻愜意的心。
看了儀表盤上的時間,這已經快有兩個小時的車程了, 莊園也差不多快到了吧。
當豎起的一塊指示牌扁像一盞指路燈被鑲嵌在高電線桿上時, 田地也不再被丟慌了,一片又一片連綿不絕的甘蔗地呈現在眼前,路邊聳立了幾座小山丘一樣的甘蔗堆,白的黑的甘蔗一整整齊齊疊放著, 每座甘蔗堆上坐著一個穿著厚實服的五六歲小孩, 大概是路過的行人都不怎麼老實,沒人看管甘蔗堆的話, 會損失慘重。
“停一下吧。”聶長生突然開口道。
莊凌霄看著甘蔗堆上那些凍得一團的小孩,知道聶長生心又開始泛濫了,抿了抿, 緩緩地把車停在黃泥路邊。
聶長生打開車門,一寒氣撲面而來,野外凜冽的冷風卷著細碎的雨撲了過來,后座的賀鴻梧了脖子,睜開一條眼,了惺忪的眼睛,沙著嗓子問道:“到了嗎?”
鄰座的龔卿也醒了,他往窗外張了一下,道:“還沒吧,聶叔叔去買甘蔗了。”
Advertisement
果然,聶長生抱回了幾甘蔗,一分為二地攔腰折斷,塞到了后車廂里,回到車上時,上還帶回一陣水汽,發上,肩膀上都沾染了絨絨的雨屑。
汽車緩緩超前驅去,將坐在甘蔗堆里的激不已的孩遠遠的拋在后頭,他凍得通紅的手里攥著一張紙鈔,那是他這麼多天以來拿到過的最大面額的紙幣了。
“這麼冷的天,他們怎麼都不回家啊?”車上的四個人之中,只有從未吃過苦的龔卿會問起這麼一個不知人間疾苦的事。
“他們一離開,過路的人就會走甘蔗了!”賀鴻梧在福利院呆過幾年,什麼暗面的事兒都聽過也見過,心有戚戚地回答,他再一次慶幸被聶長生收養了去,否則留在福利院,天知道現在會不會比這些小孩更悲苦一點?
龔卿愕然一怔,他的印象里,一尺長的甘蔗也就一兩塊錢一吧,這麼便宜的東西,就算放在路邊也頂多損失幾百塊吧,為了這區區的幾百塊,寧肯讓自家小孩呆在野外淋著細雨吹著寒風?一不小心冒發高燒了,上醫院看個病所花的錢也不止幾百塊吧?
心思涌,他回過頭,甘蔗堆與小孩早就沒在片的甘蔗林里了,只有呼嘯的風將綠油油的甘蔗葉刮得此起彼伏,波浪似的推向遠方。
當轎車停靠在平坦的停車場時,恭候在一邊的莊園主人撐著油紙傘微笑著迎了過來。
原本的雨已經演化為淅淅瀝瀝的雨線,卻掩蓋不了莊園旺盛的客流量,是停車場上停著數十輛名牌汽車就知道慕名而來的有多人了。
雨幕下的莊園遼闊而寧靜,像一位氣韻不凡的小家碧玉坐在煙霧里沉思。
賀鴻梧第一次撐油紙傘,覺得很新奇,轉著傘柄甩起了雨珠兒,甩得莊園主人一個機靈,抹去了臉上、脖子上的冷水珠兒,心里憋著一氣,臉上卻還得陪著笑容。
Advertisement
還是聶長生出言制止了賀鴻梧的胡鬧,年吐了吐舌頭,有點憾天的院子這麼快走完,進了大堂,油紙傘也被迎客的侍應生收走了。
大堂里滿滿當當地坐在七八張桌子的食客,空氣里飄溢著陣陣菜肴的濃香氣味,兩個年肚子里的饞蟲瞬間被勾起,小白也盡發揮吃貨的特,一下子跳下了龔卿的懷里,循著氣味很快就找到了被客人丟在桌下的塊骨頭了。
“小白!”賀鴻梧忙召喚著有了吃就渾然忘了主人的吃貨,見它不理會,還大口地啃咬著別人丟下的殘渣,無奈地跑過去,把它抱了回來。
“嘿!賀鴻梧!”有個屬于男生變聲期時特有的鴨公聲驚異地響了起來,在喧鬧的大堂里顯得很是突兀。
賀鴻梧皺了皺眉,不用特意去搜尋,尖猴腮的巫溟晟已經站了起來,斜著眼睛看著他。
“喂,你的狗怎麼還沒弄死啊?”巫溟晟奚落地道,“養不起寵就不要養嘛,跑來乞討骨頭,也夠可憐的。”從滾燙的火鍋里撈起一塊擲在賀鴻梧的跟前,挑釁似的冷笑著。
賀鴻梧冷著一張臉,真倒霉,這樣也會遇上這家伙!真想放小白去咬巫溟晟那張不可一世的瘦臉。
巫溟晟邊坐著的貴婦模樣的婦人顯然也注意到了兒子的挑釁,罵道:“快吃飯,別惹事!小心你爸爸回來剝你的皮!”
巫溟晟似乎不把他媽媽的恐嚇放在心上,正要再奚落幾句時,卻見龔卿掰著“咯咯”作響的手指走了過來,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樣,好像他再不識抬舉,就要用拳頭的實力說話了。
巫溟晟了頭,顯然是吃過龔卿拳頭的虧,不過大庭廣眾之下,他邊還有父母,諒龔卿也不敢用拳頭揍他,于是朝兩個同學豎起了中指。
Advertisement
于是鬧劇就這樣上演了,龔卿一拳揮到囂張的巫溟晟的臉上,他本就是個瘦子,慘一聲,腳下一個趔趄,狠狠地倒在地上,帶倒了旁的一張空椅子,撲倒在地上,頭腦一片空白,他沒有想到向來彬彬有禮的龔卿說開打就開打,張剛要哇哇大哭時,龔卿已經坐在了他的肚子上,左右開弓,“啪啪啪啪”四五聲中,他狹小的臉頰瞬間紅腫了起來,疼得他一冷汗布滿了額頭,一句疼也喊不出聲。
那位貴婦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邊狠力拉扯在兒子上的兇犯,一邊又又罵,吵鬧的大堂瞬間安靜了下來,不明就里的尋找鬧騰的地方看來。
賀鴻梧見那個的指甲都招呼上了龔卿的臉上了,龔卿的臉上帶著痕了,快步上前幫忙,跟小白一起,試圖拉開發狂的婦人,可惜那貴婦重比較客觀,他小胳膊小兒,怎麼也沒法拉半分。
彼時聶長生坐在廳里,他上的一側了幾條線,這是他買甘蔗時,不小心被甘蔗上的牙口卡住,等到發現時,也不過是出小小的一個口,并不怎麼影響外觀,所以也就不怎麼為意了。
眼尖的莊凌霄卻向莊園主人借來了一細細的小夾子,笨手笨腳的要把卡出來的線條埋進里衫去,他曾經打籃球時,也是被對方扯破過一個丑陋的破,聶長生就是用這種方法將他的弄好的。
聶長生低垂著頭,蹲在他邊的莊凌霄神認真,卻不得要領,怎樣也無法將那調皮的線埋里衫,聶長生的邊揚起一笑容,這個不可一世的男人,竟然會小心翼翼的給他埋殘線,而不再是從前嘲諷他的節儉。
Advertisement
原來不知不覺之中,彼此的影響,已經深骨髓。
接過他手里的小夾子,聶長生三兩下的穿梭,衫里敗落的線就服服帖帖地藏在里衫里,恢復了原狀。
“莊先生……”一個侍應生急急忙忙地跑過來,慌地道,“您帶來的兩個小孩……打……打架了!”
聶長生臉一變,手里的夾子落,人飛快地朝大堂跑去。
等莊凌霄沉著臉步大堂時,紛擾的鬧騰聲集中在發生事故的那張桌上。
頭發凌的一個婦人正用尖利的高音憤恨地對著聶長生大罵:“你養什麼小孩!這麼野蠻屋里,不會教就別養!”
一個魁梧的頭中年男子也惡狠狠地罵了一聲國粹,道:“你別想走,人證證都在,你的小孩把我兒子打著這麼重,你是想私了,還是去警局?”他口中的“證”,可不正是臉頰腫得老高的巫溟晟麼?
沒有吃多虧的賀鴻梧見到哭得稀里嘩啦的巫溟晟就一陣幸災樂禍,他知道素來不崇尚暴力的龔卿為什麼會點燃了怒火。上一次,因為小白咬了他,兩人被請了家長,龔卿的監護人迎頭就給他一個耳,龔卿當時一邊臉就腫了起來,角也掛了一條,那是目驚心的鮮,賀鴻梧從來沒有料到,“監護人”會充當赤的施者。
新仇舊恨,沒有吃過一點苦頭的龔卿終于發了中的怒意,將讓他嘗到了耳滋味的巫溟晟以十倍的代價償還。
聶長生太習慣被別的家長投訴了,對方雖然態度很惡劣,但錯的畢竟是己方,正要道歉且自認賠償時,那個滿口污言惡語的頭突然滿臉笑容,很諂地對聶長生后那人道:“莊大總裁,幸會,幸會,您怎麼也在……”
“我的師哥不是不會教小孩麼?”莊凌霄吐著一口煙霧,冷冷地道,“只好我來教了。”
頭臉一垮,上一次,他的兒子被狗咬破了一層皮,正要興風作浪狠刮對方一層皮時,收到了莊凌霄的一通電話,電話里,莊凌霄提到了“師哥”這號人,那是他無論如何也招惹不起的人,沒想到他這麼倒霉,一連兩次得罪了同一個人,別提多晦氣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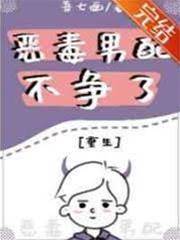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0242 -
完結239 章

替身受假死之后
許承宴跟了賀家大少爺五年,隨叫隨到,事事遷就。 哪怕賀煬總是冷著臉對自己,許承宴也心甘情願, 想著只要自己在賀煬那裡是最特殊的一個就好了,總有一天自己能融化這座冰山。 直到某一天,賀煬的白月光回國了。 許承宴親眼看到,在自己面前永遠都冷淡的男人,在白月光面前卻是溫柔至極。 也是這時,許承宴才知道自己只是一個替身。冰山是會融化的,可融化冰山的那個人,不是自己。 狼狽不堪的許承宴終於醒悟,選擇放手,收拾好行李獨自離開。 而當賀煬回來後,看到空蕩蕩的公寓,就只是笑著和狐朋狗y打賭:不超過五天,許承宴會回來。 第一天,許承宴沒回來。第二天,許承宴還是沒回來。 一直到第五天,許承宴終於回來了。只是賀煬等來的,卻是許承宴冷冰冰的屍體,再也沒辦法挽回。 三年後,賀煬依舊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賀家大少爺。 在一場宴會上,賀煬突然看見了一道熟悉身影。賀煬失了態,瘋了一樣衝上前,來到那個黑髮青年面前。 “宴宴。” 向來都冷淡的賀家大少爺,此時正緊緊抓著青年的手不放,雙眼微紅。 “跟我回去,好嗎?”而耀眼的黑髮青年只是笑著,將男人的手移開。 “抱歉先生,您認錯人了。”渣攻追妻火葬場,1v1。 受假死,沒有失憶。假死後的受一心沉迷事業,無心戀愛,渣攻單方面追妻。
50.5萬字8.18 51379 -
完結143 章
願以山河聘
原名《嫁給暴君後我每天都想守寡》 秦王姬越是令七國聞風喪膽的暴君,卻有這麼一個人,風姿羸弱,面容楚楚,偏敢在他面前作威作福。 年輕的帝王沉眸望著美麗動人的青年,還有抵在自己脖頸上的一把冰冷匕首,語似結冰。 “衛斂,你想造反?” 衛斂含笑,親暱地蹭了蹭他的唇:“你待我好,我就侍君,你待我不好,我就弒君。” _ ——孤攜一國作嫁,不知陛下可願否? ——願以山河聘。 1.對外暴戾對受沒辦法攻vs腹黑淡定美人受 2.甜文HE,非正劇 3.架空架空架空,朝代是作者建的,不必考據 扮豬吃虎/強強博弈/並肩作戰/至死不渝 想寫兩個魔王的神仙愛情
39.5萬字8 64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