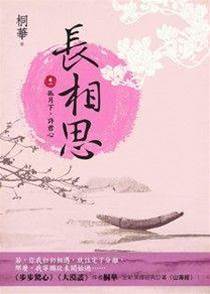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洞房前還有遺言嗎》 第九十三章 月狗掉馬(二)
雕花木門吱嘎一聲搖曳開來。卿如是躊躇片刻, 過門檻。巧云端著水盆跟上。
目所見, 思君秋水。
滿墻的字畫, 落筆潑墨都只為一個人。
卿如是的腳步微頓,心底驀地升起一久違的熱沸騰。那是一個在卿如是的心中已經死去多年的故人。
那人心高氣傲,快意恩仇;為悖世的信仰揮毫萬字, 一飲千盅;不屑風月,舉手投足卻凈是風月;三杯兩盞淡酒, 往來云煙過客, 浮華褪盡, 只余筆墨。
那個子活了十年西閣里最與懷念的模樣。也是如今回不去的模樣。
秦卿。是秦卿。
崇文先生說,的名字簡潔明凈, 干干脆脆,咬在口中又婉轉生趣,最好不過。
這滿室的字畫,都是秦卿。
踏門檻的那一剎那, 仿佛再次走了闊別多年的秦卿的世界。
那書桌上本就沒有落塵,有的只是一摞摞用草書和簪花小楷兩種字跡寫了滿篇“秦卿吾,至死不渝”的澄心紙,紙張角落印著孤傲的青竹。這是專門為做的紙, 只配屬于曾經那個秦卿的東西。
桌邊展著一幅畫。是在葉渠的書房里見過的百年廊橋。還記得頭次看到這幅畫時的心境:無花無草, 無人無鳥。萬都枯萎,生靈皆死去。大地忽而蒼茫, 晴空驟然失。
畫卷上那句潦草的題字,讓卿如是倏地捂住輕泣出聲。
能想象月一鳴彼時用如何絕死心的語氣坐在床前喃喃地念。他念:“夜深忽夢卿, 驚坐起,不知今夕何夕。我看清風是卿,我看月影是卿,捕風風不停,捉影影不應,驚坐起,不知今夕何夕。唯恐卿卿不夢,推窗請風進,熄燈把影留。”
Advertisement
他的秦卿再也不應他,他的清風月影也不應他。
想起月隴西說……不,不。或許此時該喚他月一鳴!
卿如是的手抓在紙上,紙面被的指尖皺,咬牙低喚,“月一鳴……!”像是從牙中出來的字。
他說,有一晚他被夢魘著了,坐起來就拿刀子扎了手。那時候他已經接近瘋魔了。何時能死,何時能去找都是他每日苦思冥想的問題。
道這幅畫的題字為何如此潦草,失了他那一手狂放草書的髓。原是他在畫這幅畫之前右手就再也不能握筆。可他卻執拗地用右手題字,寫下了無生意的念句。
白墻上掛著數幅佳作,一片沉悶死寂。卿如是記得自己這世醒來后,翻找過現存于世的秦卿畫像。發現幾乎都出自月一鳴之手,畫中的從來沒有笑容。彼時以為是月一鳴為了抹黑才這般為之,如今……他不怎麼常見對他笑啊。自死后,想必也再畫不出的笑,心境蒼涼,如何作畫。
“偕老共卿卿。”
“夜深,頻夢卿。”
“莫將閑事惱卿卿。”
“有時醉里喚卿卿,卻被旁人笑問。”
書架上陳列的書籍中,隨意翻來便有寫滿如此字句的紙箋出,幾片上落著淚滴干后留存的痕跡。或有生前最喜的幾種花的花瓣作書簽,順著書簽翻開,上邊是月一鳴生前的手記。
“奇怪,卿卿為何就瞧不上我呢?”日期是府的那天:“倘或一直不心,我便要永遠等著?愿如此。”
“卿卿病了。整日坐在屋里看書,能不病嗎?想知道寫的什麼。書中的如玉有我半分好看無?為的暴殄天到痛心疾首。”
卿如是失笑,淚水卻被這一笑駭得灑出來了些。
Advertisement
“想跟卿卿要個孩子。陪著孩子跑跳,就不病了。想跟有個家。”
“風和日麗,無事可做。就去逗卿卿。”
“廊橋拿回來的毽子,好像有些臟了。可憐我一個大男人也不知該如何清理這些東西。”
“想知道口中的崇文先生究竟想了些什麼。整得跟邪。教似的,卿卿覺都不睡了。”
“聽聞半月后新廟有燈會,我想帶卿卿去玩,苦心籌備多時,命人買來燈籠掛滿扈沽城。料定被我。滿心期待,最后卻不愿跟我去。失算,失算。下回問問采滄畔何時能不辦斗文會。不是我說,他們這文會是否辦得頻繁了些???都快趕上我跟卿卿行房的次數了。整日里為些死而醋,我也十分無奈。”
“翻了幾日崇文的書,竟覺他的思想與我時雜七雜八想的那些東西差不離。雖不能完全通,但于我而言很好理解。我覺得,我也能跟卿卿作知己。”
“卿卿去雅廬抄書,竟整日里只煮面條來吃。瞧著心疼。”
這一年所記之又。
“興許是反骨作祟,我近期瞧著惠帝愈發不順眼。”時間是秦卿被廢雙手的前幾日。
這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他都沒有再繼續寫。日頭跳躍了幾年,他寫道:“謀反,可行。卿卿,等我。”
在這之后,又是很長的一段空白期。
“卿卿……真的不要我了。”日期停留在下葬的那一天。
此后,月一鳴再未續筆。年的思徹底被塵封,化為深,只行而不言。
卿如是無意抬手抹了抹眼。到滿手的淚。
哽咽著,頭酸。忽察覺到余里站著一個人。
月隴西就佇立在門邊,天乍泄,傾覆在他后。他就那般凝視著,眼角猩紅,須臾,他忽然抿輕笑了聲,哽咽道,“秦卿,別來無恙啊。”
Advertisement
話音落的一瞬間,卿如是跑過去摟住了他。
頃刻天覆,卿如是有種在時空中徒步跋涉,終于回到前世的暈眩。目盈盈,聲喚道,“月一鳴……”幾個字咬得百轉千回。那是一種過盡千山萬水后與子重逢的氣回腸。
月隴西的眸愈漸幽深,歲月的沉淀讓他對這個名字到些許陌生,風華已如流水逝,如今的他再不配這桀驁恣意的三字,鮮活明的一生。再沒有任何一個男人能配得上這三字,包括如今的自己。
這三字是他癡心妄想的過去,自死后,被塵封多年,末日余暉為其上了鎖,朝添了三分,便沉海底,再翻不起風浪。但還好,他很喜歡聽用這般語氣喚他。
月隴西笑了笑,低頭時驀地眼角猩紅。他捧起的臉,凝視著,啞聲道,“再喚幾聲。”
“月一鳴……”卿如是咬,哭道,“月一鳴……月一鳴啊……”
月隴西偏頭失笑,一滴滾燙的淚自眼角落,他嗓音微嘶,偏執地為前世耿耿于懷的事作一問。他問:“那,現在給親了嗎?”
那年花燭夜時,他挑起的下頜,滿懷期待地想著,假如吻下去,定要給予最大的溫。可猛將他推開,不稀罕且嫌惡他的親吻,這一推,就是一輩子。難以忘記彼時倔強又決絕的眼神。
倘或面前的是月一鳴,給親了嗎?
卿如是抱住他,踮腳主與他擁吻。心底有個聲音在指使自己,永遠不要再推開他,要抱住這個為你遍鱗傷的男人。
卿如是的順著他的下頜下,埋在他的頸間,淚水黏在上邊,哭得口齒不清,嗚咽著不知在說些什麼。月隴西卻聽得清,他明白,他都知道。
Advertisement
說:“對不起……月一鳴,秦卿對你的喜歡來得很遲很遲……”說完,又攥著月隴西的襟,固執地踮腳吻他。
要和他地老天荒,要和他像月一鳴從前希的那樣地老天荒。
要那月,那廊橋,要那世間萬統統給他們作見證。
月隴西雙手捧起的臉,熱烈地回應著的吻,撬開的齒攻城掠池。
他如此,卿如是有些不住,下意識了下,兩人接吻的姿勢便不順當了。月隴西停下來,微微氣,退了些,手抬了抬的下頜,意迷中還不忘低啞著嗓子教,“著我,下抬起來。記得呼吸,不要憋氣。”語畢,又覆而上穩住了。
一吻作罷,卿如是已泣不聲,卻不想放開他,眷地勾住他的脖子,凝著他道,“還要……”
月隴西沒有片刻猶豫,打橫把抱起來,朝臥房走去,放到榻上,覆上去溫地親吻的眼睛。
“月一鳴……”卿如是稍緩下的緒再度被燃起,哭著、抖著低聲喚,“月一鳴啊……”似乎下一刻就要忍不住嚎啕,卻被口的酸瞬間封住了聲音,不敢驚擾此刻的溫。
“嗯。”月隴西拂開額邊的青,哽咽地問,“……喜歡了嗎?”
“喜歡……月一鳴,秦卿很喜歡你。”
“那一會開始之后要好好吻我,還要喚我的名字,還要喊夫君。”月隴西幾近無聲地問,“好不好?”
卿如是篤定點頭,“好。”
月隴西稍頓,卻沒有作。須臾,他握住的手抵在自己的邊,任由眼淚過側頰,又滴落在的指間,他用商量的語氣笑說,“月一鳴他……對不住你的地方太多了,或許,我還是喜歡你喚我月隴西。”
聞言,卿如是徒然崩潰,哭著要他親吻,“月一鳴……”
這世間之事,難說行之對錯,唯有值得不值得。
“但若是你喚,我還是要應一聲。”月隴西輕吻的手背,合上眼回道:“誒,卿卿,月一鳴一直都在。”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廢後謀
那年,看見他,仿佛就已經中了她的毒,日日思念不得見,最後她嫁給了他的兄弟,他只望她能幸福,哪成想,她的夫君一登基,就將她打入皇陵守孝,既然如此,他不會在放過與她相守的每一個機會了,就算全天下人反對,又如何,他只要她。
17.4萬字8 9477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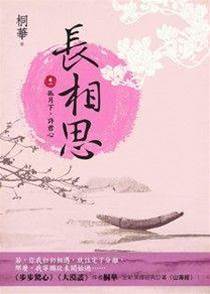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18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75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