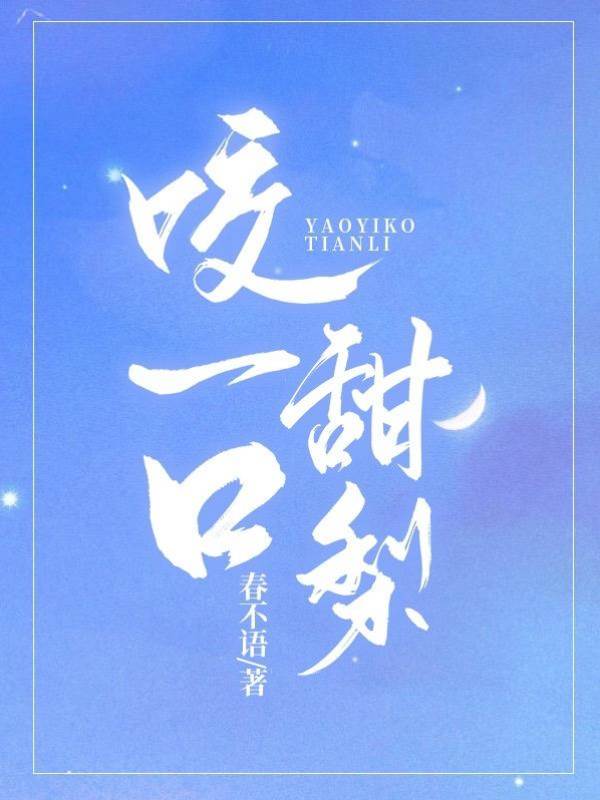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他與愛同罪》 第四十五章
燕綏到底是在吃人不吐骨頭的商界爬滾打長起來的,臨場應變能力強,初時的錯愕不過一瞬,等反應過來后,見招拆招。
微抬了抬下,一臉矜傲地邁下車:“你想得!”
上討了便宜,燕綏還嫌不夠得意,下車時狠狠撞了下他的肩膀,這才讓到一邊,笑瞇瞇道:“那就麻煩傅長了。”
傅征被撞得子一偏,深看了一眼,顧著車里還坐了辛芽,了聲音,問:“高興了?”
燕綏笑意一斂,隨手把車鑰匙拋給他。
傅征手,穩穩從半空截了鑰匙。
巷子盡頭恰巧有束車燈打來,傅征的側臉被燈勾勒出星河和山川,一明一滅的燈替中,他垂眼看來的那雙眸子深邃得像是能夠吸走所有的線。
燕綏呼吸一窒,到了邊故意挑釁他的那句“不高興”就怎麼也說不出口了。
清了清嗓子,了聲辛芽:“走了。”
傻坐在車上看戲的資本家家的傻白甜終于回過神,連滾帶爬地下了車。
車給傅征停,燕綏帶著辛芽掀了簾子先進去。
門口清雋的山水屏風前正立著兩位穿旗袍的服務員,見燕綏辛芽進來,微微頷首,溫聲細語地詢問:“您好,歡迎臨董記餐廳,請問您有預訂嗎?”
燕綏不聲地四下打量了眼,微笑:“不急,我等個人。”
辛芽缺弦,見狀,說:“我給蘇小曦打個電話。”
“不用打。”燕綏不疾不徐道:“我等的人,不是。”
在等傅征。
這家董記私房餐廳,隔著一層簾子,屋屋兩個世界。
進來時留意過,迎賓的那扇屏風,是一套十二扇緙屏風芯的黃花梨木山水屏風,瞧著那彩搭配和做工應是以前皇家用的。
Advertisement
老板能把這麼致的屏風放在迎賓口,顯然這屏風也不是真品。
古時屏芯多用絹這種細致的材料,嵌百寶鑲金。絹,紙,這些東西貴,日逐月蝕的保存不完整。真是老古董,兩百年下來,屏芯早就脆了,一即碎,還舍得放這種人來人往的地方迎賓?
燕綏原也不懂這些,對古玩字畫的鑒別賞玩是毫無天賦。不過和那些有錢沒花,就喜歡投資些古玩珍藏的資本家打道多了,多還是學了點東西。
就這山水屏風的走線和彩,門道跟國畫里筆尖勾染挑刺著墨的覺一樣,不是皇家用品,不會這麼細。
這扇黃花梨木山水屏風雖沒真品值錢,但價貴重,毋庸置疑。
這種地方,蘇小曦請不起。
——
傅征停好車,掀了簾子進來,見燕綏還站在門口,腳步停了停,躍過燕綏把車鑰匙遞給辛芽:“你先跟們去包間。”
辛芽接過車鑰匙,一頭霧水地就被服務員引著繞過屏風,去二樓的包間。
人一走,隔了屏風的迎賓口就像是獨立的一隔斷。
燕綏目帶審視,盯著傅征看了一會,問:“今晚到底是蘇小曦我來,還是你?”
傅征好整以暇地回視:“蘇小曦。”
燕綏的眉心一蹙,很快又若無其事地松開,只不過眼神里卻多了一玩味:“你是哪邊的人啊?”
傅征不答,他從袋里出煙盒,低頭了煙咬住,聲音含糊地問:“我煙?”
燕綏做了個“你隨意”的手勢,看他點了打火機,火焰上煙屁的時候,他抬眼睨了一眼。
那眼神,莫名的有幾分威懾之意。
燕綏還沒從他這眼神里回過味來,他低頭,頗迫地靠近,那雙眼在煙霧里微微瞇起,眨也不眨地盯著,問:“腦子呢?”
Advertisement
燕綏:“……”
傅征耐住子,一字一頓道:“你這邊的。”
聲線得低,又含著一口煙,嗓音低沉微啞,磁得像是有磁石互相著,低醇悅耳。
燕綏暗暗磨了磨牙。
這人生來就是克的吧?
退后一步,和他拉開距離,語氣越發不善:“你是不是知道我要來?”
“嗯。”傅征看一眼,走了兩步,把煙灰彈落在前臺的煙灰缸里,反問:“你以為我為什麼在這里?”
燕綏習慣了他喜歡用反問句回答問題的方式,終于舒坦了:“我把話說前頭,我跟蘇小曦磁場不合,互看不順眼。而且我這人,目中無人慣了,等會要是故意惡心我,你別指我會給你面子。”
傅征笑得揶揄:“我在這,不敢。”
這話勉強順耳,燕綏那臉沉徹底放晴,一副“那”的架勢,示意他:“你帶路。”
這句話實在有意思。
傅征回憶了下,保持著領先一步的距離邁上樓梯:“上次跟我說這話的人,沒活過二十四小時。”
燕綏的腳步一頓,腳心發涼。
他的語氣一本正經,聽著不像是和開玩笑……所以,現在跪下爸爸還來得及嗎?
傅征余瞥見腳步遲疑,彎了彎,慢條斯理地補充了一句:“不一樣的是,上一次我是被脅迫的,這一次,心甘愿。”
燕綏也是納了悶了,擒故縱這招是不是普遍男人都吃?
之前捧著哄著就差跟他搖尾了,也沒撬他冰山半角。這段時間冷幾天,再一,毫無包袱地撂了狠話,他倒是舍得開竅了?
想是這麼想,燕綏其實也知道,沒前期一步一算計地在傅征面前刷足了存在,哪來現在的厚積薄發?
Advertisement
心里嘟囔著,當做沒聽懂傅征的調戲,故意把重點落在他的前半句:“脅迫?誰拿槍指著你了?”
“三年前。”走到二樓,傅征停下等同行:“駐外華僑企業家遭綁架,我接到命令,安全帶他撤離。我被俘二十四小時后獲救,他就死在我的槍下。”
這個話題不適合細說,傅征點到即止。
燕綏也沒追問,知道他輕描淡寫的幾句話里是不能與外人道也的兇險,揭人傷疤滿足自己窺探私的事,從來不做。
——
“到了。”傅征下門把,推門而。
滿室暖的燈爭先恐后地涌出來,燕綏跟在傅征后,只看見了天花板上奢華寶氣的數盞琉璃宮燈。
等傅征側,替拉開辛芽旁邊的座位,的視野從他的后背擴至整個包間,第一眼先看見了坐在蘇小曦左側的年輕男人。
干凈的寸頭,雙眼有神,臉頰微凹,出幾分病弱的憔悴。
下沿至脖頸,有結痂也有未愈的數傷口,頸后領下更是出大片紗布。
這麼明顯的特征,燕綏就是想裝得遲鈍一點也做不到。目落在蘇小曦的臉上,微微一停頓,笑了笑:“終于見到本尊了。你好,我是燕綏。”
遲宴整片后背至大被炸傷,雖然傷勢恢復驚人,但目前行還是不太方便。他扶著桌子想要站起,燕綏看出他的意圖,忙道:“別別別,你坐著就好,不講究這些虛禮。”
第一次見面,遲宴還有些靦腆,下意識瞥了眼傅征,見他微點了下頭,笑了笑:“久聞不如見面,我是遲宴。”
燕綏心里“嘖嘖”了兩聲,這就是被上“冤大頭”標簽罵了無數遍不長腦子的遲宴啊,長得是俊秀,可惜眼神不太好。
Advertisement
還暗自慨著,蘇小曦站起來,表不見一點生疏,熱地招呼燕綏坐下:“剛職,要學習得東西太多,都沒時間。早就想請你和辛芽一起吃飯,謝下你們的照顧。正好今天遲宴出院,就邀請了你們過來,不介意吧?”
手不打笑臉人,蘇小曦客客氣氣的,燕綏也大方,等服務員添滿茶杯,舉杯:“有什麼好介意的?反正大家都認識。”
蘇小曦又笑,燈下,的笑容委婉人,遮掩起燕綏看不慣的那世俗氣,瞧著順眼了不。
——
人到齊,菜很快就被端上來。
辛芽對自己的定位是“湊數的”,不尷不尬的,也不打算參與任何話題。
有個定律怎麼說來著……
哦!
想減存在,吃吃吃就行,千萬不要有眼神對視,更不能有表流,否則高智商的人是談笑風生,到那就是彈棉花。
辛芽不忙著吃,偶爾也合時宜地犯職業病。
盯著燕綏喝了三杯茶后,怕喝多了太提神,晚上會失眠,讓服務員換上清水。
蘇小曦正和遲宴有說有笑地聊剛進淮岸工作的趣事,聞言,說了一半的話戛然而止,側目看向辛芽。
辛芽用紙巾掖了掖,確保自己沒有滿油,笑盈盈解釋:“小燕總睡眠質量不好,睡難。除非白天工作量強度大,否則不能喝太多茶,傷。”
說完,又補充了一句:“小燕總的食住行基本都歸我管,有點犯職業病,你們無視我就行。”
燕綏微笑。
覺得辛芽是真招喜歡,也不是很聰明啊,可每次該機靈的時候就機靈,一點也不犯糊涂。
遲宴出院了,仍需要休養。
蘇小曦這人婊是婊了點,但絕對不笨。看能拿遲宴這麼久就知道,善于抓人弱點。這種該表現溫良賢淑的時候,絕對不可能要求遲宴來董記這種不符合消費水平的地方。
那就只有遲宴自己要求的這一種可能。
燕綏不知道是什麼事讓遲宴剛出院就迫不及待約蘇小曦在外面餐廳見面,不過瞧蘇小曦那樣子,心里應該門兒清,否則怎麼會想著上一起吃飯,謝的照顧?
雖然不知道蘇小曦打的什麼主意,但就黏遲宴的那黏糊勁,一副燕綏們是打包來的樣子看著就讓人窩火。
辛芽這一打岔,就差直接提醒蘇小曦:“我小燕總金貴,你著點伺候啊。”
——
燕綏這人記仇,焉壞,好巧不巧的這時候想起一件事。
在桌下,用腳尖踢了踢傅征,問:“你部隊都在打賭你什麼時候打報告的事你知道嗎?”
按劇本,傅征無論知不知道,都該裝作第一次聽到的樣子。
不料,傅征視線一偏,側目看,語氣聽不出緒地反問:“知道,你賭了多久?”
燕綏:“……”靠?!
猜你喜歡
-
連載1965 章

左先生寵妻百分百
她是能精確到0.01毫米的神槍手。本是頂級豪門的女兒,卻被綠茶婊冒名頂替身世。他本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專情總裁,卻因錯認救命恩人,與她閃婚閃離。他從冇想過,有一天,她會用冰冷的洞口指向他的心臟。“這一顆,送你去給我的孩子陪葬!”她扣下食指……
164.4萬字8 184421 -
連載2383 章

錯嫁纏婚:首富老公乖乖寵我
為了救父親與公司,她嫁給了權傾商界的首富,首富老公口嫌體正直,前面有多厭惡她,后來就有多離不開她——“老公寵我,我超甜。”“嗯......確實甜。”“老公你又失眠了?”“因為沒抱你。”“老公,有壞女人欺負我。”“帶上保鏢,打回去。”“說是你情人。”“我沒情人。”“老公,我看好國外的一座城......”“買下來,給你做生日禮物。”媒體采訪:“傅先生,你覺得你的妻子哪里好?”傅沉淵微笑,“勤快,忙著幫我花錢。”眾人腹誹:首富先生,鏡頭面前請收斂一下?
219.6萬字8 148203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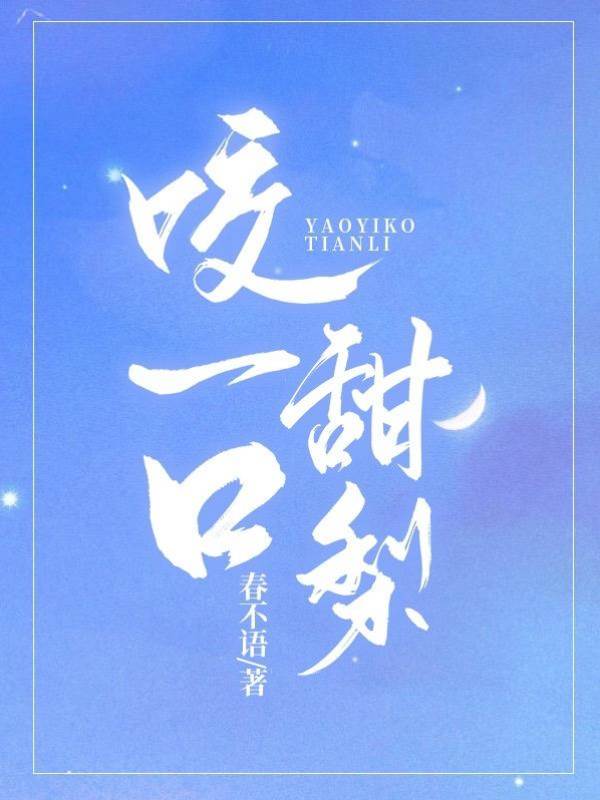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