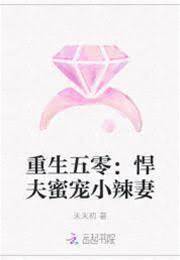《將軍總被欺負哭》 第11章
初秋的時節,下了一場秋雨,風中便著一涼意。
程千葉居于寶馬香車之,掀起簾子看著兩側的街道。
這座剛剛被戰火洗禮過的城市,帶著一種破敗和蕭條。
不遮、神灰敗的流民三三兩兩地在泥濘的道路上行走。
那些崩壞的墻之下,不時可以約看見一團蜷著的。
程千葉不敢去仔細辨認,因為那或許又是一失去生命的尸。
“真是蕭條,我們晉國比起這里好多了。”程千葉是從晉國一路領軍過來,親會了兩地民生的巨大差距。
“那是因為大晉有主公您啊。”蕭繡湊過來一起看向窗外,“汴州最近幾年都在戰之中,輾轉于不同勢力之手,每撥人馬都只想著拼命搜刮一通就走,還有誰會管老百姓的死活。”
也許是作為理科生的程千葉,中學歷史和政治只學了個表面。
在的潛意識里,封建帝制下的君王,就是個剝削和獨裁的象征。
他們站立在廣大群眾的對立面,養尊優的吸取民脂民膏,應該是被百姓討厭和憎惡的對象。
到了這里,才發現。
在這種年代下,有一個固定的主君,一個穩定的國家,才是人民真正的期待。
所有的對于平等和人權的需求,那都是建立在溫飽和社會富足之后的產。
“這麼說來,我還有可能是一個被這里的百姓期待的主公啊。”程千葉下。
“那當然,主公您是一位仁慈而善良的君主,是我晉國百姓之福呢。繡兒要不是遇到了主公,早就死街頭了。”蕭繡靦腆地說道。
程千葉點點頭,沒有注意蕭繡這句話。
因為在道路的前方正出現了一個人口買賣的市場。
Advertisement
說是人口買賣市場,其實也不過幾個奴隸販子在收購奴隸。
一堆走投無路的平民,或賣自,或賣子,著草標站在那里供奴隸販子挑挑揀揀。
如果挑中了,奴隸販子就和賣的人或者他們的父母簽下賣文書,用一小袋糧食把人換走。
領到一個燃著炭火的火盆邊上,拿起一個燒紅的烙鐵,滋啦一聲在那人的上烙上專屬標記,然后把所有新買的奴隸用鐵鏈銬一串。
不時的有一聲短促的慘聲,伴隨著烙鐵灼燒皮的聲音響起。
人群卻麻木而淡然,仿佛這只是理所應當,習以為常之事。
程千葉聞到空氣中約飄來一刺鼻的味道,看著那些不時冒出的白煙,伴著一聲聲慘呼,只覺得膽戰心驚。
突然回頭看了俯臥在車上的墨橋生一眼。
墨橋生正地打量著,被這猛得一回頭逮了個正著,躲避不及,急忙閃開目,紅了臉低聲說了一句:“主人還未曾給下奴賜印。”
他因為傷勢不便穿,只在腰上蓋著薄薄的一條錦被,出后背。
那兩塊形狀漂亮的肩胛骨上,重疊著顯眼的烙印,舊的烙印被燙去,新的印記隨意地加附其上。
賜你個鬼印,你居然還一副期待的樣子。
程千葉差點要罵人,忍了忍:“從今以后,自稱我,不許再稱七八糟的東西。”
墨橋生垂下了眼睫,抿了。
程千葉沒好氣的繼續看窗外。
一位衫襤褸的人,前坐著四個孩子,其中兩個孩子頭上著一草標。
不由吩咐停下馬車。
這個母親要把自己的孩子賣去做奴隸。
程千葉不敢想象,作為一個母親怎麼會舍得讓孩子,去承小墨曾經承過的那種遭遇。
Advertisement
那個母親形容枯槁,神態呆滯,仿佛一活著的行尸走。
程千葉不是沒有見過貧困的人,但是在生活在那個富足安定的世界,無論再怎麼想象,也沒有親眼見到這些孩子來得目驚心。
那幾個孩子,瘦到如同筷子一樣伶仃的四肢,深深凹陷而顯得巨大的眼睛,枯黃得和稻草一樣的頭發,簡直令人不忍直視。
蕭繡從車窗湊過腦袋來看著:“賣了總比死強。像我那死鬼老爹,就把我領到了一個人生地不的地方,哄我呆著等他,自己跑了。”
他像是說一個和自己毫無關系的故事,“不但浪費了一袋可以換回家的糧食,還害得我差點死街頭,真是蠢。”
程千葉覺得自己真的有必要轉換一下思維方式。
知道蕭繡的觀念才是正確的,當人的生存都還困難的時候,溫飽問題重于天理人倫和一切需求。
一個奴隸販子走到那個那母親面前,抓起年紀較小的那個孩,上下打量,又開看看了牙齒。
不滿意地搖頭放手:“長得還湊合,就是太瘦小了,說不定賜個印都熬不過。”
那位母親有力沒氣地回答:“半袋糧食就夠了。”
那奴隸販子滿意了,手去抓那個孩。
那瘦骨嶙峋的孩尖了起來,拼命往姐姐后躲。
的姐姐抱著,跪地磕頭,“主人把我一起買了吧,我長得沒妹妹漂亮,但我力氣大,能干活。”
奴隸販子一面拉扯,一面罵道:“死一邊去,我這是往窯子里供貨,買你這種賠錢貨來干啥?”
程千葉實在看不下去了,用手指敲了敲車窗,阻止了這場買賣。
沖蕭繡打了個眼。
蕭繡跳下車,隨手拋了一小錠碎銀子,抬了一下下,“跟我走,命真好,主公看上了你了。”
Advertisement
那奴隸販子,見著他們一行隨從眾多,排場浩大。
知道是一位貴人出行。不敢爭執,點頭哈腰地離開。
那妹妹拽住姐姐的服失聲痛哭,姐姐卻一把抹掉眼淚,把推了出去,“快去,那是一位貴人,有飯給你吃,不肚子。”
程千葉扶著額頭,沖蕭繡打了個一起帶走的手勢。
兩個衫襤褸的小孩登上了車,華干凈的馬車讓們無所適從,兩人在一起,畏畏的跪在角落里,用兩雙因為而顯得特別大的眼睛畏懼地看著程千葉。
本來寬敞的車廂,又添了兩人便顯得稍有些局促。
墨橋生撐著,挪了一下。為們騰出些空間。
蕭繡不滿地皺起鼻子,他覺得整個車廂多了一難聞的氣味。
但他從不違背程千葉的任何話語,因此沒有多言,只在香爐里狠狠地添了一大把香料。
程千葉放下簾子,閉上眼,隔離開外面那個充滿痛苦的世界。
那麼多的孩子和那麼多值得同的人,我這樣能救得了幾個。
雖然,我這主公只是吉祥一般的存在。但在找到回去的方法之前,我姑且也稍微盡職一點吧。
程千葉分外的想念起自己那個安全又溫馨的時代,想念起自己那真正一起長大的雙胞胎哥哥,和自己的那些家人朋友。
一行人駐西山的溫泉山莊,
那傳說中的月神泉,只是一道小小的月牙形泉眼。
四季恒溫的泉水帶著點淡淡的淺黃,水面蒸騰著裊裊白煙。
這座山莊的原主人顯然很懂得,在泉眼的沿邊砌上大塊的漢白玉,修筑了扶手的欄桿和坐浴的階梯,此外再無多余人工斧琢的痕跡。
溫泉四面種植著大片的楓樹林,此刻漫天紅葉如云,零星小葉飄搖墜水面,似幻還真,宛若仙境。
Advertisement
程千葉正沉醉于欣賞這片景之中,突然聽見蕭繡不悅的低聲斥責:“快下去,你這樣是干什麼?不識好歹的東西。”
程千葉看了過去,只見蕭繡和兩個侍從,正要將墨橋生抬泉中,墨橋生那骨節分明的手死死地抓住欄桿,不愿水,上泛起一代表恐懼的濃郁黑。
當看見程千葉看過來的時候,他上那圈顯眼的金邊亮了一下,把那黑強下去。
隨后他放棄掙扎,把自己沉水中。
程千葉到有些奇怪,走到泉邊,蹲下,看著泡在水中的墨橋生。
“你很怕水嗎?”
“不……不怕。”他雖然浸泡在溫熱的泉水中,卻面蒼白,全僵直,一直手拽住岸邊的扶手。
程千葉揮退了其余的人。
饒有興致地看了一會水中的墨橋生。
只見他抿著,保持著僵的姿勢一不,顯然是強忍著懼怕。
程千葉蹲在那里,出手輕輕了他的頭頂。
“小墨,我自從當了這個主公,每天都有很多人,對我說著各種好聽的,恭維的,關心的話語。可是我知道,他們都在騙我。”
慢慢取下墨橋生頭上的一片楓葉,看到那個漉漉的臉蛋,從水霧中抬起來著自己。
“我希你,能不騙我,好不好?”
“我……”一個低沉好聽的男音,從蒸騰的白煙中響起。
“我年之時,曾被賣楚懷館,那是一個男館。一進去里面,當時的主人就要訓練我取悅男人的技巧。”墨橋生低下頭,順的黑發垂落下來,遮住了眉眼。
“我那時候年紀太小,脾氣倔強,竟敢不服從主人的指令,拼死抗拒。主人懲罰我,把我按水缸中,瀕死之時,才提我上來。如此反復,延續數日。直至當時一個正紅的小倌看見了,為我說,把我安到他邊做侍從,方才停止那種懲。”
“雖然過去了很久,可是,我……我依舊有些怕水。”
“我,我雖然在小倌館待過,但那方面技巧,確,確實一點都不會。”
墨橋生忐忑地想:我咬了韓大人的手,又違逆前主人,都被主人知道了。他會不會厭惡我這種桀驁難馴的奴隸。
這時他到他的雙眼被一道黑的布條蒙上了。
邊響起有人水的聲音。
一只的手輕輕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別怕,我陪你泡一會。我會看著你,不會讓你掉進水中的。”
他聽見主人的聲音在耳邊響起。
“眼上的布帶不能摘哦。”
猜你喜歡
-
完結1347 章
權傾天下,攝政王強寵下堂妃
她是22世紀古醫世家傳人,藥毒雙絕。一朝穿越,成為天岱首富家的傻子二小姐,還被綁上花轎代姐出嫁。隻是她嫁的這位攝政王不但毀容跛腳,還是個暴力狂。她受儘羞辱,決定在逃跑前送他一頂有顏色的帽子以報“大恩”!誰知……*傳說,天岱攝政王鐵血冷酷,威震天下。傳說,天岱攝政王權傾朝野,手握重權,連皇帝也要忌憚。傳說,天岱攝政王容顏絕世,勾一勾唇,連天上神女也為之傾心。……夏淺墨隻想呸,傻子纔會為這個變態王爺傾心!可是,當攝政王拿下麵具,當一切的真相浮出水麵,夏淺墨看著那張攝魂奪魄的英俊容顏,眸中卻浮上詭笑。
245.2萬字8.18 67471 -
完結80 章

王府小妾
原名《梅素素古代記事》 梅素素穿成了一個古代小妾。 小妾有過兩個男人,前頭那個遭流放了,現在這個拿她當征服白月光的工具人,倒霉的是,白月光就是她前頭男人的正妻。 也就是說,等哪天白月光想通了,她也就混不下去了。 —— 全王府都知道,蘭馨苑那位才是王爺放在心尖尖上的人。 晉王殿下高傲冷漠、心狠手辣,誰都不放在眼里,唯獨對這位寵愛有加,將人偷偷藏在府中,什麼好的都緊著她,小院圍的跟鐵桶似的。 隨后進府的梅氏跟她比起來,待遇千差萬別。 梅素素心里也清楚自己的地位,所以面對晉王的寵愛,她從不動心,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跟他虛與委蛇,暗中想著法子離開這里。 直到那天白月光突然召見她,她就知道自己機會來了。 ......姬長淵知道梅素素離開的消息時,只是淡淡嗯了一聲,沒有多余的反應。 府里下人都以為王爺并沒有多喜歡梅主子,真正被他放在心頭上的還是蘭馨苑那位,連他自己都這麼認為。 直到后來,他才后知后覺發現,自己每次回府會下意識往一個方向走去,有時候睡著了,耳邊也不自禁聽到某人熟悉聲音,甚至忙的累了他會叫出一個名字...... 心里仿佛空了一塊,密密麻麻的疼。 他后悔了。 ps:女主沒心沒肺,男主追妻火葬場的故事,結局he,男女主非c......慎入...
33.3萬字8 31539 -
完結8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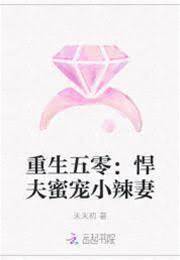
重生年代:悍夫蜜寵小辣妻
【無底線甜寵,1v1雙潔】 水落落穿越了,麵對一家子的極品,她乾脆利索的嫁人跑路,與其熬乾自己奉獻全家,她選擇獨自美麗。 洛水寒一輩子孤傲卻被一個小媳婦給打破,她每天都要親親抱抱舉高高,撒嬌賣萌毫無羞恥感。 直到有一天小媳婦要離婚。 洛水寒看著絞著手指的小女人:“離婚?” “不是你說我們不適合的嗎?”水落落好委屈,這個男人竟然凶她。 “抱也抱了,親也親了!你竟然敢要離婚?”男人的眼睛裡充滿了暴風雨來臨前幽深。 “誰,誰叫你老是嫌棄我的?”水落落炸毛吼道。 婆婆:離婚好呀,落落就可以做我好女兒了! 小姑子:離婚好呀,落落就冇有跟我搶了! 小叔子:離婚好呀,我就可以娶落落了! 男配一:同上 男配二:同上 …… 洛水寒:“都給老子爬!”
142.6萬字8 275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