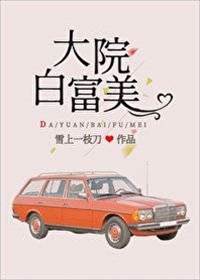《親昵》 第38章
傳話的士兵并未立刻離去, 而是又清了清嗓子,道:“秦營長,方隊說他一會兒還得開會,請您盡量快點。”
秦崢狠狠一個撞,嗓音極低:“行。”
“……”余兮兮眉頭蹙, 在他懷里劇烈顛簸,咬得發白, 用盡全力才克制住出聲的沖。
可桌子不固定,在沖力作用下往后移, 吱嘎一聲, 似不堪重負, 桌子腳也和水泥地面,噪音尖銳又刺耳。
門口的士兵:“……”
余兮兮驚得一, 嚇壞了, 慌忙用形抗議:“不要了,你快點兒出去。”
秦崢沒說話, 兩手分別穿過膝蓋彎的窩兒,一下抱起來, 墻上。背著墻, 纖細十指無意識地想抓住什麼, 然后抱住他脖子, 的,弱的抖如狂風暴雨中的一片葉。
他弓腰,激烈吻咬的舌和脖頸。
門外, 穿迷彩裝的年輕戰士一頭霧水,略上前,側耳去聽里邊兒。
沒什麼靜。
于是士兵試探著開口:“秦營長……”
懷里的軀頓時又不安地掙扎起來。秦崢眉心擰個川字,抱,暗暗咬牙:“你他媽還有事兒?”
這語氣沉不善,夾雜怒意,小戰士干咳一聲,連忙道:“沒、沒了。”隨后腳步聲很快遠離。
等士兵走遠,余兮兮再忍不住,咬著秦崢的肩膀小聲罵他,嗚咽低泣:“你、你簡直是個混球……”
他用力蹭蹭滾燙的臉蛋兒,低笑:“刺激?”
拿指甲狠狠掐他:“壞蛋!”
“噓。”
秦崢吻了吻的,嗓音低地哄:“乖點。況特殊,我爭取半小時之完事兒,回來再伺候你。”
結束時,外頭的天已經黑,幾只不出名兒的鳥矮矮飛過天空,往巢的方向歸去。訓練場上仍回響著戰士們的口號聲,洪亮渾厚,乍一聽,頗有幾分滌山河的氣勢。
Advertisement
秦崢緩緩退出去,綿綿的,臉頰乖巧著他的膛,平復呼吸,全上下的皮都蒙上一層薄。
他轉把放到床上,拿被子從腳裹到脖子,然后低頭,親吻汗的額頭,紅的臉頰,和略微紅腫的瓣。
余兮兮連說話都覺得費勁,了,嗓音:“再不走,你們那個方隊應該要等睡著了。”
秦崢笑,食指勾逗的下,“現在去也差不多”
眸閃了閃,“……會不會罰?”
“不會。”
他語氣很淡,撿起T恤和軍套上,扣皮帶,“不是什麼要事兒。”
余兮兮眨眼,好奇地湊近一分,“你怎麼知道?”
秦崢微挑眉:“猜的。”
剛才士兵來門兒,原話是“盡量快點”,給人留足余地,明顯不可能是什麼十萬火急的軍務。
聽出他敷衍,癟癟說了個“切”,隨后困意上頭,翻過,卷發在軍綠的枕頭上鋪陳開,像一匹墨的綢緞。
不多久,秦崢扯過外套隨手搭肩上,弓腰,腦袋,“先走了。”
余兮兮眼皮打架,懶懶地應道:“拜拜。”
他又親了下的鼻尖兒,“待會兒別忙洗澡。”
“為什麼呀?”
秦崢似笑非笑:“等我回來一起。”
怔了下,旋即反應過來他在打什麼注意,臉發熱,隔著被子踢過去一腳。他躲都不躲,挨完后上去,抬起的下又是一陣親吻,片刻道,“乖,閉眼睡覺。”
門開了,又關上。
天暗下去,夕殘留的芒已悉數被夜吞噬,屋子里逐漸變得黑漆漆。好在黑暗并未持續多久,走廊的燈亮了,白線依稀投進來。
余兮兮攏了攏被子,閉上眼睛。
Advertisement
耳畔,不知哪個方隊的兵唱起了軍歌,嗓門兒的,全靠喊,本聽不出調子:“軍號嘹亮步伐整齊,人民軍隊有鐵的紀律,服從命令是天職,條令條例要牢記……”
睡在駐地,聽著軍歌,忽然就想起了山狼,嘯天,逐日,想起軍犬兵李黝黑憨厚的臉,想起之前在基地工作的短短兩個月。那些日子,掙了余衛國的束縛,遠離了那個由富二代組的朋友圈,從事喜歡的職業,滿懷熱,努力上進,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可世事無常。后來,余衛國甩了一掌;再后來,嘯天和逐日因為的失誤藥中毒……
短短幾天,失去了父親,失去了親人,失去了工作,從云端跌落,摔進了泥地。
好在……
還有這個地方能躲。
“……”余兮兮沉默看著窗外,窗戶沒關,微涼的山風溫吹進來,帶著泥土味兒。自然的,清新的,聞不到任何工業痕跡。
這一刻,的心忽然就靜下來。
正神游天外,背包里的手機震起來。
余兮兮回魂兒,撐拿包,費力掏了半天才拿出來。一看來電顯示:李同志。
皺眉,別過頭用力清了清嗓子,然后才接起:“喂,小李同志?”
李的聲音從聽筒傳出,像是松了口氣,道:“謝天謝地。余醫生,你總算接電話了。”
“……你之前給我打過?”
“對啊。從昨兒晚上就開始打了,一直沒人接,我還以為你出什麼事兒了呢!”
余兮兮抱歉:“不好意思,之前一直沒看手機。”
“原來是這樣。”李嘀咕著,又關切地問:“那你還好吧?”
“沒什麼事。”道:“對了,嘯天和逐日的況怎麼樣?”
Advertisement
“我就是想跟你說這個。放心吧,那倆防暴犬已經沒大礙了。”李說著又嘆了口氣,有些憤然,“這事兒羅隊也太草率了,什麼都沒查清楚,居然就讓你……”
這孩子一貫單純善良,心眼兒實在。余兮兮有些無奈,說:“這事怎麼也怪不到羅隊頭上。你想,當時現場有那麼多領導,我一個實習醫師帶犬只已經不符規定了,他再不理我,整個基地都得倒霉。”
利害關系分析了,但李還是想不通,只道:“無論如何,你平時的工作況大家都有目共睹,我覺得這件事肯定有誤會!”
苦笑,“謝謝你相信我。”
那頭靜了半天,終于遲疑地問出一句:“余醫生,秦營長現在在石川峽,我聯系不上。要不,咱想辦法,托人跟他說一聲?”
聞言,余兮兮臉微沉,想也不想便道:“不必了。這件事暫時不要讓他知道。”
“啊?為什麼啊?”
“不為什麼。”余兮兮淡淡的,換另一只手拿手機,“總之你聽我的就好。”
見態度堅決,李也不好再多言,只囁嚅了下,道:“那,好吧。”
拂曉大隊立多年,期間,駐地搬遷三次,最終落腳在石川峽這個小縣城,深深扎。
暮中,一棟辦公樓矗立在宿舍區和醫院的左前方。四層高的樓房,占地面積不大,外觀老舊,墻面斑駁,遍布大片大片爬墻虎,看上去,很有些年頭了。
辦公室里,一個三十七八歲的男人站在窗邊兒煙,材健碩,相貌周正,青白的煙霧在間吞吐。
腳步聲從走廊的另一頭響起,略急促,然后,一個年輕士兵站在門口高聲喊:“報告!方隊,秦營長來了!”
Advertisement
“……”那人回頭,一把掐滅手里的煙,低聲嘀咕:“媽的,等了四十來分鐘,這臭小子。”
接著又是一陣腳步聲,速度也不慢,但穩健有力,教人聽不出毫慌張。他側目瞧門口,看見個拔高大的男人,迷彩短袖裹著一副結實軀,底下的格外長,抿,面容冷峻,沒什麼表。
秦崢站門口:“報告。”
方義武把手里的煙頭仍垃圾桶里,甩過去倆字兒:“進來!”
秦崢上前幾步,站定。
方義武繞到辦公桌后頭坐下,一轉頭,看見他前和后背的服全都是汗,整個人神清氣爽。不皺起眉:“四十分鐘之前蔣飛就回來了。結果你這會兒才來,干什麼去了?”
秦崢冷著臉,眉都沒一下,“拉稀。”
“……”方義武靜默,手點點他裳,“那這麼多汗?”
“天熱。”
“……”方隊一聲冷哼,懶得跟他鬼扯,后仰靠椅背,食指點桌面:“我聽說,你媳婦兒從云城跑過來探親了?”
“對。”
“之前你為什麼不給組織打報告?先斬后奏,符合哪門子規定?”
“之前也沒跟我打報告。”
方義武給氣得笑出來,“合著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兒,你教育媳婦兒教育得還功。”臉一沉,桌子敲得邦邦響:“當部隊是姥姥家呢,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
他面無表,沒吭聲。
部隊對家屬探親有規定,通常都要求家屬探親之前提申請。但規定是規定,許多戰士家屬怕申請失敗,在來部隊之前都不會提前打招呼,久而久之,大家也習以為常。
方義武罵完消了火,自然也沒真打算追究,只點了煙,不大自然地道:“家屬區那邊兒收拾出來了麼?要實在嫌臟嫌麻煩,就住你嫂子那屋去,前幾天剛走,屋里干凈,床單被套也有新的。”
秦崢沒什麼語氣,“不用。我媳婦兒跟我睡。”
方義武嗤:“一米二的床,你他媽那麼大塊頭,怎麼睡?”
秦崢淡淡看他一眼:“這他媽也要匯報?”
“……”
方義武被煙嗆得咳嗽一聲,頓幾秒,道,“怎麼睡怎麼睡,誰稀得管你……”說完用力清了清嗓子,手指秦崢,聲音低:“先說清楚,這里是駐地,你給老子悠著點兒。帶好手底下的兵,抓安排各項訓練,別天尋思搞那個。”
一個多月未見,秦崢忍耐太久,需索起來便半點不知節制。當晚,余兮兮累得散架,直到凌晨四點多才終于有機會休息。
蜷小小一團,腰間沉重,男人從背后摟,軀嚴合。
須臾,低沉嗓音從耳朵邊響起,聲問:“疼不疼?”
“……”余兮兮下意識地脖子,搖頭,忽然又想起什麼,轉過,雙頰通紅,聲音小得像蚊子:“你、你又全都弄進去了?”
秦崢一臉平靜地點頭,“嗯。”
余兮兮無語,拉高被子蓋住整張臉,有點想哭:“沒什麼,晚安。”
這個男人似乎毫不介意會不會懷孕,之前提過,他反而一臉淡然地說有了就生。很佩服,這心態著實是太好了點兒。
次日,石川峽迎來個云朗風清的好天氣。
秦崢今天給手下的兵派了野外偵察訓練,六點整,分隊準時集合出發。余兮兮迷糊睜開眼,將好聽見軍卡的引擎轟隆,載著一車的人平緩馳出駐地。
再次醒來已經是上午九點多。
起床簡單梳洗了一番,列了個清單,填了張出門條,然后便走出大門,準備去縣城中心買東西。
石川峽并不發達,沒有滴滴也沒有優步,沿著大路往前走,好半晌才攔下一輛電三車。
車主是個頭發花白的大爺,要價公道,去縣城中心只收七塊錢。余兮兮沒還價,直接坐了上去。
大爺樂呵呵的,隨口問:“姑娘哪兒人吶?”
“哦,云城的。”
“難怪,我就說像云城口音。”大爺笑起來,“來石川峽玩?”
余兮兮不好多說,也笑笑,“差不多。”
大爺說:“來這兒就對啦。我們這兒可是好地方,山好水好,比你們大城市養人。”
一路閑聊,不知不覺周圍就熱鬧起來。
大爺把余兮兮放下來,又熱心地給指路:“你要買東西,這條路往左走就有個超市。要吃飯的話咧,有一家豆花魚不錯,也在這條路上,生意好得很。”
“謝謝啊大爺。”
余兮兮揮了揮手,轉過,順著下坡路筆直往前。
街道上,時不時就能遇見些穿草鞋,背背篼的人,蔸里玉米蔬菜裝得滿滿,抄著一口本地方言,有說有笑。
鄉下景象余兮兮沒見過,覺得新奇,趕拿出手機拍拍錄錄。
左轉時沒留神兒,腳下一崴,被什麼東西給絆了下。
“……”余兮兮低呼著摔倒下去,屁鈍痛,頭昏眼花。
街邊兒一個人目睹這一幕,慢悠悠走過來,嗓門兒拔高,“張媽,你家孫子又調皮,把椅子搬到路中間,還摔著人了咧!”
接著就是一個中年婦人驚乍乍的罵聲:“哎呀這個死娃娃!”
一時間,小孩兒的哭聲和大人的打罵聲織片。
隨后又是那個人的聲音,輕描淡寫的:“來,我拉你。”
“……”余兮兮甩了甩頭,目落在那只手上:白膩,指纖細,小拇指上套著一個上佳的翡翠戒指,極其地養尊優。
微怔,目從頭到腳打量那人--
三十五歲上下,卷發懶盤,皮雪白,上穿牡丹刺繡旗袍,細腰翹,曲線曼妙。細細的眉細細的眼,涂著艷紅膏,這五,拆分開來并不算出眾,但組合在一起卻極有味道,曼麗,妖嬈,風萬種。
余兮兮握住了那只手,人把拉了起來。
“謝謝啊……”
“不客氣。”人勾角,“小妹妹,出門要看路。”說完轉過,里哼曲兒,款款進了一家黑漆漆的門店。
這種小地方,居然能見到這麼漂亮的人。
余兮兮來了幾分興致,視線上移,看向那家店的招牌:一夜酒吧。
:“……”
猜你喜歡
-
完結88 章

和周先生先婚後愛
婚後,宋顏初被周先生寵上了天。 她覺得很奇怪,夜裡逼問周先生,“為什麼要和我結婚,對我這麼好?” 周先生食饜了,圈著她的腰肢,眼眸含笑,“周太太,分明是你說的。” 什麼是她說的?? —— 七年前,畢業晚會上,宋顏初喝得酩酊大醉,堵住了走廊上的周郝。 周郝看著她,隻聽她醉醺醺地歪頭道:“七年後,你要是還喜歡我,我就嫁給你吧!” 少年明知醉話不算數,但他還是拿出手機,溫聲誘哄,“宋顏初,你說什麼,我冇聽清。” 小姑娘蹙著眉,音量放大,“我說!周郝,如果七年後你還喜歡我,我就嫁給你!”
13.1萬字8.09 58565 -
完結280 章

總裁夫人她馬甲轟動全城了
前世,花堇一被矇騙多年,一身精湛的醫術被埋冇,像小醜一樣活了十三年,臨死之前她才知道所有的一切不過是場巨大陰謀。重生後,她借病唯由獨自回到老家生活,實則是踏入醫學界,靠一雙手、一身醫術救了不少人。三年後她王者歸來,絕地成神!先替自己報仇雪恨,嚴懲渣男惡女;同時憑藉最強大腦,多方麵發展自己的愛好,畫家、寫作、賭石...隻要她喜歡,她都去做!她披著馬甲在各個行業大放光芒!權勢滔天,富豪榜排名第一大總裁席北言:媳婦,看看我,求求了!餘生所有,夢想、榮耀、你。
51.6萬字8 29860 -
完結2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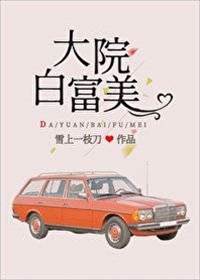
七零大院白富美
別名:大院白富美 肖姍是真正的天之驕女。 爸爸是少將,媽媽是院長,大哥是法官,二哥是醫生,姐姐是科學家。 可惜,任性的她在婚姻上吃了虧,還不止一次。 二十二歲時,她嫁給了識于少時的初戀,可惜對方是個不折不扣的渣男,兩年后離婚。 但她并沒為此氣餒,覺得結婚這事兒,一次就美滿的也不太多。 二十六歲再婚,一年後離婚。 三十二歲三婚,閃婚閃離。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集齊了極品婆婆,極品小姑子,極品公公之後,她終於遇上了最適合的人。 三十五歲肖姍四婚,嫁給了最後一任丈夫趙明山,二人一見鍾情,琴瑟和鳴,恩愛一秀就是幾十年。 重生後,她麻溜的繞過一,二,三任前夫,直接走到趙明山的面前,用熱辣辣的目光看著他, “哎,你什麼時候娶我啊?” 趙明山一愣,肩上的貨箱差點砸到腳了。
97萬字8 12440 -
完結1436 章

我在娛樂圈修仙
【女強+絕寵+修仙】暴發戶之女林芮,從小到大欺女霸男,無惡不作。最後出了意外,一縷異世香魂在這個身體裡麵甦醒了過來。最強女仙林芮看了看鏡子裡麵畫著煙燻妝,染著五顏六色頭髮的模樣,嘴角抽了抽。這……什麼玩意兒?! “雲先生,林影後的威亞斷了,就剩下一根,她還在上麵飛!” “冇事。”雲澤語氣自豪。 “雲先生,林影後去原始森林參加真人秀,竟然帶回來一群野獸!” “隨她。”雲澤語氣寵溺。 “雲先生,林影後的緋聞上熱搜了,據說林影後跟一個神秘男人……咦,雲先生呢?” (推薦酒哥火文《我,異能女主,超兇的》)
135.2萬字8 23125 -
完結169 章

勾月亮
『特警隊長×新聞記者』久別重逢,夏唯躲著前男友走。對他的形容詞隻有渣男,花心,頂著一張帥掉渣的臉招搖撞騙。夏唯說:“我已經不喜歡你了。”江焱回她:“沒關係,玩我也行。”沒人知道,多少個熬夜的晚上,他腦海裏全是夏唯的模樣,在分開的兩年裏,他在腦海裏已經有千萬種和她重逢的場麵。認識他們的都知道,江焱隻會給夏唯低頭。小劇場:?懷城大學邀請分校特警學院的江焱學長來校講話。江焱把她抵在第一次見她的籃球場觀眾席上撕咬耳垂。他站在臺上講話結束後,有學弟學妹想要八卦他的感情生活,江焱充滿寵溺的眼神落在觀眾席的某個座位上。一身西裝加上他令人發指的魅力,看向觀眾席的一側,字音沉穩堅定:“給你們介紹一下,你們新聞係的19級係花小學姐,是我的江太太。”--婚後有天夏唯突然問他:“你第一次見我,除了想追我,還有沒有別的想法?”他低頭吻了吻女孩,聲音帶著啞:“還想娶你。”他擁抱住了世間唯一的月亮......於是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他江焱——已婚!〖小甜餅?破鏡重圓?治愈?雙潔〗
28.6萬字8 75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