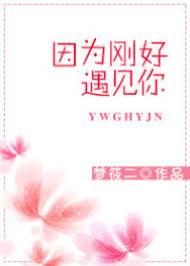《在暴戾的他懷里撒個嬌》 第21章 彩虹糖
家里有錢有勢的在德新高中并不見, 不過這里面又分為兩批,一是家里有勢的, 這些家庭的小孩因為嚴苛的家教, 都被管束得相當謹慎持重, 平日里很是低調, 避免坑爹。
還有一類就是家里有錢的,而且是那種短時間里暴富起來的家庭, 這類家庭的小孩以前過欺,現在有了倚仗, 便在校園里作威作福欺負弱小,但是真的遇到牛的大佬, 譬如上一類家庭的小孩, 他們也是不敢太過分, 避著走的。
姚武便算第二類, 欺怕他是行家, 平日里他很看不慣謝隨, 謝隨家里什麼都算不上,憑拳頭, 怕他個屁啊,自己家里有錢,欺負死他!
然而,這次事卻讓姚武看明白了,謝隨牛,不僅靠拳頭, 還因為他邊有一幫講義氣的兄弟,而這些兄弟里,不人家境都很不錯,無論謝隨落到何種境地,他們都會無條件地站在他邊。
而姚武自己呢,那些過去跟著他吃喝玩樂的所謂“哥們”,在他出事的時候,沒一個站出來幫他出頭。
謝隨把他到天臺去的時候,那些“哥們”畏畏地推說自己有事,不敢跟著他一起去天臺壯大聲勢,還是姚武提出,跟他一起去的每個人都有錢拿,這才勉強了幾人上天臺。
天臺,狂風呼嘯著,謝隨站在階梯邊,居高臨下地著他,宛如看著一條喪家之犬。
他邊的叢喻舟幾人,坐在欄桿上,神很不屑。
“謝隨,不想道歉也行。”
姚武知道謝隨的格,絕對不會道歉,所以他早就想好了整治他的后招——
“聽說你玩賽車厲害,咱們賭一局,你贏了,這件事一筆勾銷,如果你輸了,你以后見著我,都給我繞路走。”
Advertisement
叢喻舟幾人笑了起來:“就你這慫貨,還想跟我們隨哥賽車?”
“敢不敢,一句話。”
謝隨走到他面前,面無表道:“可以,但是修改一下。”
姚武問:“修改什麼?”
“如果你輸了,轉班,學校見我繞道走,他媽在我面前晃。”
姚武早就已經謀劃好了,所以滿口答應了下來。
他離開以后,叢喻舟對謝隨說:“況不對勁,就那種家伙敢跟你玩賽車,肯定沒安好心,指不定背后會使什麼招。”
謝隨漫不經心道:“背后對老子使招的人還了?”
這些年爬滾打,什麼招他沒領過,還不是這麼過來了,他謝隨怕過誰,他什麼都不怕。
放學的時間,謝隨和幾個朋友從教學樓出來。
寂白推著車從自行車棚出來,停在梧桐樹下,顯然是在等他。
看著咬著下言又止的模樣,謝隨無可奈何地回頭問:“賽車的事,誰給講了?”
蔣仲寧手肘推了推叢喻舟,叢喻舟瞪了他一眼,解釋道:“不是,隨哥,主要這個寂小白套話功夫一流,三言兩語就讓繞進去了,實在沒辦法啊,隨哥,這丫頭不簡單,你要跟周旋得長二十個心眼才行啊。”
謝隨翻了個白眼,一小丫頭,還能把他吃了不?
幾個哥們推推搡搡地離開了,謝隨散漫地溜達到梧桐樹下,順手把寂白的車給推走了:“已經決定的事,就不用勸了,我不會聽。”
寂白抿抿,還沒開口,卻見他瞇起眼睛著樹梢,溫地說道:“我只聽我朋友的話,當我朋友,什麼都聽你的。”
“......”
他繞來繞去,就繞不開這個事了是吧!
“謝隨,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為什麼要鬧這麼大。”
Advertisement
寂白有時候,真的很不能理解謝隨,他總是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
謝隨沒接話,繼續道:“對不起三個字,有這麼難嗎?”
“叮!”謝隨打了打清脆的車鈴:“你再多說一個字,我會生氣。”
他這話說得平靜,眼底已經蓄了不滿的緒。
寂白的手握了握拳,又緩緩地松開,最后,還是忍不住低聲嘀咕道:“你要是覺得拉不下面子,我...我去幫你道歉,總行了吧。”
只聽“砰”的一聲,謝隨將自行車狠狠地往路邊一擲:“你聽不懂我的話,還是覺得老子不舍得罵你,讓人去幫我道歉,我什麼了!”
周圍有不同學,都被突如其來的靜驚了驚,朝他們投來好奇的目。
寂白被他突然兇了一下子,眼睛瞬間紅了,一言未發推起自行車。
自行車的椅子都歪了,騎也騎不了,推著車氣呼呼地往前走。
放心不下他到去和人賽車,怕他真的出意外,現在反倒了不好了...
寂白覺得自己真的是瞎心,家里的問題都自顧不暇,還去到管閑事,人家本不買賬,還兇。
怎樣怎樣,就算出事了,也跟沒有關系,又不給他當老婆,管他那檔子玩意兒會不會白瞎了!
謝隨原地站了幾秒鐘,著額頭,心煩躁至極。
看著眼睛泛了紅,他瞬間就后悔了,心疼了,恨不能給自己一掌。
該死!
他糾結了片刻,還是小跑著追了上去,奪過了手里的自行車,檢查坐墊,沉聲道:“還沒太嚴重,我給你修好。”
“走開!”
寂白看也不看他,奪車走,可是謝隨也沒有松手,兩個人僵持不下。
“小白,你知道我脾氣不好,你原諒我一次,行不。”
Advertisement
寂白急促地呼吸著,垂首不說話,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委屈了。
寂緋緋在家里作天作地,威脅污蔑,都從來不委屈,可是面對謝隨,哪怕有一點點的不順遂,都會讓的心思格外敏。
謝隨握住了纖細的手腕,用力地攥著,低聲懇求道:“我以后不會了,再也不會了,我他媽再這樣,我...”
他從包里出折疊刀,遞到的手里:“你捅我一刀解氣。”
“......”
神經病!
寂白將折疊刀和自行車一起往他懷里一推:“修好了還我,然后不要出現在我面前了。”
說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謝隨低頭看著自行車歪斜的座椅,微微蹙起了眉頭,跟著罵了聲王八蛋。
后幾個看熱鬧的哥們騎著車走過來:“喲,隨哥罵誰呢!”
“罵我自己。”
叢喻舟笑了起來:“隨哥你這認錯的姿勢,還他媽刀子了,真的牛,哥幾個服。”
“想死嗎。”
“隨哥,孩子不是這麼追的,別說還沒追到手,就是追到了你都不能兇,你一兇,人家就哭,那最后心疼的還不是你自個兒嗎,你得溫,惹人家生氣了,你就得送禮,賠禮道歉。”
“送禮?”
“對啊,你看看那些給你送禮的孩,可不就是為了討你喜歡嗎。”
謝隨若有所思地想了想,忽然明白了什麼,推著車加快步伐離開:“晚點去拳室,不用等我。”
……
次日清晨,寂白提前了半個小時出發,步行來到了學校,權當是鍛煉。
冬日早晨白霧彌漫,空氣中漫著淡淡的水霧顆粒,這并非是空氣污染的霾,像是加里打出來的輕薄細膩的煙,令人神清氣爽。
Advertisement
寂白走進校園的時候,已經從正東方逸夫樓頂冉冉升起了。
經過自行車棚,無意間朝里面瞥了眼,第二排固定停車的位置上,白的自行車規規矩矩地停靠在那兒,車干凈如新,就連胎的鐵都被拭得锃亮。
走到自行車邊檢查了一下,坐墊已經被調整的四平八穩,車鏈子上也刷了潤油,車胎加足了氣。
整個自行車煥然一新。
還算滿意地拍了拍車坐墊。
車籃子里好像裝了什麼東西,寂白手將籃子里的小瓶子拿起來,居然是一盒彩虹糖。
瓶子上著一張便箋紙,寫著三個字——
“對不起。”
年的字便如同他的格一般,張揚不羈。
原來他會說這三個字,還以為骨頭多呢。
寂白從瓶子里磕出一顆彩虹糖,彩虹糖顧名思義,七種的的糖粒,像藥片一樣,不同的糖片的味道也不一樣。
寂白知道,謝隨不喜歡吃甜點,可是獨獨喜歡彩虹糖。他上一世說過,彩虹糖在吃進里之前,你永遠不會知道那是什麼味道,是酸的、甜的,菠蘿的還是草莓味的...
蛋的人生,偶爾也需要一點驚喜,不是嗎。
就像他那天下午無意間拐到民生路24號,從副食店出來,買了包煙,煙叼在里還沒點燃,不早一刻也不晚一刻,寂白穿著病號服,渾渾噩噩地撲過來,暈倒在了他的腳邊。
那是他這幾年平淡如水的人生里吃到的第一顆彩虹糖,草莓口味的。
后來他很喜歡喂吃彩虹糖,無論是在拉琴的時候,還是看電視的時候,甚至,在奄奄一息的時候...
他喂吃的最后一顆彩虹糖,也是草莓味的。
寂白看著那盒彩虹糖,眼睛有些紅,知道自己不太適合過多回想上一世的事,因為對這個世界上的人來說,那些都是沒有發生的事,那些深刻而悲傷的緒,也只不過庸人自擾而已。
寂白了眼睛,將彩虹糖小心翼翼地揣進了包里,轉回了教學樓。
樓頂,謝隨和叢喻舟他們趴在臺上,朝樓下觀著。
周遭漫著晨霧,看得不是特別清楚,叢喻舟很興地拍著他的肩膀說:“看樣子,寂小白是收下了,這下可以放心了吧,隨哥。”
謝隨嚼著口香糖,眉心微蹙著,漆黑的眸子里蘊著深沉的底。
不知道是不是他看錯了,孩轉的時候,好像抹了抹眼淚,霧氣太朦朧,他看不真切。
他呼出一口白霧,縷縷的疼意漫五臟六腑。
猜你喜歡
-
完結653 章

陰妻獻祭:冥王纏上身
家鄉受難,父母至親慘死,因為他的出現,我活了下來。他是冥王,也是我的老公,我很小就被祭獻給他,所以我的命也是他的。為了找出全村人消失的真相,我為他所用,整天與鬼作伴、為他送陰魂、養鬼胎。直到有一天,他爬上我的床,將我壓在身下,「洛青檸,你人都是我的,何況你的身體,滿足我的需求,自然會得到你想要的……」
110.5萬字8 11752 -
完結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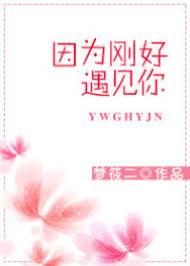
因為剛好遇見你
【文案一】 近日,向來低調的互聯網大亨顧琰,被網友拍到跟一美女深夜逛棧橋。 兩人的牽手照迅速占據各大娛樂版、財經版的頭條。 昨晚,又有網友曝出容深跟一美女同進同出某酒店的照片。 網友發現:照片里的美女可不就是前幾天跟顧琰夜游棧橋的那位? 而容深是誰? 容深是顧琰的競爭對手?? 吃瓜群眾一片沸騰,趕緊搬著小板凳前排坐好,靜等著年度qíng感大戲jīng彩上演。 【文案二】 某天,發小調侃顧琰:“你這個萬年大冰川,鉆井平臺都鉆不透,邱黎是怎麼把你搞定的?” 顧琰指尖把玩著煙,沒吱聲。 怎麼搞定的? 邱黎沒搞定他。 而是他縱容并寵溺邱黎在他的世界里撒嬌、任xing甚至是霸道。 人設:互聯網大亨VS互聯網B2B平臺創業者
17.4萬字8.18 38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