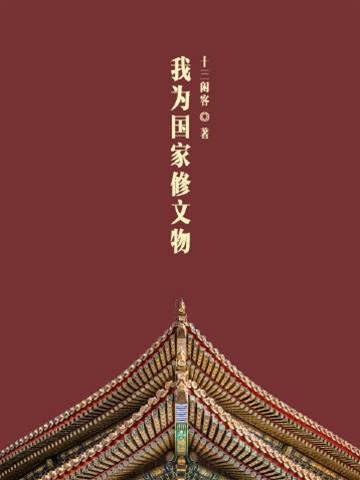《官道桃花緣》 第五十六章 湯書記的愛好
晚上,三個老同學聚在一起吃飯。
吳承耀道:“這個張老還真是個怪人,要麽就不幫忙,幫忙又不收錢,他這生意是怎麽做的?”
譚誌方道:“這個你們就不懂了,我師父屬於奇人異士那種。別看他一把年紀,是是非非心裏清楚得很。”
譚誌方端起杯子,“其實今天這事,還多虧了左曉靜,要不是在師父麵前說好話,事就沒這麽順利羅。”
顧秋道:“不管怎麽說,辛苦兩位了,來,我敬你們一杯酒。”
喝了這杯酒,吳承耀又發揮了記者的特強,“那個左曉靜是什麽人?我看對書畫在行的。”
譚誌方開起了玩笑,“你不會看上了吧?人家還是大二的學生,手下留吧!”
“切!分明就是你喜歡人家,瞎子都看得出來。”
譚誌方老臉一紅,“能不揭人家短麽?”
顧秋看著兩人鬥,這兩家夥隻要在一起,從來都沒消停過。吳承耀道:“不過據我以記者的眼來看,誌方,你恐怕是單相思一場。左曉靜這孩子的確很可,但長大以後,絕對看不上你的。”
“草,有你這麽打擊人嗎?我們還是不是兄弟?”
吳承耀道:“我這是在幫你,別陷太深。這丫頭,得很。”
Advertisement
“丫的,你什麽時候學會看相了?”譚誌方不服氣的。
顧秋道:“別鬧了行不?喝酒!”
兩人停下來,端起酒杯喝酒。
顧秋心道:“這個左曉靜,對書畫方麵的知識如此淵博,看來也非等閑之輩。”想到自己在南省,沒有任何助力,顧秋又有些心事重重。
從政軍事件,很可能激發兩大勢力之間的爭鬥。如果說以前是暗鬥,現在多半會明鬥。何縣長已經按耐不住了,正蠢蠢。
顧秋吩咐兩人,字畫的事,絕對不可以告訴任何人。
在省城呆了二天,張老已經把顧秋的字裱好。
顧秋接在手裏,激萬千,給張老錢,他堅決不。顧秋隻得謝過張老,別了吳承耀和譚誌方,連夜趕回縣城。
此番回來,比預定的時間,又早了一天。
從彤此刻已經焦急如焚,見到顧秋,忍不住撲進他懷裏痛哭起來。顧秋安了好一陣,才止住哭泣,抹了淚水。
“你最好是今天晚上送過去,湯書記應該在家的。”
從彤哪知道這是什麽?抱在懷裏,“這是什麽?”
顧秋道:“一幅前輩的字,我猜湯書記肯定喜歡。”
從彤很快就明白了他的用意,“行嗎?”
“行不行,試試總不會有害,你媽媽一起去。”顧秋是擔心不夠份量,從彤點點頭,“好吧!我這就回去。”
Advertisement
從夫人這幾天可憔悴了許多,臉上明顯了往日裏那種冷漠,多了一憂鬱與消沉。從彤回來,立刻迎上去,“彤彤,怎麽樣了?”
見從彤抱回來一個長方的盒子,“這是什麽?”
從彤道:“打開看看!”
將盒子打開,拿出顧秋寫的那幅字。
“好漂亮的書法!彤彤,這是哪來的?”
從夫人雖然傲慢,但畢竟是書香門第出,對書畫也有些見聞。眼前這幅破陣子,讓欣喜不已。
“這是顧秋花了兩天時間,日夜兼程,從老家拿來的,希能幫得上忙。”
從夫人臉上閃過一複雜的表,一直反對從彤與顧秋談,沒想到關鍵時候,還是顧秋肯幫忙。也去求過謝家,謝畢升隻應著好說,好說,卻不行。
從夫人知道,湯書記的字寫得不怎麽樣,但喜歡收藏。
不知道幕的,還道他是個雅士,其實湯書記隻是別有深意。
母倆人來到湯書記家裏,開門的是他家的保姆。
從夫人說明來意,保姆道:“你們等一下。”
砰!
門又關上了,母倆人心裏一,熬了大約五六分鍾,保姆才出來開門。“進來吧!”
見到湯書記,湯書記坐在寬大的沙發上,目掃了眼這對母,“有事嗎?”
Advertisement
從夫人道:“湯書記,我家彤彤今天從老家回來,在老宅裏找到這個,不知道湯書記喜不喜歡。”
從彤立刻拿出那幅字,當然不知道這玩藝就是顧秋弄出來的,如果知道的話,從彤哪裏敢來?
打開這幅字,上麵的書法,果然是龍飛舞,靈蛇穿梭。鄭之秋先生的字,不拘一格,有著自己的風格,有人能模仿。正因為他放不羈的個,被人稱之為鄭瘋子。
湯書記看在眼裏,見是鄭之秋的真跡,心裏暗暗震驚。
好字!果然是好字!
真沒想到從家的寶貝還真不,湯書記不聲,“你們先回去吧,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難道你們自己都對從政軍都沒有信心嗎?”
從彤聽出了話裏的弦機,忙暗示了老媽,“那就打擾湯書記了。”
走到門口,聽到湯書記道:“把你們那些煙酒帶回去,別搞這一套。影響不好。”
煙酒帶回去,意味著這幅字他就笑納了。
從彤一付很老實的模樣,接過保姆手中的煙酒,匆匆而退。
湯書記拿了那幅字,來到二樓書房。
越看,越是不釋手。
但他又不敢確定,這是不是鄭瘋子的真跡。不過怎麽說,這字,寫得真漂亮。掛在書房裏也風雅。
Advertisement
鈴--!!!!!
電話響起,湯書記立刻走過去,“喂!”
“立業同誌,是我!老左。”
“哦,左部長,您好,您好!”
左部長說話,總是慢吞吞的,一點都不急,隻聽到他緩緩道:“從政軍同誌到底是怎麽回事?有進展嗎?”
湯書記道:“暫時沒什麽進展。”
“算了吧,多大的事?鬧大了,影響不好。”
“我知道了,知道了,請左部長放心。”
掛了電話,湯書記籲了口氣,從政軍跟左部長沒什麽啊?怎麽連左部長都給他說了?看來這事還真不能再查下去。
ps:好久沒吼了,吼兩聲看!
書評一片冷清!兄弟們,起來!
有什麽想法就說吧,不說我怎麽知道呢?嗬嗬……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