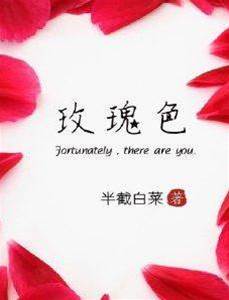《虐文女主只想煉丹》 第102章 尾聲二
蔣寒秋和金竹等人正和魔修纏斗, 互聽水晶祭臺傳來“轟隆”一聲巨響,循聲去,只見水晶石中一人下墜, 一眨眼功夫便不見了。
蔣寒秋一劍斬下面前一個魔修的頭顱,踏劍向祭臺飛去。
不等飛至,裂兩半的祭臺訇然合攏, 祭臺部紫紅芒一閃,整座祭臺竟然在眾目睽睽之下,憑空消失了。
不但祭臺和通往地下的水晶階梯無影無蹤, 連峽谷中央那個巨大的深坑也不見了,竟了一片平地, 與周圍沒有半點區別。
蔣寒秋不信這個邪,在半空中揮劍一劈, 排山倒海的劍氣震得山谷一,地面裂開一條一丈來寬的隙, 往下一看, 裂中只有褐紅的土壤。
“蘇毓!”蔣寒秋對著裂吼道。
抬腳一踹,把一塊紫水晶踹進裂中:“死出來你這禍害!”
一邊罵一邊舉起劍, 正要再劈,胳膊被一人拽住。
“大師姐, 別擔心,”金竹道,“師叔沒那麼容易出事……”
“我是怕他出事嗎?”蔣寒秋忿忿道,“我是怕他死了不能跟小師妹代!”
師兄弟幾個不約而同想起小頂生死未卜那三年, 誰都經不住這樣的事再來一次。
蔣寒秋見他們一個個蔫頭耷腦的,反倒迅速鎮定下來,在他們背上挨個拍了一下:“禍害千年,那玩意兒死不了,都給我振作起來!多殺幾個魔修去!”
眾人聞言一振,對啊,禍害千年,像師叔這種尖酸刻薄、冷心冷肺、睚眥必報、錙銖必較,討人嫌到極點的貨,應該與天地同壽才對。
“對了,小師妹呢?”蔣寒秋猛然想起來。
金竹道:“師叔給了我一只同心鈴。”
他說著從袖中取出鈴鐺,一邊訣一邊晃了晃,他這邊鈴鐺一晃,對方的鈴鐺也會共鳴,他就能據此判斷對方所在。
Advertisement
他聽辨了片刻,后背上一涼:“小師妹……在地下。”
……
蘇毓只覺耳邊風聲呼嘯,迅速墜落。
他強行穩住心神,以手訣,施了個回風咒,一勁風自下吹來,像一只溫的手托住了他。
下墜之勢漸緩,但與此同時,他的氣海慢慢凝滯,直至凝固,再也掀不起一波瀾。
片刻后,他的雙腳落在某種堅實平的東西上。
蘇毓從袖中取出顆夜明珠一照,發現自己站在一水晶柱的頂端,落腳之只有五六尺見方,四周便是萬丈深淵。
顧蒼舒空冷的笑聲忽遠忽近,在四周回翔:“阿兄,這是弟弟給你選的墳冢,如何?”
蘇毓心臟一,立即熄了夜明珠。
手不由自主地握拳,隨即緩緩松開。
他本來百思不得其解,那人為何要在殺死他母親后將尸保存在玄冰棺中,如今終于明白了。
母親死時懷有孕,尸放在玄冰棺中,腹中胎兒便隨著母一起凍結,不生不死。
他能預見后事,自然可以設計娶顧英瑤,也能算到何時誕下私生子,還能算到顧老宗主會用別的孩子調換。
他只需算好時機,掘墓開棺,取出尸首,將母子制傀儡人,再將自己的孩子神不知鬼不覺地換進顧家。
他明面上是個窩囊的贅婿,被人戲稱為“傀儡”,殊不知顧氏一門盡在他掌之中。
蘇毓依稀記得那人喜歡弈棋,無事便與母親對局,興致來時便將他抱在膝上,教他如何布局。
他很喜歡那樣依偎在父親溫暖的懷抱中,由他握著自己的手,“啪嗒啪嗒”地落子,卻不知他們從一開始就被他擺到了棋枰上。
顧蒼舒的笑聲不絕于耳,夾雜著毒蛇吐信似的咝咝聲,辨不清來,時而在頭頂,視而在腳下,時而又來自四面八方,似乎無不在。
Advertisement
蘇毓心中毫無波瀾,亦不會為他所擾。
這只是個任人擺布的傀儡罷了。
蘇毓熄了夜明珠,向無盡的黑暗了一眼:“顧清瀟,出來。”
陣陣回聲從空谷中傳來。
良久,有人輕聲道:“阿毓,許久未見。”
那口吻與他所知的“顧清瀟”判若兩人,與他記憶中的如出一轍,溫文爾雅、謙遜有禮,卻絕沒有人敢輕忽。
蘇毓握手中的本命劍,冷笑道:“做小伏低這麼多年,真是難為你。”
那人寬容地一笑:“你長今日這副模樣,實在出乎爹爹的意料。”
就在這時,耳畔忽然傳來疾風之聲,蘇毓一偏頭,帶著鱗刺倒鉤的鞭梢堪堪從他臉側過。
顧蒼舒得意道:“阿兄,承讓了。”
蘇毓臉頰上傳來針扎般的刺痛,從傷口滲出來,順著他臉頰往下淌。
破相了,他心道,這下蕭姑娘又得生氣了。
這種時候竟然還心這種事,連他自己都覺不可思議。
然而這念頭就像一涓涓暖流,流過他心上封凍的荒原,僵冷的里又有了些微暖意。
周遭一片黑暗,顧蒼舒是邪魔之,而他卻不能用靈力,所能依仗的唯有手中三尺長劍。
比起西極取藥那回,這次的兇險又不啻十倍百倍。
蘇毓沉下心來,從風聲中聽辨鞭子的來向和招式,舉劍格擋,在方寸之間閃轉騰挪,如泰山之穩,如風電迅烈,只聽劍刃與玄鐵鞭“叮叮當當”相擊不停,電迸濺。
顧蒼舒以為將蘇毓至歸墟之上,他不能用靈力,取勝定然易如反掌,誰知他的劍法出神化、變幻莫測,劍招不風,幾乎無隙可乘,他方才在祭臺上了無數道劍傷,修補傷口耗費了大量魔氣,此時也已所剩無幾,不敢孤注一擲。
Advertisement
顧清瀟道:“好,你的劍已臻化境,將連山劍的‘蹈虛抵隙,見機生’發揮到了極致,凌厲更勝爹爹當年。”
頓了頓:“舒兒,你的鞭法還稚了些,還需磨礪。”
顧蒼舒心中升騰起怒焰,從牙中出一句:“爹爹教訓的是。”
他說著,暗暗將所剩的魔氣全部貫鞭中,猛然向著蘇毓腳下的水晶石柱斜過去,這一鞭挾著萬鈞之力,若是擊中,脆弱的晶石柱定會斷裂,蘇毓便會葬深淵之下。
蘇毓未及細思,一招天霜橫劍揮出,他忽然到腳下的深淵中有什麼了,他的氣海也隨之一。
靈力陡然從經脈中奔涌而出,與平生所學盡付于這一劍,凜冽蕭索的劍意如雪風饕,只聽“叮”一聲尖銳的脆響,玄鐵鞭竟斷了兩截。
“好,好,”顧清瀟聲音里滿是贊賞,“這一劍真是風濤地,萬里霜寒。”
他的聲音聽起來閑適又怡然,仿佛只是在指導一雙兒子對斫切磋。
蘇毓本來想問一句“為何”,真的來到了這里,反倒不想問了。
顧蒼舒的長鞭被削了短鞭,他的氣海又空了,若要再打,便得落到臺上,與蘇毓在方寸之間短兵相接。
近纏斗,他定然不是蘇毓的對手。
正遲疑間,互聽顧清瀟道:“舒兒,不可冒進。你憑借魔氣尚且不是你兄長的對手,何況氣海已空。”
顧蒼舒咬牙道:“爹爹且看。”
便即飛撲過來,扣鞭樽上的機簧,鞭三尺來長的鞭。
因了顧清瀟之言,他越發要顯出自己的本事,將短鞭舞得虎虎生風,勇悍如,剛猛如刀,每一次出手都是殺招。
蘇毓游刃有余地化解,冷笑道:“顧清瀟,你也曾是一劍震爍十洲的大能,如今像蛇鼠一般藏頭尾,只會躲在暗調遣你的傀儡人,像你這樣的可憐蟲,便是飛升又如何?”
Advertisement
顧清瀟淡然一笑:“你想激怒我。”
顧蒼舒卻是一愣,形不由一頓:“什麼傀儡人?爹爹,他的話是什麼意思?”
雖然只是一瞬間的愣神,蘇毓卻乘隙出劍,一劍刺穿了他的右肩。
顧蒼舒發出一聲慘。
顧清瀟的聲音里流出些許慈和憐憫:“舒兒,你在你阿娘腹中時便已死了,爹爹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他頓了頓道:“爹爹并非有意瞞你,你只是心上比別人多嵌了一塊石頭罷了,除此之外并無不同。爹爹這些年可曾迫你做過什麼事?”
“不可能!”顧蒼舒大聲道,“我不是傀儡人!”
“無妨的,舒兒,”顧清瀟溫聲安,“待爹爹得到歸墟之力,便能凌駕于天道之上,到時候你和你阿娘都能活過來……”
蘇毓冷笑道:“活過來?你要的只是言聽計從的傀儡罷了。”
顧蒼舒右肩被劍刺穿,將短鞭換到左手,向著蘇毓急攻過來,與蘇毓相似的面容扭曲猙獰:“我要把你殺了!”
他不管不顧地縱撲來,出好大一個空門。
蘇毓自不會錯過良機,一劍刺了他心口。
沒有金石相擊的聲音,只有利刃穿過的裂帛聲。
蘇毓失神道:“他不是……”
四周有點點熒亮起,千萬顆夜明珠齊放明。
巖壁皆是水晶,在明珠的照耀下璀璨奪目,猶如幻境。
顧蒼舒瘋了一樣大笑,一線鮮順著他的角淌下來:“我不是傀儡人,我就知道!蘇毓,阿兄,你殺了你的親弟弟,哈哈哈哈……蘇毓……我恨……”
他雙手握住劍,用力拔出,鮮噴涌而出,蘇毓眼前一片紅。
他握著滴的劍,木然地站在一旁,看著顧蒼舒的眼皮無力地垂下來。
顧清瀟從上方的水晶臺階上翩然飛下,輕輕落在水晶臺上。
仍是那張俊秀瘦削,略帶病容的臉,眉宇間的局促卻一掃而空,與當初那個唯唯諾諾的傀儡宗主判若兩人。
他整了整天青的袍袖,瞥了一眼死去的子:“他不是傀儡人。我將你阿娘放進水晶棺里時,腹中的孩子還活著。”
“為什麼?”蘇毓雙目中盡是,提劍向他直刺。
顧清瀟輕輕一讓,以兩指夾住劍尖:“你我父子一場,不必刀劍相向。你心神不寧,劍招也了。”
他低頭看了一眼水晶臺,顧蒼舒的正在慢慢流遍布祭臺的刻紋中,的圖案正慢慢顯現。
“祭一開始便無法逆轉,如今做什麼都是于事無補。”
他微笑著一拂袖,兩人中間出現一方棋枰:“我們父子難得相聚,眼下還有時間,不如與爹爹對弈一局。有什麼不明白的,爹爹告訴你。”
蘇毓神木然,慢慢坐下。
“這就對了。”顧清瀟哄孩子似地道,“還是像從前那樣,爹爹讓你五子。”
一邊說,一邊將五顆白子落到棋盤上。
“為什麼?”蘇毓抬起眼,凝視著他,“為什麼要殺阿娘?”
顧清瀟答非所問:“你阿娘是個意外。我算到了會為我生下天命之子,卻不曾算到這樣惹人喜,我甚至好幾次想過,就這麼與廝守一生,過完凡人的一世,倒也未嘗不可。”
他頓了頓,接著道:“不過太聰明,竟然發現我另有所圖。你阿娘真是我見過最聰慧的子,可惜只是個沒有仙骨的凡人,不然定有所。應該先下手為強,讓你外祖派部曲殺了我,但是心了,失了先機。說起來你的聰慧和弱,都是隨了。”
蘇毓一言不發,死死地盯住棋枰。
顧清瀟接著道:“阿毓,你生堅忍,卻像你阿娘一樣太過重,這終究會害了你。”
“你苦心孤詣地設這個局,便是為了歸墟之力?”蘇毓道。
顧清瀟道:“師父傳我歸藏易之事,云中子已經告訴你了吧?”
他一邊說,一邊拈起一顆黑子,“啪”一聲落在棋枰上。
“歸藏易運用得當,可以察知上下千年,窺破天機,只不過歷代傳人都是師父那般謹小慎微、固步自封的人,被所謂的‘天道’、‘天罰’縛住手腳,瞻前顧后,畏首畏尾,懷和氏之璧,卻視作頑石,豈非暴殄天?”
蘇毓從棋笥中出一顆白子,輕輕落下:“如此說來,你無所不知,無所不見?”
顧清瀟目一,執棋的手微微一頓。
“你知道我們在某個人創造的小世界中,”蘇毓淡淡道,“所謂的歸墟之力,便是這個小世界的力量源頭。”
他往旁邊看了一眼:“我想這萬丈深淵之下,大約連著那人的氣海。你想奪取歸墟之力,便是要奪那人的靈力、修為和仙緣,甚至取而代之,這便是所謂的超回,凌駕于天道之上。”
他頓了頓:“所謂的祭祀,便是擾他的心神,令他氣海紊,經脈逆流,沖破歸墟的屏障,你便可以趁機奪取他的一切,我猜的對麼?
“至于為什麼要用親,我猜是因為那人的經歷與我如出一轍,親眼見過父親殘殺母親,親相殘最能喚起他深埋心底的噩夢,擾他的心神。”
顧清瀟眼中有一瞬間的愕然,隨即復歸鎮靜:“你比我料想的還要聰慧。”
他無奈地笑道:“只不過木已舟,你親手殺死了一母同胞的弟弟,祭一旦開始便無法轉圜,這一局,你還是輸了。”
蘇毓角一挑,手一揚。
只聽得“嘩啦”一聲,棋枰被掀翻了,玉琢的棋子滾落一地。
顧清瀟一愕,脖頸上一涼,劍尖已抵住了他的咽。
“這早已不是你的棋局了,”蘇毓道,“你好生看看,顧蒼舒死了沒有。”
他左手兩指間著一枚白子,向顧蒼舒的死上輕輕一彈,那“尸”一陣搐,接著發出一聲。
猜你喜歡
-
完結16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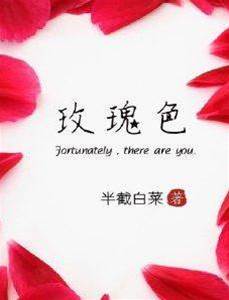
玫瑰色
總有一個人來愛你。 依舊熟女文,甜文。 第一次寫甜文。 儘量不膩歪。
22.4萬字8 9834 -
完結179 章

世子寵妻錄
林紈前世的夫君顧粲,是她少時愛慕之人,顧粲雖待她極好,卻不愛她。 上一世,顧家生變,顧粲從矜貴世子淪爲階下囚。林紈耗其所能,保下顧粲之命,自己卻落得個香消玉殞的下場。 雪地被鮮血暈染一片,顧粲抱着沒了氣息的她雙目泛紅:“我並非無心,若有來生,我定要重娶你爲妻。” 重生後,林紈身爲平遠軍侯最寵愛的嫡長孫女,又是及榮華於一身的當朝翁主,爲自己定下了兩個目標—— 一是:再不要把一手好牌打爛。 二是:不要與前世之夫顧粲有任何牽扯。 卻沒成想,在帝都一衆貴女心中,容止若神祇的鎮北世子顧粲,竟又成了她的枕邊人,要用一生護她安穩無虞。 * 前世不屑沾染權術,不願涉入朝堂紛爭的顧粲,卻成了帝都人人怖畏的玉面閻羅。 年紀尚輕便成了當朝最有權勢的重臣,又是曾權傾朝野的鎮北王的唯一嫡子。 帝都諸人皆知的是,這位狠辣鐵面的鎮北世子,其實是個愛妻如命的情種。 小劇場: 大婚之夜,嬿婉及良時,那個陰鬱淡漠到有些面癱的男人將林紈擁入了懷中。 林紈覺出那人醉的不輕,正欲掙脫其懷時,顧粲卻突然輕聲低喃:“紈紈,爲夫該怎樣愛你?”
28.6萬字8 162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