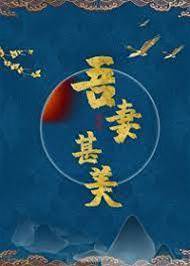《穿到大佬黑化前》 第82章
傅云深一直都是一個人,面對竇初開,是那麼手足無措,他只是想把最好的告白給,讓明白自己的心意,可是全都搞砸了。
他如此愚蠢,又如此稚。
時暮看了眼前方,有,像是一家店,把人從地上拉起,“來,換我帶你。”
傅云深坐上后座,他有些沉,時暮騎的很吃力。
時暮哼哧哼哧蹬著車子,說:“其實開心的,我很喜歡這次約會。”
傅云深抬了下眼皮,沒有迎合。
“你上有錢嗎?我們去住店。”
路邊開了一家不大的小旅店,牌匾有些破損,門前掛著的led燈非常廉價,于夜中閃爍著曖昧的紫。
一看就不是什麼正經店。
把自行車打到路邊,時暮推門而。
這家店很小,裝修老舊,地面臟,前臺上還散落著幾張不可描述的小名片,見人進來,材臃腫的老板抬了下頭,又繼續打著電腦游戲:“開房?幾間?”
時暮說:“兩間。”
老板說:“兩間四百八,份證帶了嗎?”
……份證。
時暮看向了側傅云深。
他把那噠噠的錢包從口袋掏出來,來回數了數,只有三張紅鈔票和一些零錢,好看的眉頭微微皺了皺:“我們要一間。”
老板叼著煙,攤開手:“份證。”
時暮小心翼翼道:“傅云深,我出來的時候沒帶份證……”
Advertisement
他睫,把錢和份證全遞了過去,“只用我一個人的份證可以嗎?多余的錢算是小費了。”
這種開在荒野中的旅店本來就是為了給野鴛鴦快活的,是不是正規營業的都不知道,自然也不在乎一張份證。老板點頭,給兩人辦了開房手續,傅云深又買了兩條一次后,和時暮一同上樓。
房間在二樓最里面,幽暗的走廊上空無一人,兩邊房門都關著,約聽到各種嘈雜的聲音。
到了里間,他開門。
很小的空間,正中是大床,正對著電視柜,左手邊是小小的浴室,算不上很干凈,甚至有種難聞的味。事到如今,時暮也嫌棄不了,就算環境不好,也總比宿雨夜的好。
問題來了,出來時沒帶換洗服,這套了,要怎麼辦?
傅云深把淋的襯衫下,拿起巾拭著漉漉的發,看向時暮說:“你先去洗澡吧。”
“你、你先洗吧。”
“嗯?”
時暮視線漂浮,“我不急,你先去洗。”
看一眼后,傅云深進了浴室,聽著從里面傳來的流水聲,時暮匆匆開了柜,里面掛著兩套浴袍,也不知道是清洗過還是沒清洗的,不太敢穿,擔心惹上疾病,又怕不快點換上會引起傅云深懷疑。
時暮咬咬,最終先下了上噠噠的子和上。
的已經開始長了,就算穿著運裹,在這種況還是能看到凸起,當然,不注意觀察的話別人只會當做。值得慶幸的時,上的小背心不算的厲害,用吹風機吹一下還能穿。
Advertisement
傅云深差不多快洗好了,沉思片刻,時暮關了房里的燈,把桌上的小臺燈調到最昏暗的源。
浴室水聲停了,他穿著一次衩出來,那的料子也是最便宜的,一些不該看的被看的一清二楚。
“你去洗澡吧,一會兒我用座機給司機打個電話,讓他明天過來接我們。”
時暮點點頭,起去了浴室,簡單沖了個熱水澡后,重新把吹干的背心穿好,看了眼外面昏暗的燈,滿懷忐忑的走了出去。
傅云深已經躺下,背對著。
時暮一個箭步沖到床上,快速關了燈,房間黑漆漆的。
閉著眼,聽到隔壁有人住,先是一陣短暫的歡笑談,接著,男之間的聲音開始曖昧,最后愈發不可自拔。
時暮捂住耳朵,莫名尷尬。
“時暮。”旁,傅云深再名字。
時暮低低應和。
黑夜里,他幽瞳清明,低低的聲線中帶著不易覺察的疲倦:“很小的時候,我們還沒和傅云瑞分開,那個時候我總是不明白,傅茜為什麼每次回來都擁抱弟弟,每次都給他最好的,而我想要的一個笑容都那麼困難。一次我了傷,濺到了傅云瑞上,那是傅茜第一次正視我,誤會我傷到了傅云瑞,掐著我的脖子,要讓我死。”
時暮心驚,不由轉過了。
他正看著。
傅云深邊帶著笑:“我的第一次瀕死是傅茜帶給我的。哪怕父親帶著我離了家,我也不懂為何如此待我。后來父親死的那天,我知道了真相。”
Advertisement
他說:“傅茜懼怕我,他還告訴我,其實他也怕我,他本來想把我丟到河里淹死,可跟在我后的背后靈不允許他那麼做,于是一直養著我,于是任由劉蓮待我,臨死前愧疚,或者是怕我命百鬼欺負他,所以把產都留給了我。你說可笑嗎?一個母親害怕自己的孩子,原以為最你的父親其實也想害死你。”
“還有那個背后靈。”傅云深角牽,“它消失了,被我活活燒死的,因為我想抱抱它。”
年的孩不明白自己有著怎樣的能力,簡單的擁抱后,他親眼看著對方魂飛魄散,那一瞬間,他在徹底明白自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存在。
當習慣了他人的冷落和畏懼后,時暮的溫暖接近倒讓他難以習慣。
“時暮。”傅云深接近,突然手上了的臉,溫熱的指尖讓一陣心悸。
時暮正要躲避,傅云深突然扣住了的腰,目專注:“沒遇到你之前,我已經做好了孤獨終老的準備,遇到你之后,我覺得是天注定。”
時暮心里咯噔了一下:“……啥?”
傅云深說:“我以前總想著克服對的恐懼,如今想想,我可能搞錯了方向,也許我是個gay呢?就算不是,我也愿意為你變gay。”
“………???”時暮更懵了,你他媽說啥呢?怎麼一句都聽不懂?
Advertisement
夜深人靜,細雨朦朧。
傅云深突然翻而上,眸深邃,聲線低沉:“我想說,和我在一起吧。”
“……”
未來的大boss沖邪魅一笑,“但有些事要先說好,我要在上面,你要是讓我開心,偶爾也能讓你做1。”
嗯,沒病,他真大方真善良。
時暮蒼白,瞳孔,險些被傅云深的笑晃瞎了眼。
小老弟你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前面鋪墊那麼多悲慘世,揚先抑那麼久就是為了說這個?
時暮玄幻了。
想扮男裝,苦練腹,德智全面發展,為的就是和大佬做出生死的兄弟,結果……這兔崽子想上?
猜你喜歡
-
完結41 章

親愛的,這不是愛情
她一直都知道,她跟他之間的婚姻,只是交易。他需要妻子,她需要錢,所以他們結婚。她也知道,在他的心里,恨她入骨。婚后三年,她受盡冷暖折辱,尊嚴盡失,也因為愛他而百般隱忍。終于,她看開一切,一紙離婚書,罷手而去。可糾纏不休的那個人,卻還是他……
5.2萬字8 20669 -
完結58 章

皇后的白月光另有其人
——正文完結——未出閣前,雁回的閨房里掛著一副男人的畫像,畫像中的人俊朗非常,是當今太子謝昀后來雁回嫁了謝昀,成了皇后,又將畫像繼續掛在了中宮可后宮佳麗三千,謝昀獨寵貴妃,一分眼神都未給雁回但雁回不在乎,甚至愛屋及烏到哪怕貴妃出言頂撞以下犯上,便是騎到她頭上,她也不計較貴妃生辰,謝昀舉國慶賀,大赦天下雁回生辰,謝昀過了三月才憶起,事后謝昀想給賞賜,雁回只答——日日能見圣上便是賞賜直至一日,貴妃拿走了雁回宮里的畫像雁回一路殺到翊坤宮,謝昀聞訊而來,見雁回拿刀架在貴妃脖頸上貴妃嬌滴滴:圣上救我雁回...
17.5萬字8 20143 -
完結1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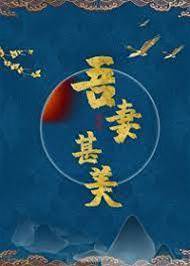
吾妻甚美
昭虞是揚州風月樓養的瘦馬,才色雙絕。 誰知賣身當天風月樓被抄了個乾淨,她無處可去,被抄家的江大人收留。 江大人一夜唐突後:我納你進門。 昭虞搖頭,納則爲妾,正頭夫人一個不高興就能把她賣了,她剛出泥沼,小命兒得握在自己手裏。 昭虞:外室行嗎? 江大人:不行,外室爲偷,我丟不起這個人,許你正室。 昭虞不信這話,況且她隨江硯白回京是有事要做,沒必要與他一輩子綁在一起。 昭虞:只做外室,不行大人就走吧,我再找下家。 江大人:…… 後來,全京城都知道江家四郎養了個外室,那外室竟還出身花樓。 衆人譁然,不信矜貴清雅的江四郎會做出這等事,定是那外室使了手段! 忍不住去找江四郎的母親——當朝長公主求證。 長公主嗤笑:兒子哄媳婦的手段罷了,他們天造地設的一對,輪得到你們在這亂吠?
28.4萬字8 21281 -
完結180 章

情陷港城
明豔財經女主播X港城豪門資本大佬港城八卦報刊登出一張照片,紅裙女人身影狼狽追逐前方邁巴赫,車中坐著低調豪門繼承人周硯京。全港皆笑話財經主播許時漾癡人說夢,竟想攀龍附鳳,卻不知當晚,她就踏進俯瞰港島的太平山頂別墅。*許時漾最初並非想上位,隻是在事業低穀為自己爭一個機會,期望得到周家繼承人的專訪資格。她踩著高跟鞋在雨中狂奔十幾米,有剎車聲響,保鏢打著黑傘,矜貴斯文的男人緩步到她麵前:“聽講你揾我?”來意還未說出,他居高臨下,打量物品般審視過她的明昳臉龐與曼妙身姿。片刻後,淺勾薄唇,粵語腔調慵懶:“今晚八點,白加道45號。”*許時漾做了周硯京的秘密情人,他的涼薄淡漠令她時刻保持清醒,矜矜業業,安分守己。等事業重回巔峰,立刻申請調回內地工作。她離開當日,周氏集團召開重要董事會議,卻有員工見到向來沉穩的繼承人飛奔而出,慌張神色再無半分冷靜克製。後來,維港下起大雪,耗費數億人造雪驚爆全城,知情者透露,這是下任周家主的追愛手段。*周硯京求婚三次終將許時漾娶回家,兒女雙全後談及往事,最無奈便是,當年他以為他在與心儀女人拍拖,她卻每天都在想著怎麼逃離他。
31萬字8 71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