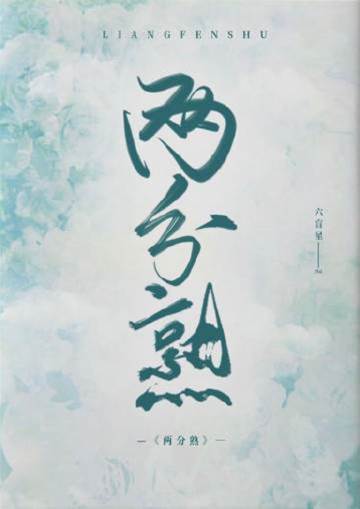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穿到大佬黑化前》 第84章
村落的白天來得早,六點剛過,外面便傳來嘈雜的農活聲。
周植打了一晚上呼嚕,又認床,到現在也不過才睡了三個多小時,時暮翻,把薄薄的毯子往上拉了拉,迷迷糊糊中,聽到年們低聲的談。
“你先睡一會兒還是吃點東西。”
“時暮呢?”
“里面呢。”
“嗯。”
腳步聲近,時暮半瞇著眼。
突然,頭頂毯子被人一把扯開,對方那冰冷的手死死掐上了纖細的脖頸,猛然的攻擊讓時暮刷的下睜開了眸子。
年的臉近在咫尺,那雙眼深不可測,好看的抿直線,時暮在他眸低看到了迸發出的火花。
他很生氣。
時暮很慌。
“在這兒舒服嗎?”傅云深到底是沒舍得下手,見表中的驚恐后,手上力氣立馬松了。
說話時,旁邊周植把一雙臭腳遞了過來,傅云深厭煩踹開,直接把肩上書包狠砸了過去。
時暮著急起后了退幾公分,蜷著滿是戒備。
他鞋上床,在時暮旁一躺,微闔了眼。
時暮吞咽口唾沫,這張床很小,兩個人又都不矮,他過來立馬變得擁,著年上的寒氣和周的疲憊后,時暮戰戰兢兢把毯子蓋過去,快速跳下床逃離了房間。
太兒嚇人了,本來以為躲夏航一這兒就能安枕無憂了,果然,還太年輕,太天真。
時暮出門對著東方紅日生了個懶腰,本來還困著,被傅云深一嚇頓時清醒,在心里嘆了口氣,時暮就著院里水池沖了一把臉。
“你不睡了?”剛劈完柴的夏航一搬了把小凳子在灶火旁,準備著生火燒水。
“不睡了。”時暮搖頭,“我能幫你做點啥?”
Advertisement
夏航一想也沒想的拒絕:“你好好歇著吧,不用你做什麼。”
“哦。”時暮四環視圈,這間四合小院有了年頭,風吹雨淋中,頭頂的屋檐瓦片早已破損,但能看出有人時不時上去修理,收回視線,低聲,“你怎麼不告訴我傅云深要過來?”
就著了火,夏航一蓋上了鍋蓋,表無辜:“他不讓我說。”
“……。”傅云深真是太狗了!
夏航一余瞥過:“你們吵架了?”
時暮心煩氣躁,了一頭發,“沒吵架,就是……”
總不能說傅云深和告白吧?
時暮咬咬,生生把一肚子的話憋了回去:“沒什麼。”
兩人正談著,夏航一的太拄著拐杖從里面出來,老人家雙巍巍的,像是馬上要跌倒,時暮急忙上去攙扶著下來。
太瞇瞇眼,細細打量著時暮,說:“哪里來的小姑娘,真俊。”
夏航一洗干凈手過來,扶著老人家在藤椅上坐下,在耳邊高聲道:“這是我和您說的時暮,不是姑娘,是小子,孫兒可沒騙你,時暮長得特別好看。”
時暮眼睛往老太太上瞥了眼,不神收回了手。
夏已有85歲高齡,耳朵有點病,可眼睛明清著呢,不住搖著頭:“姑娘姑娘,就是姑娘,老太婆的眼還沒瞎呢。”
時暮心里一,說:“太,我是男生。”
“哎呦,真俊。”像是沒聽到時暮的話一樣,老太太蒼老的手上了的臉。
時暮看得出來老人家對喜歡,也沒躲避。
夠了,老太太收回手,笑著和夏航一說:“比秀兒年輕時好看。”
秀兒是夏航一母親的名,在那麼多孫媳婦中,老太太就喜歡夏航一的娘,因為他媽最好看,十里八鄉一枝花,老太太一直覺得嫁給孫子是虧待了。
Advertisement
“有對象了沒?”
夏航一把泡好的熱茶遞到太手上,神無奈:“太,時暮還是學生,你這樣問會讓人家困擾的,你今天不是約了李吃早茶嗎?我現在送你過去好不好?”
老太太看著時暮,“我柜里有裳,本來是給秀兒做的,可有些了,回頭拿給你吧。”
夏航一攙扶著老太太向外走:“您啊真是老糊涂了,時暮是男生,穿不了孩子服,現在我送你去李那兒,一會兒接你回來啊。”
送走老人家后,夏航一不好意思看著時暮,“太有些糊涂了,你不要介意啊。”
時暮似乎有睪癥,用他們話說就是疾,本來夠自卑的了,如今這樣說,心里肯定不好。
想著,夏航一的目往雙間瞥了眼。
時暮順著視線下,定定神,道:“沒事,我不介意。”
話音剛落,時暮看到夏航一的目落在了后,覺得后背發涼,扭頭一看,對上了傅云深惻惻的眼神。
子僵住,時暮大氣都不敢出了。
“你來,我和你談一下。”他開口,神平靜。
時暮連連搖頭,匆忙跳開傅云深邊,“我、我覺得我們沒什麼好說的。”
傅云深不給拒絕的機會,強拉著時暮就是往外走。
年手勁兒頗大,任憑時暮怎麼掙都掙不開,村里過往的老人好奇往過張,坐在門口的老太太們便嗑瓜子邊沖他們投來曖昧的視線。
時暮臉上臊紅,“傅云深你松開,這麼多人看著呢。”
傅云深不依,扯著繼續往里面的樹林走,“那我們去個沒人的地方。”
掙扎的累了,息著跟年步伐,“你、你先松開,我走不了。”
Advertisement
傅云深狐疑的看一眼后,慢慢松手,借此機會,時暮撒就是往回跑,傅云深早就猜出了的套路,直接擋到時暮面前,冷笑聲:“你往哪兒跑?”
時暮子一驚,轉繼續跑。
傅云深臉上一黑,道:“你站住,我有話和你說。”
時暮不敢回頭,邊跑邊喊:“不聽不聽,王八念經!”
“……你回來。”
時暮捂住耳朵:“不看不看!公下蛋!!”
“……”
“你再不停下就撞樹了。”
砰。
在他說完這句話,時暮的腦袋狠狠磕在了樹干子上,猛烈的撞擊讓時暮搖搖晃晃后退幾步,一陣頭暈目眩后,綿綿跌倒在了傅云深上。
年一雙大手扣著雙肩,眼神充滿嘲諷:“一般來說,水分占據了人總重量的三分之二。”
時暮呼吸急
促,眼前發黑,靠在傅云深前,哆嗦:“所、所以呢?”
傅云深冷著臉:“你的三分之二都在腦子里。”
“……你他媽腦子才進水了。”
緩過神了,時暮一把推開傅云深,捂著撞青的腦門齜牙咧。
靠著樹干緩緩蹲下,等眩暈消失后抬起了頭,樹影斑駁落在他上,映襯著那雙眉眼愈發好看。
時暮了干的,“我直說吧,我把你當兄弟,你不能把我當老婆,你快收起你那齷齪的想法,告訴我之前的話都是玩笑,那樣我就和你回去,也不躲著你。”
他垂眸,目灼灼:“我要是不呢。”
要是不……
也不能怎麼辦啊!!!
傅云深抿在面前蹲下,一字一句,字字清晰:“時暮,我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深思慮才決定告訴你我的心意,我不希你把那些話當做玩笑,我喜歡你,想和你過一輩子。”
Advertisement
時暮狠狠抓了把頭發,又是好笑又是無奈:“哥哥,你今年才17歲,你知道一輩子有多長就和我說一輩子,我知道你之前過的不容易,沒人愿意接近你,沒人愿意和你玩兒,只因為我是第一個和你朋友的人,所以你誤會了對我的,但是沒關系,相信你很快能分清這些,畢竟你那麼聰明……”
時暮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看到年的眼圈發紅,神約有些不妙。
靠樹干,想到剛才的那些話有些傷人,張張,語氣發虛;“傅云深,我沒別的意思……”
“我不知道一輩子有多長。”他看著,目堅定,“但是我認定一輩子,就是一輩子。”
傅云深說:“時暮,從小到大我都沒有騙過人,我不會騙你的,你信我好不好?”
看著那像是小老虎一樣無助的眼神,時暮再不忍說出任何拒絕的話。
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殘忍,從一開始,只把傅云深當任務目標,所做的一切都是別有預謀,而傅云深呢?生活在黑夜里的傅云深把當做了一束,抓住后再不愿松開。
不能繼續騙他了,不管結果如何,哪怕回不了家,都不能欺騙這個善良的年。
時暮攥拳頭,低聲開口:“傅云深,其實我……”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攝政王的絕色醫妃
這是一個醫術高超的腹黑女與一個邪惡高冷的傲嬌男合夥禍害天下並在撲倒與反撲倒之間奮鬥的終身史!】
33.6萬字8.18 19197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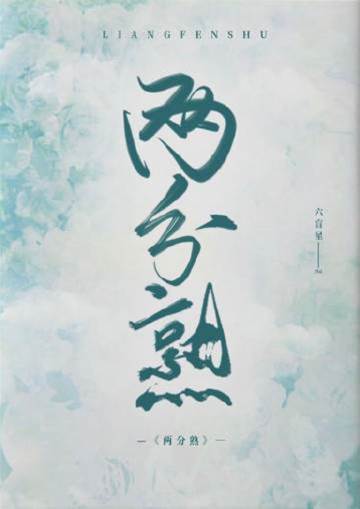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5932 -
完結179 章

你依然在我夢里
餘笙休假旅行,在古城上演了一場浪漫邂逅。 對象是她暗戀多年的男孩。 一切開始得突然,結束也突然。 男人消失在一個深夜,再沒出現過。 直到她生日那天,同事攢局,說請了朋友助興。 那人姍姍來遲。 餘笙緩慢擡眸,猝不及防跌進一雙眼,像墜入那晚古城靜謐而璀璨的星河。 晃神間有人問:“認識?” 餘笙回過神,淡定搖頭。 同事得意洋洋地介紹:“我哥們兒裴晏行,開飛機的,可牛x了。” 餘笙笑着說幸會。 那人微掀眼皮,看過來。 “幸會?” 短暫的安靜過後,他脣角勾起一抹興味:“哦,看錯了,餘記者長得像一位熟人。” * 後來,餘笙被領導發配到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拍紀錄片。 那裏有湛藍的天空,潑墨一樣的航跡雲,一架架戰鷹矗立在天地之間,昂首挺胸,氣勢磅礴。 有同事發現她和某位空軍飛行員來往甚密,調侃起來。 餘笙冷靜地表示不熟,同事一個都不信。 直到院門口傳來一道含笑嗓音: “是不熟。” 男人身影頎長而挺拔,眉眼張揚桀驁,意味深長地看着她說:“沒熟透呢。”
30.4萬字8.18 5982 -
完結208 章

藏玉懷姝
攖寧出嫁了。 皇帝指的婚,嫁的人是當今九皇子,晉王宋諫之。離經叛道暴虐恣睢,名字能止小兒夜啼。 聖命難爲,攖寧只得夾起尾巴做人。好在她心寬,除了吃食和活命沒什麼所求,沒什麼可被人拿捏的。 “真當本王不敢殺你?” “萬香閣的杏仁佛手,你不吃本王便扔了。” 攖寧:“……” 屈居人下,她沒什麼骨氣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 宋諫之娶了個小王妃,人雖然蠢了點,但對他還算真心。天天夫君長夫君短的圍着打轉,爲了救他自己還差點摔成傻子,想想養她一輩子也無妨。 爲奪皇位,他與人做了絕地逢生的戲。 騙過了父皇,騙過了兄長,那個耳朵眼都冒傻氣的小王妃自然也不例外。 他知她貪吃膽慫,做好了事後再去岳丈家接人的安排。 沒成想他逢難第二日,本該在太傅府待着的攖寧出現在大獄。她穿着獄卒衣裳,臉上抹着灰,給他揣了兩包核桃酥。 宋諫之冷着臉嚇她:“被人發現你就走不了了,得跟本王一塊上斷頭臺。” 她沒回應,低頭拆着油紙包小聲解釋:“熱食味道太大,我帶不進來。”拆到最後淚珠子啪嗒啪嗒往下掉。 宋諫之嘆口氣,將人攬到懷裏,剛要心軟安慰,便聽見她哽咽着說:“宋諫之,你一定要好好的。” 攖寧抽了抽鼻子,鄭重道:“你若出事了,我成寡婦再嫁人可就難了。” 男人給她擦淚的動作停了,聲音冷似數九寒天:“攖寧相中了哪家公子?” 攖寧拍拍他的肩,不要命的跟了一句:“等你活着出獄,就能親眼看到了。”
32.1萬字8.18 150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