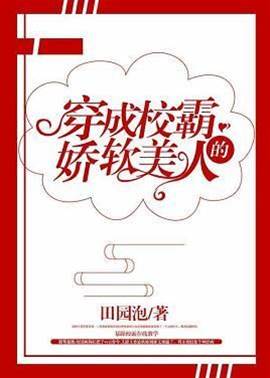《豪門女配不想擁有愛情》 第46章
聽聽,這是人說的話?
——“害你?別給自己臉上金了,你那條命不值得我進牢子。”
“老公,你別誤會……”
易揚盯著手上的剪刀,沉聲道:“離我遠點。”
“……”許辛夷往后兩步走。
易揚起亮燈,朝許辛夷手,“給我。”
敵強我弱,這種形之下許辛夷審時度勢很有骨氣,沒和他較勁,將藏在后的剪刀遞給他。
易揚看著那把剪刀上還沾著幾碎發的剪刀,大半夜的給他剪頭發?把他當傻子糊弄?
“說清楚,大半夜的剪我頭發干什麼?”半睡半醒間,模糊瞧見床前站著個拿著剪刀沖他一臉獰笑的人,魂都差點給嚇飛。
許辛夷嘟囔道:“不干什麼。”
——“就幾頭發而已,有必要生這麼大的氣嗎?”
“再說一遍?”
“就幾頭發……不是,”許辛夷一快,差點餡了,“不干什麼。”
易揚沉默看了良久,沒聽到許辛夷剪他頭發干什麼,只得沉著臉扔下一句,“把剪刀拿回去,睡覺!”
許辛夷‘哦’了一聲,拿著易揚扔桌上的剪刀放回帽間,并將自己手心里的一小撮頭發用干凈紙巾包起來,一臉喜放進首飾盒中。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易揚眉心蹙,這人又作什麼妖?
想為易揚和許微茵的孩子做親子鑒定的事并非心來,許辛夷計劃多時,并且在許微茵回國,傳出背后有金主的傳言后,就有無數狗仔暗地里跟著,企圖某天能將金主的正面照拍下,掙一大筆錢。
是以,許辛夷第三天就毫不費勁地從一個狗仔那買到了許微茵兒子的頭發。
“確定是他的嗎?”
許辛夷大風墨鏡口罩,站在地下車庫一廢棄的雜間門后。
Advertisement
對方狗仔同樣大棉口罩墨鏡全副武裝,像臥底接頭似得,站在門口,將一小包封口塑料袋從袖子里拿出來,神兮兮地從門隙里遞給許辛夷。
“我跟著許微茵的兒子和照顧的保姆進的理發店,還能有假?”
許辛夷看了眼頭發。
“我知道你想干什麼,放心,帶囊的。”
“囊?”
那狗仔說:“那孩子一進理發店就跟發狂了似得,一個勁地扯自己的頭發,我趁機從那孩子手上撿的,你拿這個去做親子鑒定,肯定能行。”
“你怎麼知道我要做親子鑒定?”
“現在誰不想知道許微茵孩子的父親是誰?”那狗仔低了聲音,說:“你如果知道孩子父親是誰,有沒有興趣合作?我這邊有人,咱們可以聯合搞個大新聞,不會讓你吃虧的。”
許辛夷對大新聞沒什麼想法,當即敷衍道:“再說吧。”
“行,那我先走了。”
說完,狗仔探頭看了四周兩人,見四下無人,這才匆匆離開。
許辛夷從雜間出來,手上拿著兩封口明塑料袋,意味深長地笑了。
明明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許辛夷’怎麼就能搞砸的?
還是得由出馬才行。
馬上,就能把里最大的謎題給解開了!
兩小時后,許辛夷接到醫院打來的電話。
電話里與悉的醫生低了聲音說:“許小姐,頭發樣本不行,做不了親子鑒定。”
“不行?不能做?為什麼?”
“用頭發做親子鑒定,得需要帶囊的頭發,最好五六左右,您拿過來的一方樣本,是剪斷的。”
許辛夷瞬間明白。
所以,想給易揚和許微茵的兒子做親子鑒定,需要親自從易揚頭上拔五六下來?
Advertisement
許辛夷著窗外暮靄沉沉,對面易氏集團依然燈火通明。
從老虎頭上拔,這件事有點難度,不太好辦吶。
不過,有事者事竟,再難,易揚的頭發,也勢在必得!
打定了注意,許辛夷下樓地下車庫開車回家,電梯口恰好遇到正準備回家的江念。
“江念?回去?”
江念似是剛練習完,頭發還是的,“是。”
“坐我車,我送你。”
以往江念答應得干脆的,今天卻一口拒絕,“不用了,今天我有點事。”
許辛夷也懷疑太多,只點了點頭。
下班高峰期堵車嚴重,就從底下車庫到公司正門口,就花了十來分鐘的時間。
正思索著待會怎麼在老虎頭上拔,就瞧見江念戴著口罩和帽子低調往前一個路口走。
許辛夷一個剎車,正準備按喇叭時,卻瞧見江念面無表走向路邊一輛邁赫。
副駕駛上有人下車,畢恭畢敬給他開了車門。
江念似是有所顧忌,和車里的人說了兩句,隨后才上車。
隔得太遠,許辛夷既聽不到他說什麼,也看不到車里坐著誰,可是在印象里,江念不是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嗎?
不然怎麼被天娛封殺后,不得已去了影視城搬磚?
開得起邁赫,請得起司機和助理的人,不像是普通人。
一個娛樂圈的普通家庭的孩子,上了一輛邁赫,這怎麼看都容易引人遐想。
難不江念有什麼事瞞著?
雖然這些都是江念的私事,無權過問,但那小朋友年紀還小,沒經歷過世間險惡,邁赫上的是好人也就算了,萬一是什麼七八糟的人,被騙了怎麼辦?
本著是江念老板的想法,許辛夷認為自己還是得給他打個電話。
Advertisement
電話很快被接通。
“喂,江念,你現在在哪呢?”
電話里停頓片刻后,江念低了聲音,說:“辛夷姐,我……我剛上車準備回家,您找我有事嗎?”
“我想起件事,三天后你不是得上那個綜藝節目嗎?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得和你代一下,你現在能回公司一趟嗎?晚上我送你回去。”
江念沉默片刻,說:“辛夷姐,我現在有點急事,我明天早點去公司,行嗎?”
有急事。
既然江念不愿意,也不能勉強他。
許辛夷想了想,還是應了下來,“行,那明天見。”
掛斷電話。
也許是自己多心了,上了一輛邁赫而已,都是年人了,有什麼好擔心的。
明天旁敲側擊問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與此同時,掛斷電話的江念將頭冷漠向車窗外,他手中握著手機,手無意識地不停地按著開關機的鍵,屏幕亮起又黑,黑了又亮起。
寬敞舒適的后座彌漫著沉重的氣氛。
車視線太過昏暗,邊的男人看不清全貌,車窗外偶爾掠過一盞路燈,得以窺見那雙凜冽眉峰下眸凜然的眼睛。
男人低聲笑,“小朋友,別張,咱們只是回家和爸一塊吃頓便飯而已。”
江念手一滯。
“你不應該讓我去吃飯,他不會高興的。”
“怎麼會?他期待這一天很久了。”
江念轉過頭來,看著邊的男人,眼底沉沉濃濃的恨意與翳,“我不會讓他高興的。”
車輛轉過彎,緩緩駛別墅區。
————
另一邊許辛夷順利通過堵車的道路,剛到家就見著有一西裝革履的陌生男人從別墅走出。
見著許辛夷,停下側微微躬。
疑看著側送人的陳伯。
Advertisement
陳伯笑著介紹說:“這位先生是來給老先生寄請帖的。”
“請帖?”
男人解釋說:“我們是來給老先生送慈善晚宴的請帖。”
許辛夷恍然大悟。
原來是易揚昨晚提過的慈善晚宴。
進門。
易老先生正和易夫人坐在沙發上談話,面前放著一張請帖。
“爺爺,媽,我回來了。”
“回來了?剛好聊起你。”
“我?”
“對,”易夫人將面前那封請帖拿給看,“三天后A城的慈善晚宴,以往都是易揚和我參加,今年特地邀請了爸,不過最近兩天天氣太冷,爸一向不好,不想出門,所以就想讓我和易揚還有你去參加。”
“慈善晚宴?有到場嗎?”
“這個是肯定的,怎麼了?”
許辛夷面帶難拒絕,“那天我有點事,可能去不了。”
三天后江念參加第一檔綜藝節目,那小孩是工作室下的第一個藝人,當然得盡心盡力,之前就答應了作為嘉賓一同上節目,答應過的事反悔總是不太好。
最重要的是,和易揚出席那種場合,和易揚的關系還不是分分鐘給曝了?
“這樣……那待會易揚下來你和他商量商量。”
“行了,這事待會再說,了吧?老陳,麻煩你易揚下來,吃飯了。”
服都沒換的易揚從樓上下來,坐在餐桌邊上。
——“易揚最近這麼閑的嗎?回來這麼早?”
許辛夷坐下,著筷子深思慮該怎麼從易揚頭發拔才行。
“對了,剛才慈善基金會的人來送請帖,三天后的晚上,你準備一下。”
易揚看向許辛夷。
許辛夷埋頭吃飯,還往一邊躲了躲,渾上下寫著‘莫挨老子’四個字。
易揚冷笑,“我知道,我和辛夷一定去。”
許辛夷抬頭看著他,很是為難,“可是我那天有事,可能……”
“推了。”
“是很重要的……”
“推了!”
“……”
——“要死要死,這不是我公布我和他的關系嗎?”
——“完了完了,他這是讓我吊死在他這棵樹上!”
——“狗男人以前守口如瓶,把我當空氣,什麼宴會都不帶我參加,簡直當沒我這個人,現在一個勁的往我上湊,什麼意思?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好氣!”
許辛夷憤憤吃飯,眼神不住往他頭上瞟。
——“不行,我得想個辦法才行。”
易揚看了一眼。
“對了,”易老先生提醒他,“到時候江家肯定也會派人去,你自己注意點。”
易揚點頭,“我知道。”
“江家?”
“江氏電子科技,”易夫人解釋說:“以前有過合作關系,但后來關系淡了。”
許辛夷恍然大悟。
原來是男主一家。
江淮與易揚一樣,都是四年前和許微茵有過糾纏的人,其實許微茵有過糾纏的男人也不止他們兩,還和韓驍演過戲,其他幾個排的上號的富二代也和許微茵有點關系。
只不過就著重寫了這三人,其他的人背景板,彰顯許微茵的魅力而已。
而江淮之所以抱得人歸,是因為江淮沒有一個像一樣,和許微茵作對的妻子。
然而很不幸的是,易揚有。
“老公,”許辛夷殷勤將一塊的藕塊夾到他碗里,賢妻良母似得微笑道:“你最近工作辛苦了,多吃點。”
自昨晚被許辛夷剪了一小撮頭發后的易揚如今在面對時,神高度戒備,唯恐許辛夷這人在他面前又作妖。
“謝謝。”
“我們夫妻之間有什麼好謝的,”許辛夷無比心道:“老公,你最近工作別太累了,我在新聞上總看到那些加班熬夜猝死的新聞,你也小心點。”
易揚眉心蹙,自打能聽到許辛夷心里話以來,他這眉心都沒展平過。
聽許辛夷這語氣還期待的。
又在作什麼妖?
老先生問了一句,“最近公司事還多嗎?”
“不多,階段的工作暫時理完了。”
“那就好,”易夫人給他夾了塊排骨,“最近你天天深夜才回來,得好好補補。”
幾人吃飯,飯桌上只聽得見碗筷的聲音。
“哎呀!老公,你頭發怎麼回事?怎麼有白頭發了?”
一聲驚呼引起幾人注意。
許辛夷急頭白臉地放下筷子就要去他的頭。
易揚形往右一晃,反應極快離了半米遠,戒備看著,“干什麼?”
許辛夷手停在易揚眼前,一臉無辜,“我看你有白頭發了,所以想仔細看看。”
猜你喜歡
-
完結1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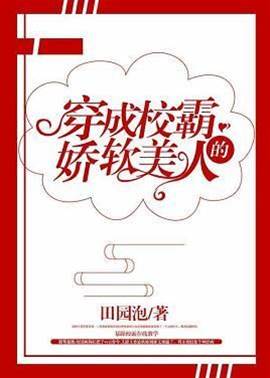
穿成大佬的嬌軟美人
作品簡介: 按照古代賢妻良母、三從四德傳統美德培養出來的小白花蘇綿綿穿越變成了一個女高中生,偶遇大佬同桌。 暴躁大佬在線教學 大佬:「你到底會什麼!」 蘇綿綿:「QAQ略,略通琴棋書畫……」 大佬:「你上的是理科班。」 —————— 剛剛穿越過來沒多久的蘇綿綿面對現代化的魔鬼教學陷入了沉思。 大佬同桌慷慨大方,「要抄不?」 從小就循規蹈矩的蘇綿綿臉紅紅的點頭,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出格表演。然後全校倒數第一抄了倒數第二的試卷。 後來,羞愧於自己成績的蘇綿綿拿著那個零蛋試卷找大佬假冒簽名。 大佬:「我有什麼好處?」 蘇綿綿拿出了自己覺得唯一擅長的東西,「我給你跳支舞吧。」 ———————— 以前,別人說起陸橫,那可真是人如其名,又狠又橫。現在,大家對其嗤之以鼻孔。 呸,不要臉的玩意。
34.1萬字8 9596 -
連載403 章

時光與你皆傾城
一場錯愛,她忍受四年牢獄之災。四年後,她浴火重生,美得淩厲,發誓要讓他百倍奉還。隨著時間推移,真相一層層析出,當初的背叛,是刻意,還是誤會?他帶給她的,到底是救贖,還是更甚的沉淪……
73.7萬字8 8594 -
完結375 章

怪他過分沉淪
傳聞,蔣蘊做了葉雋三年的金絲雀。傳聞,她十九歲就跟了葉雋,被他調教的又乖又嬌軟。傳聞,葉雋隻是拿她當替身,替的是與葉家門當戶對的白家小姐。傳聞,白小姐回來了,蔣蘊等不到色衰就愛馳了,被葉雋當街從車裏踹了出來。不過,傳聞總歸是傳聞,不能說與現實一模一樣,那是半點都不沾邊。後來,有八卦雜誌拍到葉家不可一世的大少爺,深夜酒吧買醉,哭著問路過的每一個人,“她為什麼不要我啊?”蔣蘊她是菟絲花還是曼陀羅,葉雋最清楚。誰讓他這輩子隻栽過一回,就栽在蔣蘊身上呢。【心機小尤物VS複仇路上的工具人】
70.7萬字8 28298 -
完結153 章

後腰紋身
盛傳頂級貴公子淩譽心有白月光,但從他第一眼見到慕凝開始,就被她絕美清冷的麵龐勾得心癢癢,世間女子千萬,唯有她哪都長在他的審美點上,男人的征服欲作祟,他誓將她純美下的冷漠撕碎。某日,淩譽右掌支著腦袋,睡袍半敞,慵慵懶懶側躺在床上,指尖細細臨摹著女人後腰上妖治的紋身,力度溫柔至極。他問:“凝兒,這是什麼花?”她說:“忘川彼岸花。”男人勾住她的細腰,把她禁錮在懷裏,臉埋進她的頸窩,輕聲低喃:“慕凝,凝兒……你是我的!”他的凝兒像極了一個潘多拉盒子……PS:“白月光”隻是一個小過渡,男主很愛女主。
26.7萬字8 21017 -
完結430 章

人前人後
縱使千瘡百孔,被人唾棄。
69.9萬字8.18 84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