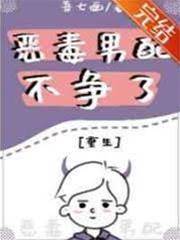《穿到明朝考科舉》 第45章
“《資治通鑒綱目》《大學衍義》《遷安縣志》《小學》《孔子家語》……還有這摞《四書對句》?”
謝瑛翻著謝山遠從遷安縣提來的兩摞書, 長眉微挑, 看著垂手站在堂前的長隨,好笑地問:“你在家里又要錢、又要車、又要人地籌備了這麼久, 帶的家丁比我出門帶的緹騎都多, 就買回來這麼幾本書?這書摞起來還沒你搬去的銀錢箱子大吧?”
桌旁站著的管事差點憋不住笑, 跟著去遷安的護院們也微不屑之,覺得謝山太小題大作。
謝山的臉紅了又白, 委屈地說:“小的不是為了辦好這樁差事麼!是老爺說的崔家小公子耿介清高, 不通俗務,小的就想著他家縱有個鋪子, 料來生意也好不到哪兒去。誰知道還沒找著他那個書鋪, 從路上就遇見好幾波兒去遷安買崔人兒箋的, 到了他那店里更是……”
他想起在店里排隊時,看見墻上掛的那張等婉寧秋思圖,兩腮不又漲紅了幾分,咽了咽口水說:“人家那人兒圖畫的, 比畫箋好看, 不, 比那真正的人兒還好看——大人你是不曾親眼看見,就云揚班那個唱旦角的小玉笙都不及那般絕!”
那張圖雖是畫的,卻有真人也難及得上的嫵風,這一提起來,就連隨行的護院們也頗懷念當時的悸,顧不上笑話他了。
謝瑛指尖在桌上輕叩, 清脆規律的敲擊聲把他們的魂兒又從人圖上拉回到眼前。
眾人連忙屏息低頭,抑住心中躁。謝山也夾了尾,老老實實地說:“不是小的們辦事不力,實是人家崔小公子買賣做得極好,店里的人多的轉不,本找不出什麼難賣的書。”
Advertisement
他瞄了地上那兩摞書幾眼:“除了《四書對句》是在外頭擺著,一看就無人問津,容易買回來的,剩下的還是小的著他家伙計爬梯子上書架,上上下下索了好幾次才尋出來的呢。”
謝瑛料知他不敢騙自己,聽到他那店鋪生意這麼紅火,便流出一點意外的神:“他這些日子不是正用功讀書麼,竟還有力把書坊經營這樣……倒是我低估他了。”
謝山一拍大,道:“崔小公子可不有本事麼!他們店外招牌上就寫了,十五齡神集圣賢書里的句子出了對書,這神連書都能出,管一個書店更不在話下了。”
謝家老管家卻不敢相信,嘀咕道:“敢莫是他家請了個好掌柜吧,一個十五歲的小兒哪里會懂經營?不是老朽看低他,咱們千戶十五時還跟著趙同知辦差呢,那小公子又不是天上神仙托生的,怎個就能頂門立戶,自己管買賣了。”
謝瑛搖搖頭,替他分辯了一句:“你莫小瞧他。我在他這個年紀,若落到賊人手里,進退無門,也沒有他那份鎮定。當初代廟考校神李東,出對‘螃蟹渾甲胄’,東對以‘蜘蛛滿腹經綸’,代廟便稱其有宰相之,我看這位崔小公子亦有此量。這是經營天下的人才,經營起一間鋪子也算不得什麼。”
他彎下,撿起一本《四書對句》,翻看幾頁,見里面聯綴的對句比年前給他的那本更多,眼中嘉許之更濃,嘆道:“可惜了,好好的神竟拖到這個歲數。崔郎中真是個糊涂人。”
管家勸道:“這畢竟是人家的家事,父親不管兒子前程,大人又能怎麼幫他。就是那小公子自己也要講孝道,不能違背了父親的話哩!”
Advertisement
謝瑛笑了笑說:“這怎麼只說是家事。天下英才皆是皇爺的臣民,神也是天降與我朝的祥瑞,豈能任由他埋沒了。”
這樣的書本該薦給那些有清流名的翰林學士等輩,可惜他們錦衛與清流天生的不對盤,他要是貿貿然去向人推薦,反倒傷了崔燮的聲。
說來說去,還是怪崔郎中給他拖到了這把年紀。
若在十歲之,直接舉薦給皇爺,送進國子監或順天府學讀書又有可難?可十五歲終究是大了些,江南才子中,這個年歲考上秀才的也不新鮮,一個生試也沒考過的白年,皇爺縱然知道了,也未必肯召他進宮奏對。
他想得有些投,雙眸微微瞇起,上彎的角也抿平了,半合的眼眸間便出一凜冽的芒。謝管事簡直以為他要殺人奪子,急的勸道:“崔公子的事自有他老子娘打算,大人合他非親非故的,又不是沒幫過他,怎地就這們上心了?”
是啊,非親非故的,只不過見了兩面,何必這麼心。
謝瑛看著地上那兩摞書,眼前閃過崔燮稚孱弱的模樣和與面容不符氣質,輕嘆一聲:“他沒了親娘,老子又靠不住,我不替他打算還有誰替他打算呢?當初父親在萬全都司故,咱們府上艱難的時候,還不是趙大人提攜我才有今日。得幫人時便幫一把吧。”
他拿著一本《四書對句》離開,剩下的人替他收到書房里,吩咐管事:“替我辭了兩天后的聚會,就說我得了一本神書,見人家十五歲的子都能通四書,也激起讀書的心氣兒來了。”
謝瑛要閉門讀書的消息很快便在錦衛兩司十四所傳開,同僚、下屬奇怪不說,幾位同知、僉事聽說這事,私下也不免八卦幾句。過不多久,連權知錦衛事的懷寧侯孫泰都傳兒子過來問了一句:“他一個見任職的衛所千戶,閉門的讀什麼書?難不還要考進士?”
Advertisement
孫應爵道:“我哪兒知道,只聽說他看了什麼神寫的四書,自己就想發讀書了。這年月神是過不了幾月就出一個,誰知道哪兒來的神書呢。再說四書五經有什麼好看的,外面現在都看崔人兒的……”
孫泰待信不信地說:“不就是那個四人合集嗎?后軍都督陳瑛家還有他的大圖呢,我看過了,也就……倒也是好看的吧,他可真看那個看迷了?那再好也是紙人兒,還不如正經說個大家閨秀親呢。”
“是隨書贈的四幅大圖嗎,兒子也集了幾套套的,父親若喜歡,兒子回頭便送父親一套把玩。”孫應爵笑道:“謝瑛倒是不大看那個,誰知道他看的什麼書。父親敢莫是想給他做了?是誰家兒,容貌如何,配得上他麼?”
孫泰從鼻子里哼了一聲:“你也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人家都替皇爺辦了多差,還知道念《四書》,還要求上進,你干過什麼!你至今出過京麼?看你這樣子,將來能什麼氣候!”
將來能什麼……當然是繼承懷寧侯府了。
孫應爵暗地撇了撇,面上老老實實地,垂頭肅手而立,說:“父親放心,我找個時機問他一句。你老要是給他相了哪家千金,也提前告訴我一聲,我跟他個底,好他高興高興。”
他自己也好奇謝瑛這種連《聯芳錄》都不上心的人能什麼樣的書迷住,便撿了日子去謝府問他。
卻不想他去的時候,謝瑛卻不在家。謝管事將他讓到花廳,親自端了茶上來,告訴他:“我們千戶看神書看的迷了,這兩天滿心都是那書,回武學拜訪教諭去了。”
孫應爵支著眼睛問:“他還真打算考進士哪?這們大年紀,好好個親,生幾個大胖小子蔭襲他的武職不好麼!他這麼上進,倒比得我不行了,那天我爹聽說他讀書,可是差點兒就上鞭子打我了!這是哪個神,直是個索命的冤孽!”
Advertisement
老管事也覺得冤孽,可是想起墻上那張寶像莊嚴的觀音像,又不敢往惡想,心里暗念了聲佛,無奈地說:“可不就是云南司崔郎中家那位旌表了義士的大公子,我們千戶與他也是緣份忒深,大事小都要關照著。”
孫應爵哪里在意一個小小的義士,想了一下沒想起來,便渾不在意地說:“你們謝大人真個要當文人了。罷了,你也別備茶了,我去看看他。”
他翻便去了城東武學,看門的軍士都認得他,連忙迎上前問:“世子今日也來了?敢莫是知道了張尚書下武學來,也想聽聽他會講?”
孫應爵笑罵:“我都什麼年紀了,又不是都指揮,還回來聽這訓誨?你們見著謝千戶不曾,我過來尋他的。”
兩個軍士笑道:“回世子,謝千戶早上就來了,此時還沒走,世子不妨進去尋他。”
孫應爵翻下馬,把韁繩扔給他們,隨意指了個人引路,整整冠,大步流星地進了武學大門。學里此時已經散了會講,下學的和武將子弟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說話、練武,有認得他的便上來行禮。
他隨手還禮,忽見有相的教諭過來,便上去見禮,問道:“先生今日可曾見過謝瑛?知道他往哪兒去了麼?”
那教諭也客客氣氣地拱手答道:“謝千戶散堂后與張尚書一道走的,世子若尋他們,便到講堂后廳看看。他如今學問深了,竟能跟張尚書聊得起四書,真難能可貴。”
孫應爵聽得牙疼,連忙跟他分手,找到講堂后面,正見到謝瑛和張尚書在門口說話。張尚書手里還拿著本薄薄的書,封皮上印著打眼的《四書》,底下還有什麼字被他手指住了,看不清楚。
張尚書溫煦地說:“我做左侍郎時便在這里升堂會講,也算是看著你長大的,知道你一片向學之心。如今的武職子弟和們可比不得你們當年……”
謝瑛垂眸微笑著說:“下當年也是渾渾噩噩,只讀《武經七書》《大誥武臣》時用心些,哪里知道圣賢之書的好。若不是后來見那位小友讀書勤苦,也生出自省之心,又怎會重燃向學之志。今日我將這些書送到武學來,也是盼著更多子弟能出勤學之心,不只作一鄙莽夫。”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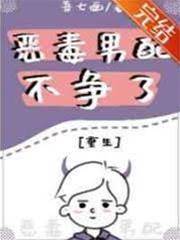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0242 -
完結239 章

替身受假死之后
許承宴跟了賀家大少爺五年,隨叫隨到,事事遷就。 哪怕賀煬總是冷著臉對自己,許承宴也心甘情願, 想著只要自己在賀煬那裡是最特殊的一個就好了,總有一天自己能融化這座冰山。 直到某一天,賀煬的白月光回國了。 許承宴親眼看到,在自己面前永遠都冷淡的男人,在白月光面前卻是溫柔至極。 也是這時,許承宴才知道自己只是一個替身。冰山是會融化的,可融化冰山的那個人,不是自己。 狼狽不堪的許承宴終於醒悟,選擇放手,收拾好行李獨自離開。 而當賀煬回來後,看到空蕩蕩的公寓,就只是笑著和狐朋狗y打賭:不超過五天,許承宴會回來。 第一天,許承宴沒回來。第二天,許承宴還是沒回來。 一直到第五天,許承宴終於回來了。只是賀煬等來的,卻是許承宴冷冰冰的屍體,再也沒辦法挽回。 三年後,賀煬依舊是那個高高在上的賀家大少爺。 在一場宴會上,賀煬突然看見了一道熟悉身影。賀煬失了態,瘋了一樣衝上前,來到那個黑髮青年面前。 “宴宴。” 向來都冷淡的賀家大少爺,此時正緊緊抓著青年的手不放,雙眼微紅。 “跟我回去,好嗎?”而耀眼的黑髮青年只是笑著,將男人的手移開。 “抱歉先生,您認錯人了。”渣攻追妻火葬場,1v1。 受假死,沒有失憶。假死後的受一心沉迷事業,無心戀愛,渣攻單方面追妻。
50.5萬字8.18 51379 -
完結143 章
願以山河聘
原名《嫁給暴君後我每天都想守寡》 秦王姬越是令七國聞風喪膽的暴君,卻有這麼一個人,風姿羸弱,面容楚楚,偏敢在他面前作威作福。 年輕的帝王沉眸望著美麗動人的青年,還有抵在自己脖頸上的一把冰冷匕首,語似結冰。 “衛斂,你想造反?” 衛斂含笑,親暱地蹭了蹭他的唇:“你待我好,我就侍君,你待我不好,我就弒君。” _ ——孤攜一國作嫁,不知陛下可願否? ——願以山河聘。 1.對外暴戾對受沒辦法攻vs腹黑淡定美人受 2.甜文HE,非正劇 3.架空架空架空,朝代是作者建的,不必考據 扮豬吃虎/強強博弈/並肩作戰/至死不渝 想寫兩個魔王的神仙愛情
39.5萬字8 64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