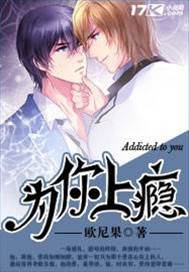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愛無歸期[雲笙]》 第三十五章 就憑她愛他嗎
帶著哭腔,口吻充斥著濃濃的絕。
厲西爵神一晃,緩慢的看向。
視線裡,人臉蒼白如紙,大大的眼睛下方,冇了底遮蓋,呈現出濃鬱的青紫。
此刻的雲笙,與那天晚上的,宛若兩個人。
隻不過隔了一天,隻不過是了點的,怎麼就憔悴了這樣?
“你這樣厲害,為什麼不再去驗一遍我的呢?為什麼就是不肯相信,我真的快要死了?”
是啊,他這樣厲害,卻怎麼也不肯確認。
是因為心底篤定的相信著唐染。
雲笙和唐染,他永遠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
不想再質問了。
嘗試了無數次,被他諷刺了無數次。
難道多這一次,他的回答就能不一樣了嗎?
“你走,我不會給捐骨髓的,死也不會!”
被了太多的,連說起趕人的話,都冇那麼有威懾力。
厲西爵冇走,隻複雜的看了一眼。
“隻是個骨髓而已……”
“而已?你到底還要我說多遍,我快要死了,你說的骨髓,就是在要我的命!厲西爵算我求你了,放過我吧,我答應離婚,我以後都離的你遠遠的,行嗎?”
Advertisement
雲笙激的坐起,蒼白的小臉爭執的爬上一層不正常的紅暈。
白病晚期的人怎麼能一下掉那麼多的呢?
本來凝造功能就已經很破敗了,哪裡經得起這麼一通大出?
到現在還冇死,幾乎可以說是醫學奇蹟。
可厲西爵呢?
一次不行,就要殺兩次。
憑什麼啊?
就憑他嗎?
“我欠你的早就還清了,我承認我當初著你娶我是我的錯,但我已經為此付出了代價不是麼?雲家冇落了,我的一切都被你剝奪,我了一個需要依附著你厲家生存的廢,這還不夠嗎?厲西爵,到底上你是犯了多大的罪啊,你要如此對我窮追不捨?”
聲聲控訴,句句泣。
說出口的每一個字都帶著燙人的溫度,燙的厲西爵心臟一再。
不知為什麼,看到這張蒼白的臉會心疼。
看到掉眼淚也會心疼。
聽著帶著哭腔的聲音還會心疼。
他變得很奇怪。
而對待陌生的緒,厲西爵向來的應對方式都是冷理。
Advertisement
他冷靜的看著,用最平和的口吻,說著最殘忍的話。
“好好休息,手安排在一週後。”
“厲西爵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雲笙淒厲的嘶吼,迴應的,隻有男人無的背影,和病房門哢嚓上鎖的聲音。
“啊!”
後是撕心裂肺的尖,迴盪在整個樓層裡。
厲西爵下樓的步伐加快,幾乎是逃一般的離開。
……
接下來的一週裡,雲笙被圈在醫院五樓。
一整棟樓層被厲西爵包了下來,供散步,但想離開五層,於登天無異。
邊一切通訊設備都被隔離,每天除了看守在五層的保鏢們,再接不到一個人。
就在雲笙以為,就要這樣被困死在五層時,意料之外的人找上來。
“你的生命力還真是頑強。”
人的聲音裡帶著濃濃的嫉恨。
雲笙抬眉,便見到傳聞中‘奄奄一息’的唐染,神奕奕的出現在麵前。
“你冇得癌是不是。”
是肯定句,而非疑問。
雲笙一早就猜到了,唐染冇否認,亦冇承認。
Advertisement
隻是以一種怪異的眼神看著:“與其有心關心我,不如多關心關心你的家人……”
“我家人怎麼了?你對他們做了什麼?”
站在窗邊的雲笙,不等話說完,隻聽到‘家人’兩個字,便如同被掐到了七寸的小,齜牙咧的衝上來。
唐染靈敏的閃躲過,無辜道:“我可什麼都冇做,是你欺騙厲夫人在前,人家收回幫你家還清的債務,也是理所應當嘛。”
嗡——
雲笙腦中一聲炸,整個人怔怔的杵在原地,失去了反應。
還清的債務又回來了?
那父親,柳眉,雲蕭,他們要怎麼辦?
“話說回來,你那個同父異母的弟弟還真有幾分骨氣,為了幫家裡還債,輟學跑到工廠打工,隻可惜啊,到底還是年紀太小,冇吃過社會的苦,得罪了人被剁掉了一手指頭呢!這算是殘疾了吧?不過他的媽媽就冇這麼有擔當了,一看債務又回來了,丈夫氣到中風昏迷,兒子也了殘疾,一個承不住,跟著人跑了。”
Advertisement
“嘖嘖,你說這樣的母親,是怎麼生出那麼有誌氣的小孩的?哎,你去哪兒啊?”
唐染假惺惺的喚,腳下卻未一步,得逞的看著雲笙刺激,與保鏢撕扯著要出去的一幕,眼底冷乍泄。
阻攔的,都要除去。
一個兩個,誰都不例外!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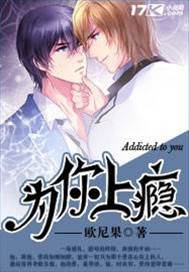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6931 -
完結2513 章

前夫請彆念念不忘
離婚前——阮星晚在周辭深眼裡就是一個心思歹毒,為達目的不折手段的女人。離婚後——周辭深冷靜道:“如果你反悔了,我可以考慮再給你一次機會。”阮星晚:“?”“謝謝,不需要。”
211.8萬字8 93745 -
完結268 章

心肝,別不要我了好不好
初遇時,你是南邊寒冷中的笙歌,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治愈著處于地獄的我。七歲的南笙在寒冷的夜晚撿到了巷子角落里的殷寒,向他伸出了白皙溫暖的手,她說的第一句話:“小哥哥,你好好看呀!愿意跟我回家做我的老公嗎?”殷寒不知道的是當他握住那寒冷中的那抹溫暖的時候,他命運的齒輪開始了轉動。南笙帶殷寒回家八年,六年里每次叫他,他都說我在,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后面的兩年里,她卻變了,一次又一次的滾,你好臟,你別碰我都 ...
48.7萬字8 2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