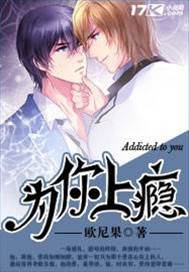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大叔,愛你蓄謀已久》 第七十九章:我和她認識了15年
房間里很安靜,安靜到令人到抑。
江浪拍打的聲音在耳邊還是十分清晰,吹來的晚風也是依舊清爽,可空氣中卻彌漫著說不清道不明的苦。
就如站在這看著面前高大沉默的任景西,近在咫尺卻遙不可及。
往后退了幾步,讓自己所有的在如此波瀾的況下慢慢的一點一點平靜。
“我會從江園搬出去,你和何雨的事從來就和我沒有關系。”
是多次失后的麻木與無于衷,才會漸漸演變如今的結果。
任景西著也聽的清楚,他明白這個道理可接卻永遠都是另一回事。
程安走了,轉離開的時候沒有再去看他一眼,腳步有些匆忙可又是堅定,在離開的道路上好似一直都是這麼果斷。
聽到關門聲任景西仿佛才回過神來,他邁了步子想去追可卻又生生的忍了上下,他有些無力的跌坐在搖椅上高大的形變的不堪一擊。
他明白此時的程安就像繃著的弦,他越努力便繃的越,最后的結果也只是弦斷了兩敗俱傷,而他永遠失去。
可這永遠都不是他想要的結果,雖然不在預料之中但即然今天他選擇將說出來那麼他就會去付之行。
不管程安有沒有相信他所說的一切,他也會讓留在邊,就像當年不顧一切阻礙把葬禮上領回家一樣。
Advertisement
既然故事的開始是從把程安帶回來算,那故事的結尾也只能是他們相伴著老去。
——
和任景西的不歡而散還是影響到了程安的緒,不過好在最近于煒也只是找了兩次聊了聊其他的工作,沒再提起任氏的新項目好似已經放棄了不再勸了。
為此程安也是松了口氣,專心致志的看起其他的項目很快的敲定了下來。
而另一方面程安也開始找起了房子,任紹揚知道這事后立馬就沖了過來。
“你和我小叔咋了,怎麼就突然要搬出來了。”
程安不想再提起那天發生的事,只是搖了搖頭說了句沒有什麼。
任紹揚看著奇怪可見別扭不愿意說的樣子便也沒再追問,不過心里也能夠猜的七七八八,估計是和任景西吵起來了,并且還嚴重的。
“對了。”任紹揚拿著雜志晃悠的手突然停了下來看向:“那天我們不是到了程敏榮了麼,我就順便查了查。”
程安本在敲鍵盤的手停了下來向他看去,聽著見他繼續說著:“程敏榮之前一直在外地是今年九月份的時候才到笠市的,后來就一直住在那。”
“九月份?”程安頓了一下:“和我回來的時間就隔了半個月。”
“嗯,而且我還查到兒子坐牢的事。”任紹揚挑了下眉,明顯是查出來了什麼事。
Advertisement
他站起來走到程安的辦公桌前坐下,有些吊兒郎當的樣子吊著程安的胃口。
程安嘖了聲有些不悅還沒得說些什麼任紹揚便已經識趣的不賣關子了。
“他賭博把人打傷住進了ICU不假,可這卻不是他坐牢的主要原因。”任紹揚手指輕輕敲了下桌面:“是詐騙勒索。”
程安微微一怔回憶著當初程敏榮第一來找的時候可沒提到詐騙這個事啊,只是說因為打傷了人坐的牢。
“而且你知道他詐騙的誰嗎?”
“誰?”
任紹揚笑了笑湊近了些小聲道:“李楠。”
“什麼!”程安皺起眉有些不可置信的著他,驚訝到緩了好一會兒才問道:“他怎麼會認識李楠,他們怎麼又扯到了一起。”
門口于煒正好路過旁邊站著過來談事的任景西,好巧不巧的聽到了程安的驚呼聲下意識的便停了下來朝閉著門過去。
于煒好似已經見怪不怪笑了下對任景西說道:“是紹揚來了,他倆有時候就會這樣,可能聊到什麼高興的事了。”
聽到任紹揚的名字任景西的眉頭便好像擰了麻繩,目再一次落到了閉的房門上。
于煒看見任景西的目心里有些忐忑,這濃烈的占有不太妙呀。
想了想便抬了下手將任景西引到辦公室,假裝閑聊似的說著:“最近小安好像有心事,不過好在紹揚總是過來陪。 ”
Advertisement
任景西進了辦公室在沙發上坐下,手搭在扶手上有一下沒一下的擰的袖扣,沒說話只是聽著于煒說。
“小安不愿意參加這次的項目我也惋惜的,不過我后來想了想便也尊重了的決定。”于煒眼里帶著些許的贊許說道:“聰明能干是個好幫手,可畢竟在國還沒有什麼特別響亮的績,一下子就當了任氏項目的主負責人,難免會到一些他人的目和猜忌。”
“想要穩扎穩打也不是什麼壞事,等以后有機會了大家也可以再合作。”說著于煒了任景西一眼話里有話繼續道:“再說現在和紹揚關系的好,說不定以后還是一家人,而且到時候你的事也定下來了大家做起事來也會更方便。”
多麼明顯的意思任景西在商場里混了這麼多年,怎麼可能會聽不出來。
他垂著目似是云淡風輕的擺弄著袖扣,半晌才悠悠的更像是自言自語的說著:“任紹揚和程安認識多年了?”
于煒愣了一下有些沒反應過來想了下說道:“他們一起出的國又是一個大學的,怎麼說也得有個七八年了吧。”
任景西抿了抿角有些慢不經心的點點頭,接著抬起頭看向于煒說道:“可我和程安已經認識了十五年了。”
從十二歲時的天真稚到二十七歲的干煉,這十五年的時間是無論誰都不走也比擬不了的。
Advertisement
于煒整個人愣住詫異的著他,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了問題,畢竟他從來沒有聽程安或者是任紹揚任何人提過。
“或許您老不知道,從程安十二歲我把帶回任家的時候起,就是一直在我邊長大的。”
只是除了他不在的那五年,讓任紹揚鉆了空子。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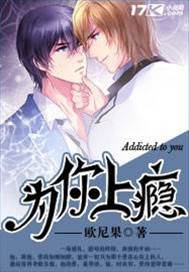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6940 -
完結2513 章

前夫請彆念念不忘
離婚前——阮星晚在周辭深眼裡就是一個心思歹毒,為達目的不折手段的女人。離婚後——周辭深冷靜道:“如果你反悔了,我可以考慮再給你一次機會。”阮星晚:“?”“謝謝,不需要。”
211.8萬字8 93747 -
完結268 章

心肝,別不要我了好不好
初遇時,你是南邊寒冷中的笙歌,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治愈著處于地獄的我。七歲的南笙在寒冷的夜晚撿到了巷子角落里的殷寒,向他伸出了白皙溫暖的手,她說的第一句話:“小哥哥,你好好看呀!愿意跟我回家做我的老公嗎?”殷寒不知道的是當他握住那寒冷中的那抹溫暖的時候,他命運的齒輪開始了轉動。南笙帶殷寒回家八年,六年里每次叫他,他都說我在,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后面的兩年里,她卻變了,一次又一次的滾,你好臟,你別碰我都 ...
48.7萬字8 26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