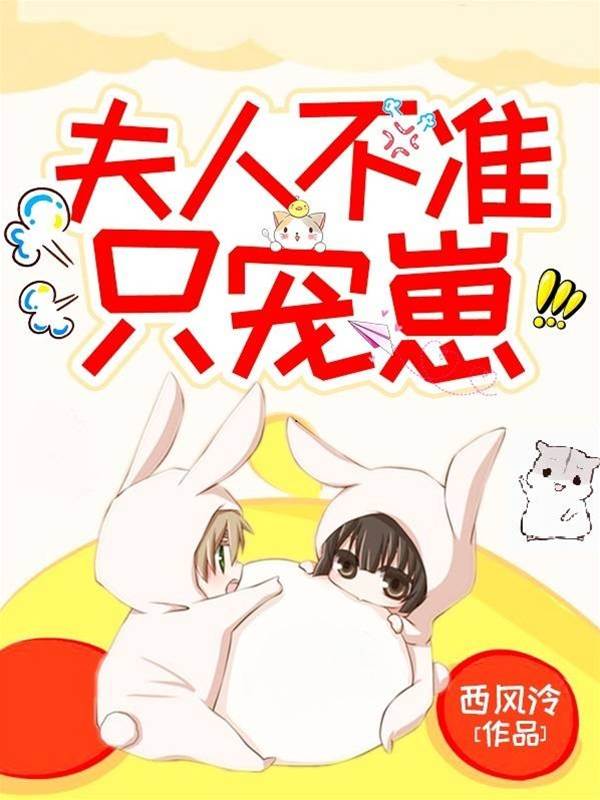《農女珍珠的悠閒生活》 第二十三章夜話
“工價不錯嘛!”珍珠託著下邊聽邊想。
這時候一個包兩文錢,一斤豬十八文,一天三十文對於平民百姓算是很不錯的工錢了,以往胡家兄弟去鎮上打散工,工價多是十八文到二十五文之間。
“柳叔說開春後何家還要修繕一院子,給我們留意著,如果要請人的話便稍話給我們。”胡長林話裡帶著一激。
他話裡的柳叔是同村的遠親,名柳常平,年紀不比他們大多,但輩分卻大了一輩,他家地孩子多,家裡也是不敷出,只能時常在附近的鎮上尋些散工過活,一年下來日子過得卻頗爲不錯,只是這散工時多時沒有個定數,家裡有田地的人是不會專門以此爲生的,多數也只會像胡家兄弟一樣,利用農閒的時候掙些力氣錢。
“常平人不錯,以後他有啥事記得多幫襯些,咱做人可不能忘恩,對咱好的要記住。”胡老爺子酒足飯飽,臉紅潤起來,一邊說著話一邊小口的喝著酒,臉上的表很是滿足。
“喝些酒,一喝酒就停不下來,長貴,給你爹盛碗蘑菇湯,這湯可鮮了,這可是你姑娘採的,兔子也是你姑娘捉的,我們可是沾了的才能吃得這麼舒服。”王氏笑著誇獎著珍珠。
“,瞧你說的什麼話,要不是你的廚藝高超,這菜能這般好吃,我們是沾了的纔對。”高帽子直管往王氏頭上戴。
老太太頓時樂開了花,咧大笑,“這丫頭,還學會奉承人了,可真甜。”
“,我姐說得對,你做的菜最好吃了!”平安著圓溜溜的肚皮滿足的說道。
“對呀!對呀!做的飯菜最好吃了。”一旁的平順附和著。
Advertisement
王氏被孫兒們一陣讚揚,樂得眼睛瞇了一條,一頓晚飯便在歡快的笑鬧聲中愉快的度過了。
晚飯過後,胡長貴領著兩姐弟便要回家去,王氏練的從鍋裡拿出特意給李氏留著的菜,放到籃子裡用花布蓋好,到胡長貴手裡,囑咐道:“快回去吧,容娘該等急了,今晚好好歇歇,明天還有好多事要幹呢,明早你和長林照著珍珠的法子試試看能不能薰著兔子,記住不要讓人看到,下午還得去砍柴,過冬的柴火得備多一些,我這烘乾蘑菇費了不乾柴,喲,事都湊一塊了。”
王氏皺著眉頭絮叨著。
“娘,不著急,能幹完的。”胡長貴低頭憨笑著看著。
“娘知道,好了,快回去吧。”王氏拍拍小兒子的手背,心疼的看著他半垂的臉,略長的劉海遮著了傷痕,一想起那一次意外重傷差點要了他的命,王氏心裡便陣陣疼。
“,我們走了。”珍珠揮揮手,拉著平安踏上了回家的路。
胡長貴默默地跟在孩子後面,平安回過頭跑到了他邊,笑著說:“爹,咱家現在有好多兔子呢,明早我和爹一起去薰兔子吧,我教你怎麼薰,好不?”
平安揚著小臉一臉期。
胡長貴微笑著答道:“好。”
“爹,姐說不能把一山頭上的兔子捉完,要不來年林子裡的大蟲、黑瞎子和老狼就沒有食了,它們就會跑出山林禍害大家了,知道不?”平安繼續發揚著教育神傳播著他這些日子吸收的點點滴滴。
胡長貴聽完,詫異的看了眼走在前方的珍珠,沉默了一會兒纔回道:“知道。”
“爹,最近我餵了好些天兔子,兔子怎樣養我都知道,你要是不懂就問我,好不?”平安繼續。
Advertisement
“好。”
“爹,前幾天我和姐採蘑菇的時候捉了一條黑斑蛇,這麼長一條。”他誇張的比了個長度“姐用樹叉把它叉住,我就把蛇敲死了,厲害不?”
“厲害,不過,下次讓爹來捉。”
“爹,…………”
珍珠聽得角直,這一大一小,一個滔滔不絕一個言簡意賅卻能聊個不停,還是老實的當個安靜的子吧。
一路黑回到家,李氏已等候多時,胡長貴遠遠見著李氏加快了步伐,走近後主靦腆的說道:“榮娘,我回來了。”
李氏溫一笑,接過他手裡的包袱,示意他們進屋。
“娘,你晚飯還沒吃呢,菜都涼了,先吃飯吧。”珍珠拿過裝菜的籃子,把裡面的菜拿出來放在桌上。
胡長貴家一家團聚,除了樂呵的平安嘰嘰喳喳個不停外,其他的人都各自吃飯洗漱各行其是。
是夜,看著一旁睡的平安,胡長貴從包袱裡翻出一貫銅錢,遞給李氏,低聲說道:“榮娘,這是這些日子掙的,你收好,爹孃那邊給了二兩百文,是今年該孝敬老人的,我就提前給了。”
李氏含笑點頭,也不細數錢銀,接過後鎖進了炕邊的櫃子裡,然後找出胡長貴的裳,遞了過去,早早燒好了熱水,外出多日洗澡不易,每次出門回來總要從頭到腳徹洗一番,胡長貴不多話,接過裳便自行洗刷去了。
這廂,老宅東屋的炕邊王氏和胡長林還在忙著烘蘑菇,胡老爺子也坐在一旁編著竹筐,三人邊幹著活邊說著話。
“娘,這一個多月掙了一千一百一十文,後面三天下雨沒幹活,所以了九十文,裡面還有臨走前你給的二百文錢,來回的路上坐車買吃食花了二十文錢。”胡長林從懷裡掏出個沉甸甸的錢袋子遞給了王氏,老宅的銀錢一直由王氏管著,胡長林很孝順,從未對錢銀問題有過意見,即使梁氏私下埋怨過他,他也沒在意過。
Advertisement
王氏欣的笑著,從錢袋裡掏出兩串銅錢遞給他,溫和的說:“這兩百文給你媳婦收著,需要添減什麼你們自己買,剩下這些娘收起來,年前得把債給還上。”
“娘,這也收起來吧,我們不缺啥,先把這債給還上。”胡長林推辭著。
“給你就拿著,這些年家裡也沒能存上什麼錢,手頭總是不寬裕,今年只要這些幹蘑菇能賣個好價錢,那咱們就能把債都還上,明兒要是能捉上幾窩兔子,今年就能有些餘錢了,咱們勤快些,日子總能過好的。”王氏輕輕的翻著蘑菇,這些可都是進財的寶貝,得小心伺候著。
“知道了,娘,明一早我和長貴就去試試,不過這珍珠咋知道這些呀,一個小姑娘上哪聽說的?”胡長林有些疑,他不像胡長貴,除了埋頭幹活啥也不懂。
王氏笑了笑,把彭大強的事告訴了他,隨後囑咐他不要告訴別人免生是非。
胡長林點頭應著,直道珍珠是個有福氣的,胡老爺子一旁側聽倒也不多話,只是待著別說,以免給胡家帶來麻煩,一陣閒聊後才各自歇下。
隨後的幾天,胡氏兄弟忙得不可開,早早起來便揹著籮筐進了山林,胡長貴只帶平安去了一次山林,其後兩兄弟爲了防止被人看到,便進了更深一些的老林子裡,經過了開始時的手忙腳,到後來兩人分工明確合作無間一逮一個準,胡家的兔子倍的增長著,不過,兩人都記著珍珠的話,不能把一個山頭的兔子一網打盡,跑了幾個山林後,天氣漸冷,採蘑菇和逮兔子的工作便停了下來。
兩家的柴火都沒準備好,胡長貴家的兔舍也得從新建一個,如今他家裡的舍早就不夠用,還有一些兔子關在柴房了,珍珠還說了,兔子需要活空間,要不,不吃食不長。
Advertisement
爲了不引起村裡人的注意,兔子都養在胡長貴家,公兔放一塊即打架又撞欄,母兔也不時的發生撞,珍珠有些不勝其煩,也知道,野兔不是家兔,不是那麼容易圈養的,好在,用空間產的蘿蔔白菜葉挨個餵養一兩次,它們就都老實了些。
不過,珍珠還是建議先把那十幾只公兔先賣掉,年公兔吃草也不長了,放在家中養著也是浪費草糧,只需留兩隻雄壯的公兔配種即可。
珍珠和平安每天都在忙著囤積草糧,翠珠和平順也不時幫忙,就怕冬天沒過完兔子都沒了口糧。
珍珠的建議得到了王氏的支持。
於是,某天清晨,胡氏兄弟各自揹著四隻公兔,帶上珍珠一路抄著小道走出瞭林村,按胡長林的意思原是不帶珍珠去的,從村裡到鎮上大人步行都得一個時辰,而珍珠還是個小姑娘,速度還要慢些,坐車倒是能快些,可坐車的人都是本村的,他們揹著的兔子本就遮掩不了,所以還是得辛苦些走路去。
珍珠怎麼可能錯過去鎮上的好時機呢,到這個時代這麼久了,連村子都沒出過,不趁此機會出門,估計等到猴年馬月都沒機會出去了。
也不理會胡長林,只和王氏說明要去鎮上打探一下養兔子的前景,兔子養得多了也要有銷路才行,總不能自己都吃了吧,珍珠的話惹得王氏哈哈大笑,當即拍板讓跟著去鎮上,珍珠臉上不顯,心裡卻笑開了花。
猜你喜歡
-
連載942 章
陰婚不散:鬼夫大人狠狂野
繼承奶奶的祖業,我開了一家靈媒婚介所。一天,我接了一單生意,給一個死了帥哥配冥婚,本以為是筆好買賣,冇想到卻把自己搭了進去。男鬼帥氣逼人,卻也卑鄙無恥,鬼品惡劣,高矮胖瘦各種女鬼都看不上。最後他捏著我的下巴冷颼颼的說:“如果再找不到合適的對象,你就要自己上了。”我堅決拒絕,可惜後來的事情再也由不得我了……
168.7萬字8 10233 -
完結71 章

第二春
【1】林念初愛慘了梁辰,倆人相戀七年,結婚三年,梁辰卻出了軌,小三懷孕上門逼宮,林念初毫不留情直接離婚,從此之后看破紅塵、去他媽的愛情!程硯愛慘了心頭的朱砂痣、窗前的白月光,然而卻被白月光虐的死去活來,從此之后看破紅塵、去他媽的愛情!某天晚上,林念初和程硯在某個酒吧見了面,兩個去他媽愛情的單身青年互相打量對方,覺得可以來一場,于是一拍既合去了酒店。一個月后林念初發現自己懷孕了,和程硯商量了一下,倆人決定破罐破摔,湊合一下過日子,于是去民政局扯了證。【2】某...
31.1萬字8.38 55510 -
完結10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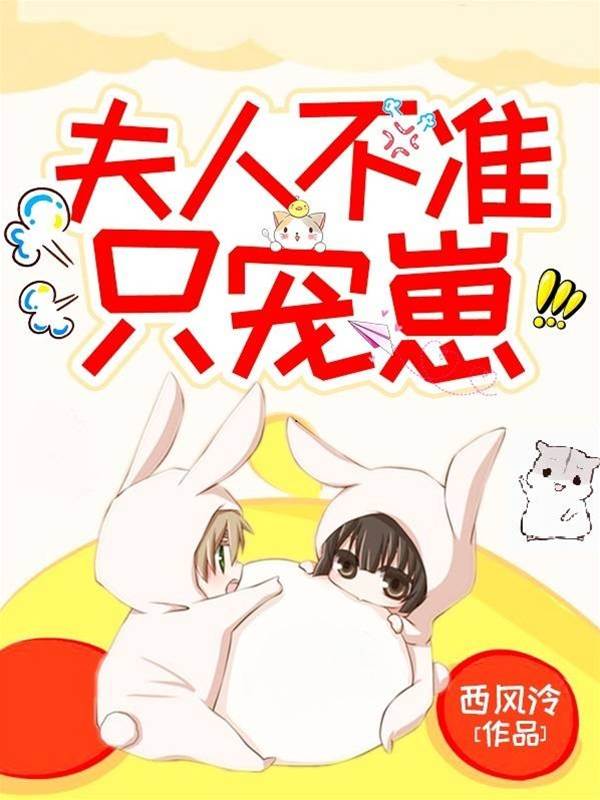
夫人不準只寵崽
南悠悠為了給母親治病為楚氏集團總裁楚寒高價產子,期間始終被蒙住眼睛,未見楚寒模樣,而楚寒卻記得她的臉,南悠悠順利產下一對龍鳳胎,還未見面就被楚家接走。
24.6萬字8 7964 -
完結150 章

許你一片深情海
【小甜餅+女主視角先婚後愛+男主視角蓄謀已久+男女主嘴毒且損+追妻火葬場+雙潔】*英姿颯爽女交警x世家混不吝小公子*所有人都以為京北周家四公子周衍喜歡的是陸家長女陸蕓白,結果他卻讓人大跌眼鏡地娶了妹妹陸苡白,明明這倆人從青春期就不對盤。兩人三年婚姻,過得談不上好,也談不上壞。一個不上心,一個看似不在意。陸苡白以為這輩子就糊糊塗塗地和周老四過下去了……結果陸苡白卻意外得知當年婚姻的“真相”,原來周衍比所有人以為的都要深情,不過深情的對象不是她而已。 他是為了心愛的人做嫁衣,“犧牲“夠大的!睦苡白一怒之下提出離婚。 * 清冷矜貴的周家四公子終於低下高昂的頭,狗裹狗氣地開始漫漫追妻路。 陵苡白煩不勝煩:“周衍,我以前怎沒發現你是一狗皮膏藥啊?“ 周行:“現在知道也不晚。我就是一狗皮膏藥,這輩子只想和你貼貼。“ 睦苡白:“.好狗。
27.2萬字8 84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