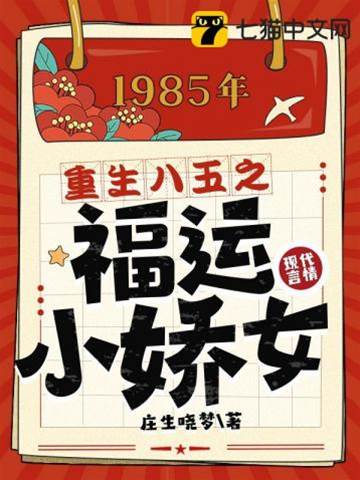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基因迷戀》 第84章 番外六
每一次S星大選前后,住在總督山附近的居民都會變得異常張。
一個盲慢慢地在街頭行走。智能盲杖在地上輕輕敲,避開障礙。
耐不住幾個小孩子在街頭嬉笑打鬧,直直地撞進的懷里。
小孩子們不懂事,慌忙道了歉,仍然像樹上黃鸝一般嘰嘰喳喳。
盲微微蹙眉,語氣嚴厲:“都快到大選日了,你們怎麼還敢在外面玩?快回家吧。”
后一個清亮的聲音道:“大選日怎麼了?”
“大選日……”言又止。
手指用力地攥了盲杖,聲音因為莫名的緒而收。
但路嘉石并沒有在意。
他蹲在地上,孩子王一般,隨口將這幾個混小子教育了一番。又拍拍膝蓋站起來,很好心地問:“你要去哪里?我帶你一起。”
“槍械商店。”對方鎮定地說。
與這細細的聲音形鮮明對比的,是語氣里的冷。
路嘉石笑道:“去那種地方干嘛?”
對方睜著黯然無的眸。
假如不是失明,這本該也是雙漂亮的眼睛。
“不是說了嗎?”輕聲道,“大選日快到了。”
路嘉石一怔。
接著才明白這個孩話里真正的含義。
的視力,就是在大選日失去的。
十年前。
S星的混由來已久。
而大選之夜,就是一次很好的發泄機會。
新總督的支持者會通宵游街,徹夜狂歡。槍炮,酒,吶喊,飛揚的旗幟。他們用各種瘋狂的方式來慶祝自己的勝利。當然,不能避免地,他們會和另一幫人,失意的選民,大打出手。
在這樣的時刻,政治只不過是個尋訊滋事的由頭。事件總是是會從群激的械斗,演變一場無因的大破壞。
Advertisement
夜飾了一切的暴力、、憤怒和趁火打劫。失控的人群會開槍、縱火、打碎商店的櫥窗。甚至于無意中經過的路人,也會變被狩獵的羔羊。
而十年前,盲眼中所見的最后一幕:是家門口一向黑黝黝的巷子,罕見地被明亮的火照耀起來。人群稠,擁不堪。一張張紅彤彤的臉,也像是著了大火。
這之后,和弟弟就被那群人團團圍了起來。
……
十年后再度回憶起這一幕,那一切依然太過清晰。不是噩夢,而是一部VR電影。一雙慘白的手,立刻將拉進那個纖毫畢現的世界里。
仿佛再次置于火海,灼熱的日曬得大汗淋漓,額頭滿是汗。
盲不打算再打算跟路嘉石說什麼,轉過去。
“繼續導航。”吩咐智能盲杖。
但路嘉石卻仍然在后,以一種愉悅的語氣對說:“你去了也沒用。所有的槍械商店都已經關門了。”
腳步頓住:“為什麼?”
“因為大選日啊。”他笑嘻嘻地說。
他快步走到街角,將槍械商店門口的那則停業通知,毫不在意地撕下來,塞進的手里:“喏,你自己讓人念吧。”
兩周后,大選日當天,盲和弟弟坐在家中投影前,等待大選結果的時候,的手中仍然用力地握著這張皺的紙。
盡管這段文字,已經反反復復地讓盲杖為自己念過太多次,以至于都能夠倒背如流。
【停業通知:為配合限時槍令,維持公共安全,本店將于競選期間暫停營業。請各位市民注意,槍令期間,嚴攜帶攻擊武出行。】
大選進行得相當順利。S星以從未有過的高效,迎來了自己的新任總督。
Advertisement
在聽到選舉委員會念出Chase的名字的時刻,他們全家人都抱在一起,痛哭出了聲。
“太好了!”
“以后再也不用擔驚怕了……”
連盲都不能不為之容。
淚水從干涸已久的眼眸里奪眶而出,像是決堤的河岸。
槍令。
心想,等待這個詞,已經等了十年。
假如十年前就有這樣一個人出現,那麼也不必被孤零零地拋在黑暗里。
可是,從未有人真正關心過普通人的生活,真正想要去改變這不安的現狀。不是高喊著那些虛無的口號,而是切切實實地為他們做點什麼。
直到現在。
的弟弟在一旁,好奇又小心翼翼地趴在窗口朝外看——
這麼多年來,這是第一個大選之夜,他們膽敢拉開窗簾,而不是躲在厚厚的墻壁背后,瑟瑟發抖,害怕再一次被外界的所波及。
街上仍然人流如織,人們興得滿臉紅,甚至于眼泛淚花。
有人在放聲歡呼與高歌。有人在倒立和狂奔。騎托車的機車黨在瘋狂地按著喇叭。
不知是誰在放煙花。漆黑的天空上,絢爛的禮花層層疊疊綻開。五十的夜。人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慶祝史上支持率最高的總督的到來。
但這一場狂歡始終秩序井然。
每一個街角,都站著嚴陣以待的星際警察和巡邏的AI。
盲聽著弟弟為自己描述街頭的景象。
“也許從今往后,S星是真的要不一樣了。”他充滿希冀地慨道。
“嗯。”也輕聲道,“是真的要不一樣了。”
因為他們選了一個對的人。
當然,并非所有的S星居民都在今夜滿懷希,期盼自己的新未來。
總有人還是愁容滿面,臉灰敗。
Advertisement
例如S星的現任總督梁嚴。
他清楚自己鬧了一個多麼大的笑話:他是過去的五十多年里,S星第一位連任失敗的總督。
但敗象也早已被預見了,梁嚴甚至沒有留在總督山,而是在一座私人府邸里,觀看了競選的全過程。他數次因為雙方票數之懸殊,而氣得砸爛了書房里大部分的花瓶與石膏像。
滿目瘡痍,一如他慘淡的政績。
幕僚在旁邊小心翼翼地建議道:“大人,要不要出去散散心,打一場高爾夫球?”
“哼。”梁嚴冷笑一聲,“打什麼球啊?”
“Chase不是要發表獲勝演講了嗎?我倒想看看,他能夠再睜著眼說些什麼瞎話。”
結果梁嚴還當真如愿地從這次演講里找了些樂子出來。
在他眼里,池晏一向是個巧舌如簧的惡魔。
每一次與他辯論,自己總是被制得死死的。
但他沒有想到,在這次獲勝演講里,他竟然連自己平日三分之一的水準都沒有發揮出來。
“這小子在搞什麼?”梁嚴幸災樂禍地說,“來不及找人寫稿子了嗎?我從來沒聽過這麼簡短的獲勝演講。”
幕僚在旁邊附和道:“到底是個頭小子,一站在高位就了馬腳。他哪里能有大人的一半沉穩呢。”
梁嚴面得,又乘勝追擊地問道:“那麼我吩咐你的事,辦得怎麼樣了?”
眾所周知,大選之夜就是混的溫床。因此他也私下安排了一些人,故意在今夜攪渾水,制造一些小混。即使這些事不可能撼對方的地位,至給他潑一點臟水,也足夠大快人心。
但幕僚卻支支吾吾起來,半天說不出個準話。
最后在梁嚴的迫之下,才終于坦白道:
Advertisement
“大人,您也知道,Chase之前就直接越過咱們,通過議會頒布了槍令,今天又讓全城的星際警察都出去巡邏……這樣的局勢,再想要暗中做些什麼,實在是有些難度了。”
梁嚴重重地“哼”了一聲:“說來說去,你們就是不敢手了?趁火打劫罷了,這麼簡單的事也辦不好嗎?”
對方更小心地斟酌著字句:“不是不敢,只是假如貿然鬧得太大,尾卻收得不干凈,反倒不好……這麼多雙眼睛看著……”
梁嚴終于忍無可忍地將書桌上的最后一只花瓶也砸了。
砸完才想起來,那本不是他自己的東西,是總督府的藏品,他不過是借來把玩幾天。
這下完了。
一只花瓶,這當然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那些花邊小報一向最從總督府的下人口中,重金挖出這樣的軼聞。
梁嚴臉鐵青,額頭上青筋直豎,讓幕僚們全都退了出去。獨自看著Chase的獲勝演講——原以為對方是個笑話,其實鬧笑話的還是他自己。
演講無意義地循環播放著,一遍又一遍。沸騰的心也冷卻下來。莫名地,梁嚴突然回憶起五年前,自己大獲全勝的那一夜。
那時候他當然也知道外面鬧得有多。
但站在總督山上,俯瞰塵世,一切都變了瑩瑩的燈火。站得太高,人統統變了螞蟻。一些賤民的打打鬧鬧,與他何干呢?也不過是為他的勝利添一把柴火。
很多時候,有些事,他們并非沒有能力去做。
只是他們不愿去做。
他本以為Chase在競選里一次次地提到“重振秩序”,不過是場政治作秀。畢竟S星的沉疴由來已久,人人都習以為常。
他沒想到,這個年輕人竟然是認真的。
也許他的確是比自己更適合這個位置。
但這些話絕不可能對外人言。
梁嚴又磨蹭了一會兒,才終于決定將早就準備好的敗選演講視頻,發布在了自己的個人主頁上。
過了一會兒,他將自己的副手喊起來,心平氣和地吩咐他說:“給Chase打電話吧。”
這也是一個約定俗的流程:現任總督向自己的繼任者打電話祝賀,象征著總督權力接的開始。
接下來他們會進長達數月的過渡期。
當然,大多數要做都是連篇累牘的文案工作,繁瑣又麻煩。
梁嚴幸災樂禍地想,自己可不是認輸了,只是想讓這家伙早點開始做苦力罷了。
但就在這時,副手尷尬地說:“……沒打通。”
梁嚴:“?”
“那就繼續打。”他一臉黑線地說,“這可不是什麼小事。”
副手在虎視眈眈的注視之下,滿頭大汗地又撥了好幾個電話。
最后一臉尷尬地說:“大人,我剛剛聯系了那邊的競選辦公室。他們說,接下來的兩天,Chase會……休假。”
梁嚴:“???”
為了休假,連他的電話都不接了?
不是——有哪位總督,在勝選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給自己放兩天假啊?!
*
再一次醒來時,松虞也在思考同樣的問題:
這家伙哪里來的時間,跑過來找?
月灑落在波粼粼的海面上。
聽到了波濤的聲音。除此之外,一片靜謐。
他們相擁而眠,卻不知自己在何。
或許真是在時間的海上。
黑暗里,借著窗外微弱的線,凝視著面前這張廓深邃的面容。
古銅的皮被影影綽綽的霓虹,照出了很迷人的澤。
但他在睡著的時候,仍然是微微蹙眉的,莫名地缺生氣,像一尊死氣沉沉的雕塑。
顯而易見,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好好休息過。
正如自己,這段時間以來本忙得不過氣來。
人站到一定的高度,任何東西都變得唾手可得,只有時間。時間對每個人都最公平,所以才對每個人都最殘忍。
而他和能夠共同擁有的時間,才最珍貴和罕有。
于是低垂著眼,更用力地進他的臂彎。
將這個時刻拉長。
一只實有力的手臂,用力地箍著的腰。雙方都像嬰兒一樣,以最不設防的姿勢,蜷在彼此的懷抱里。
目所及,便是凸起的結和鎖骨。
這并不是習慣的睡姿。
通常松虞都是平躺著,一不。一旦睜開眼,就能直直地看到空曠的天花板。影緩緩地浮在墻壁上,隨著窄巷里的路燈,變換出奇怪的形狀。
在遇到池晏以前,一度想過,自己未來的五十年都會這樣度過,在那座小公寓里度過。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和影帝的新婚日記
喬繪這輩子做過的最瘋狂的事情,就是在二十一歲這年閃婚嫁給了正當紅的影帝徐亦揚。婚後的生活平平淡淡。徐先生每天都會給她早安晚安吻,會在外出拍戲的時候不時向她匯報行程。但即便是最親密的時候,他的吻,也是溫柔內斂又剋製的。喬繪鬱鬱地向好友袒露心聲,“他寵我,就好像寵女兒一樣。”到底,還是差了點什麼。徐亦揚新劇殺青的那天,他和劇中女主演的緋聞喧囂塵上,無數c粉徹夜狂歡。喬繪在床上盤著腿,考慮再三之下,提出了分居的要求。這一晚,徐亦揚冒著臺風天的惡劣天氣連夜從外地趕回,全身濕透,雨水浸的他的眼尾通紅一片,“為什麼?”少女穿著居家的粉色小熊睡衣,小臉嚴肅,“我們咖位差距太大了,沒人會認為我們般配。我想,我們可能不太適合。”第二天,一張照片點爆熱搜。空蕩無人的街頭,向來穩重自持的影帝抱著他的新婚小妻子,吻得纏綿又悱惻。
22.2萬字8.18 18726 -
完結118 章
戒不掉的喜歡
俱樂部裏來了個兼職小醫生,長得漂亮,溫柔細致,還特會哄人。隊裏常有天真少年感歎:“以後,找女朋友就要找應歡這樣的,聽話,乖巧,還會哄人……” 隻有把人撩炸了的徐敬餘知道,應歡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真妖精。 職業拳擊手徐敬餘拿到81公斤級金腰帶後接受采訪,記者問:“聽說您每次賽前一個月為了保存狀態和體力,禁欲禁酒,這是真的嗎?” 徐敬餘臉上掛了彩,眉骨和嘴角滲著血,微笑看著鏡頭:“對。” 那會兒應歡就站在人群開外,一臉冷漠地看著他。 同來比賽現場看比賽的好朋友湊過來,好奇問:“真的假的?荷爾蒙爆棚的敬王
42.3萬字8 14548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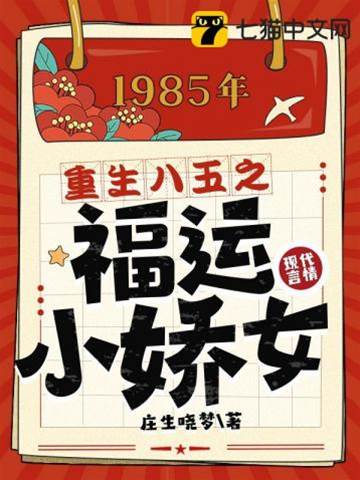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19168 -
完結108 章

心動法則
原書名《你有權保持心動》朱珊和鄰居哥哥凌霄在國外登記結婚,此后四年,未聯系一次。為了調查父母當年的案子,朱珊偷偷回國,入職市電視臺成為一名菜鳥記者。朱珊從小討厭害怕凌霄,在得知此時的凌霄是一個風評不好、未有敗績的‘撒旦’律師后,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一起烏龍,朱珊被押去警局接受調查,因此不得不聯系自己名義上的丈夫,凌霄,并與之同住一屋檐下。強奸案,家暴案,殺人案……環環相扣,抽絲剝繭。真相會浮出水面,愛亦如此。我們,都會站在陽光下。記者的存在,以事實為根據,傳達真相,告知真相。律師的存在,不是為了維護正義,而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心有所信,方能行遠。
32.6萬字8.18 38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