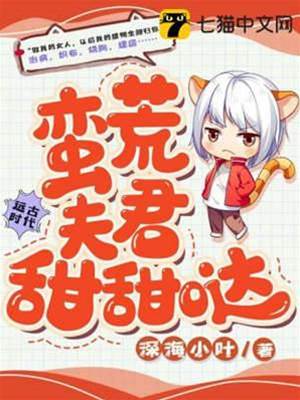《我同夫君琴瑟和鳴》 第85章 帶笑眼
泠瑯僵住, 立即轉頭往后看去。
層層蘆葦之中,赫然立著個著井天藍裳的男子。
男子形頎長,容貌俊雅, 手持一柄未打開的折扇, 見二人過來,臉上閃過訝異之。
“還真是阿瑯?”他遲疑道, “你怎會在此?”
泠瑯道:“鄧前輩, 這正是我想問您的話。”
男子微微一笑, 手中折扇嘩的一聲展開, 扇面赫然書著龍飛舞四個大字——玉樹臨風。
他溫聲道:“落日見蘆草,夏時逢故人。當下正是雁落山風景最好的時候, 豈有不來之禮?”
泠瑯抬手抱拳:“可是我聽沉鶴說, 您上個月賭錢輸了不, 如今正四躲著。”
男子笑容不變, 將折扇搖得嘩嘩響:“閑來縱山水間,不使人間造孽錢。金銀不過外,看淡之后,自然行輕。”
泠瑯點點頭:“您上次賭輸遁走,似乎也是這麼說的。”
男子搖頭嘆息:“已往之不諫,來者猶可追。阿瑯年紀小, 待人觀, 怎麼只局限于以往。”
泠瑯由衷道:“鄧前輩,一年不見,您說話愈發高妙了。”
男子謙虛道:“不過無所事事,只好飽讀終日而已……一年不見, 阿瑯變化也頗大, 竟也開始人約黃昏后, 行風花雪月之事了?”
泠瑯頓了頓:“什麼人約黃昏后,我讀書,聽不大懂。”
男子說:“我剛剛看得很清楚,你正要同旁邊那個公子嘬。”
泠瑯強笑道:“嘬……您誤會了,我是瞧著他眼睛里有東西,幫忙吹一吹。”
手去扯江琮袖子,以作暗示。
江琮頷首:“夫人說得是,之前是我眼睛進了蘆絮。”
男子瞪大雙眼,折扇也不搖了:“他你什麼?”
Advertisement
泠瑯當即有仰天長嘯的沖,雖然此事原本難以瞞過鄧如鐵,但忽然被這麼拆穿,還是讓十分尷尬不適。
江琮倒從容抱拳行了一禮:“鄙人姓江,西京人士,同阿瑯婚已經半年有余。”
鄧如鐵說:“好哦!你這丫頭,消失一年多,原來是去尋俊俏郎君婚了?”
泠瑯心中一,將計就計,一把挽起江琮手臂,親親昵昵地偎了上去。
赧道:“去年末我在西京偶遇夫君,便如那話本子上說的那樣,金風玉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當即難自已,很快就定下來了。”
鄧如鐵嘖聲贊嘆:“什麼俸祿,你還找了個戴帽的?你今兒個必須好好給我代了,江湖水深,魚蝦遍地,我可得好生盤問則個。”
泠瑯早就料到他必定刨問底,當下只能維持著甜微笑,半威脅地拖著江琮的手,跟著鄧如鐵往對岸去了。
鄧如鐵大步流星地走在前,全無方才半分從容不迫,井天藍的風雅長袍被彎起袖口,如隨時要下河捕撈一般。
泠瑯慢條斯理地綴在后面,同江琮低聲說話。
“你可瞧出了這是誰?”
“玉扇公子鄧前輩。”
“你可知道他打算做什麼?”
“想盤問于我,看我是不是小魚小蝦,是誆騙你的。”
“那你打算如何應對?”
“我對夫人一片赤誠,天地日月皆可見證,他問什麼,我從心而答便可。”
“你最好是!”泠瑯惡狠狠道,“先說好,我同你是除夕那晚上認識,我從侯府后門經過,你出來溜達,正巧上了若天仙又冰雪聰明的我……”
江琮輕笑道:“涇川侯世子平日都不會出去溜達,更何況除夕?這編造的不行。”
Advertisement
泠瑯靈一,想到綠袖曾經用過的形容,飛快地說:“那就說,我潛侯府想竊,結果發現了熹園中養病的你,瞧你長得合心意,就天天來找你攀談玩耍。”
“然后呢?”
泠瑯覺得這個思路很對,愈發流利道:“一來二往,你便難自已,無法割舍,百般要求我留下,我被你誠意所打,最終同意和你婚。”
江琮抬手,幫拂去發之中一朵小小的蘆絮,他低聲道:“這的確符合理。”
泠瑯一錘定音:“就這麼辦!你扮演一個深居侯府,不諳世事的病弱公子便好,他再怎麼樣,也不會為難你。”
“但為何需要這樣?”江琮忽然發問,“玉扇公子今年已有三十,難道會是夫人的忘年好友?”
泠瑯看了他一眼:“他不是我的好友,是我師父的好友,不好生應付難免會有麻煩。”
呼啦啦一陣風吹來,裹挾著殘余霞,落到并肩而的二人臉上。
江琮深深地凝視,沒有說話。
泠瑯微笑:“怎麼,夫君不曉得我師父是誰嗎?”
江琮輕聲:“夫人那時既然有意識,為何要告知于我?”
泠瑯哼了一聲:“你問得誠心,想說便說了,更何況這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你好幾次見過我使探云三變,難道不是早有所麼?”
語氣坦然,眉目中有滿不在乎的輕傲,說完這句便轉頭向連綿沼澤,眼波顧盼如流水,偶爾停留在絕佳景致之上。
江琮默不作聲地著眼中流轉的,他分不清那是余暉的投,還是原本就有的碎亮。
雙眼十分漂亮,任何人來看,都不會生出不同想法。
像琥珀,但琥珀沒有那麼靈,像晨星,但它亮得太過寂寥,至于溪澗湖水之類,它們清澈純粹太過,了那份難以捉的狡黠。
Advertisement
他不失笑,自己竟然會出神去思考,如何形容一個小娘子的眼睛才算恰當。
而糟糕的是,他竟然想不出。
鄧如鐵在前面嚷嚷:“怎得走這麼慢?村口的騾子都要利索些!”
泠瑯不服道:“我前幾天了傷,走得慢是正常。”
鄧如鐵說:“一年不見,竟能被人弄傷得走不道?我從前就說,了心的刀客連刀都提不穩,你現在知道了!”
江琮低聲音:“原來這句是鄧前輩說的。”
泠瑯憤憤地瞪了他一眼:“金句不問出,怎麼了?”
江琮勾著笑,不再說話。
三人繞過了一個小山頭,鄧如鐵豪邁道:“瑯丫頭,讓你瞧瞧我的雁落山別業!”
泠瑯驚嘆道:“前輩,您本宅都沒有,就有別業啦?”
鄧如鐵兩步繞過某巨大山石,并未回復這句話。
片刻后,泠瑯果真見到了一幢小樓。
小樓高二層,背靠竹林,面朝清池,樓由竹所制,走上去嘎吱嘎吱地響,清風送來竹香,十分有雅趣。
轉了幾圈,真心誠意地贊:“這里真不錯,一定得花上許多銀錢罷?”
鄧如鐵正在收拾白魚,聞言頭也不抬:“一分錢沒花!”
泠瑯早有預料,佯訝道:“此話怎講?”
鄧如鐵自得道:“我去年打這里過,想著進來討碗水喝,結果發現樓里躺著個快要病死的人。”
“然后呢?”
“他讓我替他去尋個郎中來,我說我手頭沒有銀錢,請不。他說找到郎中后自然會替我付,我怕他有詐,這麼爭執幾趟,他急病攻心,竟然就這麼死了——”
“所以您就鳩占鵲巢,登堂室了?”
“什麼鳩不鳩雀不雀的,那人病死在這里,邊一個親朋都無,還是我替他收拾裝殮,辦理后事。如此分,借住個房子,不算過分吧?”
Advertisement
縱使泠瑯知曉鄧如鐵其人有多麼貪財慳吝,聽聞了別業始終,還是忍不住搖頭嘆。
鄧如鐵將魚架在火上,似是才想起來一般:“你們借住的農家?何必去那等地方,不如今晚留在這——”
泠瑯立即說:“不用了。”
鄧如鐵說:“你還怕這個?”
泠瑯向邊的江琮瞥了一眼,嗔道:“我是怕夫君會怕。”
鄧如鐵哦了一聲,擺出一副相看婿般的刻薄態度:“年輕人要多練膽,不然出來行走,事事躲在娘子后,畢竟難看。”
火中,江琮仍是那副溫雅從容之態,他聞言只低頭一笑,面上沒有半赧然。
“讓鄧前輩見笑了,”青年溫聲道,“夫人子強,就算我有心相護,也定要搶在我前。本就習慣事事爭先,怎能由我掩了風?”
鄧如鐵沉:“如今,有你這般覺悟的年輕郎君倒是見。”
江琮微笑道:“一切都聽憑說了算,若歡喜,我便歡喜。”
鄧如鐵說:“這話我可聽見了,阿瑯這孩子命苦,自己了委屈從不愿向他人說明,若今后我聽聞江公子待不好,哼哼——”
他一把展開“玉樹臨風”折扇:“那就休怪咱家拳腳無眼!”
江琮含笑拱手:“在下素來聽聞玉扇公子雅名,如今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同傳說中一般文采高華,氣質卓然。”
鄧如鐵一喜,當即起去窖中拿酒,說今晚定要喝上一點,才不負半路知己。
泠瑯不知道這半路知己從何而來,只覺得,江琮的演技的確已到爐火純青之地步。
什麼若歡喜,我便歡喜,說得那般真摯人,眼神專注得將著,好似真是天上地下絕無僅有的癡郎君一般!
倘若他康健,指不定怎麼在西京城里招蜂引蝶,撥弄眾貴芳心。
泠瑯冷眼看著他們二人飲酒,自己卻一滴沒沾。
直到月出東山,篝火涼,鄧如鐵已經歪倒在竹編涼椅上鼾聲大作了——
江琮才站起,朝出手。
“走罷,夫人。”他于滿天星斗下輕聲,上有著淡淡酒味,卻并不難聞。
泠瑯心中想,鄧如鐵都不省人事了,你還裝模作樣給誰看?難道不能各自走夜路?
但鬼使神差地,著他帶笑的雙眼,還是將手遞了過去。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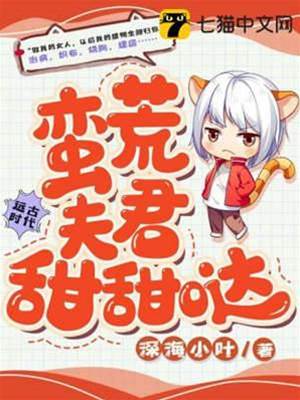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7320 -
連載205 章

食全食美
餐飲大王師雁行穿越了。破屋漏雨,破窗透風,老的老,小的小,全部家產共計18個銅板。咋辦?重操舊業吧!從大祿朝的第一份盒飯開始,到第一百家連鎖客棧,師雁行再次創造了餐飲神話!無心戀愛只想賺錢的事業型直女VS外表粗獷豪放,實則對上喜歡的女人內心…
75.2萬字8 15328 -
完結169 章

系統為我和王爺組cp
一朝穿越,蘇煙每日被系統逼迫攻略戰神謝宴歸。假裝摔倒,假裝柔弱……可是沒想到戰神竟然無動于衷!于是,蘇煙決定以不變應萬變,開啟自己的另外一個任務線路。撕綠茶,虐白蓮,打渣男……那些朝她示好的各路男神是怎麼回事?她明明只想攻略戰神謝宴歸!“王妃,你不是說只愛我一人嗎?”謝宴歸將蘇煙逼迫到角落。蘇煙笑瞇瞇地看著謝宴歸,叮咚,心動值百分之百達成!
32.3萬字8 7099 -
完結266 章
通房有喜
【雙c+1v1+甜寵+多子+非女強+he,友情提示:生子需謹慎,小說只為娛樂】貝慈穿越了。還是個差點餓死街頭的黃毛丫頭,好在將軍府老夫人心善,花二兩紋銀將其買下,不至于讓她穿越即死亡。時間一點點過去,原本的雄心壯志在看透了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本質后,她萎了。從心之下,她乖乖巧巧抱上大腿,一步步爬到安心養老的位置。若干年后,回首身后跟著的一群小崽子,貝慈感嘆,上面有人頂著,下面有人撐著。如此生活,美哉~
46.8萬字8 628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