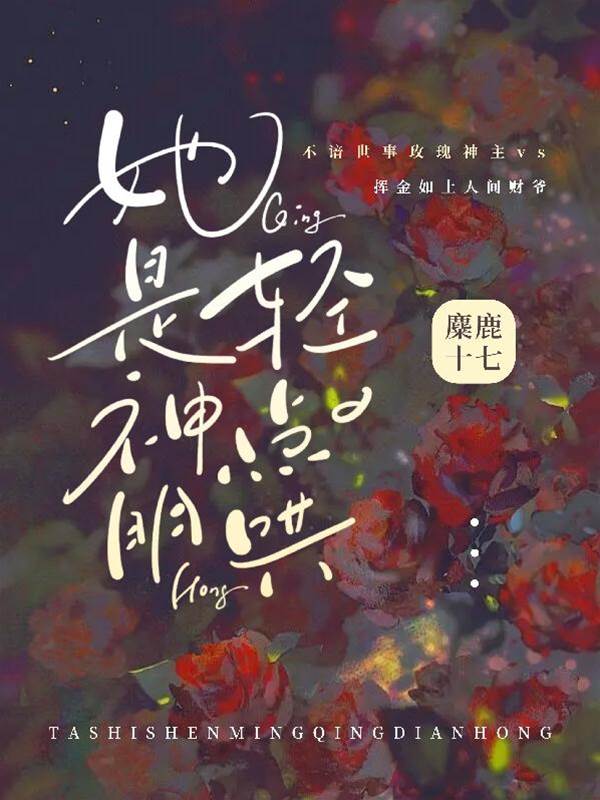《入戲》 第99章 重寫
商銳斂起笑靠在姚緋邊摘下手環斜著看側的字, 果然有個F。字剛正,橫豎規規矩矩,看起來像是商家統一刻印的LOGO, 是姚緋的字。
“你的上面刻的是什麼?”商銳眼眸深沉,著姚緋, 他的嗓音啞然,“給我看看。”
“不給。”姚緋起走到窗戶邊拉上了窗簾,打開餐桌上方的燈, 說道,“給你帶了蛋糕。”
“你的上面不會刻著我的名字吧?”商銳角上揚,黑眸中的笑很深, 嗓音緩慢,“商銳?還是我的英文名?銳哥?男朋友?寶貝?親的?”
“你吃不吃蛋糕?”姚緋臉上很熱, 不想聽他的話。是想在手鐲里刻許愿池里的王八,字太多,的時間不夠, 只刻了個S。
許愿池里的商先生。
“吃。”商銳反復的看那個F, 姚緋是個中規中矩的人,很說話,也不玩很虛的東西。送一塊黃金,刻上的名字, 重中之重了。商銳把手環戴回去,走過去到姚緋對面坐下,看到蛋糕盒上的LOGO。
這家蛋糕非常難買,全國只有一家店在北京。這回不是敷衍他,特意去了趟北京,給他買了一個蛋糕。
做的很多, 說出口的很。
他們是兩個極端的人。
“禮我很喜歡,這家蛋糕我也很喜歡。”商銳坐到對面單人沙發上,傾凝視姚緋,心里有些,那麼好,他恨不得讓全世界知道,他的朋友有多好,“對面的孩我也很喜歡,姚緋,我喜歡你。”
“嗯,對面那個男孩也很招人喜歡,需要蠟燭嗎?”姚緋拿出蠟燭,對上了商銳的眼。商銳的眼又黑又沉,心跳的很快。
Advertisement
“要。”商銳點頭,拿出手機,“我拍一張照片,發朋友圈。”
“可以拍,別發。這家蛋糕只有北京有,我剛從北京飛過來,蛋糕發出去就是宣。如果現在宣,我們必須有個人離開劇組。”
商銳不不愿的點頭。
蛋糕有點走形,路程太漫長了,再小心也不如在店里漂亮。天氣燥熱,油融化了一部分,并不好看。
姚緋拿出七夕蠟燭到了蛋糕上,點燃了蠟燭。商銳圍繞著蠟燭拍了一圈,拍的十分珍重,又錄了視頻。他坐到姚緋邊,攬住姚緋的肩膀俯吹滅蠟燭,轉頭跟姚緋換了一個綿長的吻。
“今天拍戲怎麼樣?”姚緋接過商銳遞來的蛋糕,過一段時間還要減,這個角后期有一段被毒販注新型毒品的戲,需要很瘦,蛋糕這種高熱量的東西,并沒有多大興趣,減太痛苦了。
“不怎麼樣,榮的罵聲響徹整個片場,十分彩。”商銳給自己切了一塊蛋糕,往后仰靠在沙發上,姿態倦懶,他也是真的累,“我演的還不如十二號那天好,一塌糊涂。”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不了戲。”商銳挖了一塊油,停頓了一會兒,說道,“我有顧慮。”
“顧慮什麼?能說嗎?”
“跟你沒什麼不能說,我覺得蔣嘯生很難代,我最近有點迷茫,我偶爾會恐懼。”商銳咽下油,抬眼注視著姚緋,“他是個惡貫滿盈的人,干出了很多泯滅人的事。我代他,我過不了心里那關。”
“你又不是他,你永遠不會做出那些事,你只是短暫的路過他的人生。”姚緋吃了一塊巧克力,明白他的點,演壞人確實需要克服一些心理,“你不是蔣嘯生,他的罪由他來承擔,你是商銳。不管過去還是未來,你都不會做那些事,你有道德底線。出了戲你有很好的家庭,你有很多人在等你,有人——你。”
Advertisement
姚緋又吃了一口蛋糕,把蛋糕放下了,這個角一點都不能胖,非常克制。
“需要看點影片放松下麼?”
商銳緩緩抬眼,“yellow?”
姚緋沉默,這個yellow影片是過不去了麼?
商銳笑了起來,他后仰靠在沙發里,笑的十分燦爛。深邃的桃花眼彎著,稠黑睫覆在眼下。
“再笑你出去。”姚緋臉上有些熱,看了他一眼,“我只會看跟拍攝容有關的影片,一切為了工作,我很敬業。”
“你是很敬業。”商銳點頭,“姚老師業第一敬業。”
姚緋揚眉,不置可否。
“不笑你,這個梗過去了,要看什麼?”商銳斂起了笑,支著下看,姚緋生氣起來也很可。是很文靜的漂亮,以前像水面上的薄冰,此刻是盛放的潔白梔子。
演蔣嘯生力太大了,他每時每刻都于那種仄的抑中。
只有看到姚緋,他才回到人間,到暖意。
“我跟你認真的。”姚緋這邊影片多了,打開電腦找了部很經典的犯罪片,放到桌子上。
“嗯。”商銳的目沉了下去,“我心是抗拒的,你很厭惡蔣嘯生。”
“戲外我不厭惡任何角,角是藝,所有角都值得尊重。你演的越好越會被人尊重,我分得清戲里戲外。不管別人怎麼看待,你不能厭惡,你要厭惡的話絕對演不好。對于角你可以用方式表演,搜集角特點,模仿那些紀錄片里面真正毒梟的模樣,或者經典電影里面的反派。要麼就沉浸式表演,去代他。我不是說讓你真正的代他去干那些壞事,你得找你心最暗的一面放大,用這些緒去填充他的人設。每個人都有暗的緒,這些緒并不可恥。”
Advertisement
商銳停頓許久,拿起了蛋糕慢條斯理的吃。蛋糕很甜,像姚緋。
姚緋斟酌用詞,商銳的心其實比看上去要敏,“之前我跟你的話可能有偏頗,當時我不太想讓你演蔣嘯生,想勸退你。這個角你的切點和我們不一樣,你看到的是蔣嘯生這個人。他的全部,從出生到死亡,完整的一個人。你把他的緒理順就好演多了,蔣嘯生是一個完整的人。無論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所有的壞都有跡可循。”
商銳把最后一塊蛋糕吃完,敞著長靠坐在沙發上,“你為什麼不想讓我演蔣嘯生?”
“不想讓你糊。”姚緋起去拿水,遞給商銳一瓶,看著他,“我希你永遠芒四,站在巔峰。”
同樣的話從姚緋口中說出,是不一樣的滋味。
“商銳。”姚緋關掉了屋子里全部的燈,只余下電腦屏幕的,坐到沙發上轉頭凝視商銳,“你是那麼耀眼。”
“為什麼現在改變主意?”
“不想讓你糊。”姚緋依舊是那個答案。
如果商銳想當個好演員,愿意陪他。
商銳俯而來,攬住姚緋的細腰,他吻的很兇,汲取著全部的空氣。姚緋仰靠在沙發上,圈住了他的脖子。
“姚緋。”
“嗯?”
“我想更近一步。”商銳親著的耳釘,緩緩往下。
姚緋把臉埋在他的脖子上,也不是特別抗拒,在心里想了一會兒,嗯了一聲。
來啊。
“真的?”商銳松開,低頭平視的眼。
姚緋垂下眼,抿了下,“嗯。”
商銳深邃黑眸中浸了笑,他打橫抱起,大步走向了酒店的床。
窗外已經進全然的黑暗,電腦在餐桌上放映著電影,畫面在明暗之間照出方寸的亮。國犯罪片,臺詞大膽直白。背景樂極近驚悚,這部電影姚緋看過很多遍,在心里默念著臺詞,保持著清醒。
Advertisement
人就跌進了的被子里。
姚緋在黑暗中看商銳棱角分明的面部廓,他很英俊。線越暗,就越清晰。的所有被放大,閉上眼。
商銳問想過嗎?想過。
在拍盛夏那場床戲的時候,就想過。會把所有的畫面都想象商銳,那樣,就很容易接。
一直能接商銳。
姚緋忽然想到他們曾經在孤島上看日出,他們在天亮之際開著越野車奔向未知的山頂。你想做什麼我都奉陪,這一刻,我們是自由的。
窗外起了風。
野火在夏日雨夜里燃燒著,洶涌迸發出星火,濺落在的泥土。雨夜的黑暗深不見底,只有火映出一片方寸亮。
夏筍從泥土中探出頭,剝開了層層筍,出細的筍芽。夏天的雨力揮灑,卻仍是澆不熾熱如火的夏。
傾盆暴雨長久的澆灌大地,久不能平息。雨下了半夜,終于在一聲雷鳴中。
閃電劃過,天邊見白,暴雨漸歇。
風撞上了窗戶。
商銳開了燈,倚在床頭拿紙巾細慢的手,他的手指骨節修長。是玩音樂的手,也是最好的盤手。
他一邊一邊笑,笑的桃花眼瀲滟。
姚緋看著他,覺得所有極限運加起來不及他半分。
眼神纏上便是灼熱,姚緋移開眼,不看他了。
商銳俯把姚緋攬到懷里,親汗的額頭,又親的頭頂。把死死的圈在懷里,笑的眉眼飛揚。
只是皮就能讓人上癮沉迷,真刀實槍不得上天了?
難怪人人都要談。
他的眼梢含著霧浸著笑,角上揚看著懷里的人,他的手心覆在姚緋的手背上,兩個手鐲到一起發出很輕的聲音。黃金夫妻手銬,更帶了。他修長的手指穿過姚緋的手指,十指扣,嗓音低啞,“你高興嗎?我今天很高興。”
姚緋靠在他的手臂上了,想了一會兒,撐起攬住他的脖子接了個綿長的吻。
姚緋第二天有打戲,不能過于沉淪。他們都很清醒,寒雨需要很強的專業。
一旦進組,商銳和姚緋就不能再有任何,他們要立刻分開。
商銳需要一部作品來面對質疑和辱罵,姚緋本就把電影當信仰,不會對自己放任。
商銳凌晨時分離開,姚緋醒來時邊已經沒人了。天還沒徹底亮,灰蒙蒙的從窗簾的隙里了進來,屋子里的廓約可見。
姚緋轉把臉埋在枕頭里,似乎聞到了商銳上的香水味。邊的被子是涼的,他應該走了很久。
桌子上的蛋糕不見了,包括點燃過的七夕蠟燭,收拾的干干凈凈。
他帶走了嗎?
姚緋起床晨練,發現隔壁換了其他的演員。
榮讓商銳搬走了。
半個月后商銳和姚緋要在西州拍重要的一場對手戲,他們必須要在這之前把狀態調整到非,各自冷靜是最好的方式。
姚緋這半個月的戲大多是跟鄭則,跟西州這邊的警察演對手戲。
榮擅長折磨人,一場很小的打戲讓姚緋拍了三天。一開始挑緒,后來挑作,直到姚緋完完全全沉浸進角,榮才滿意。
拍完膝蓋都是青的。
和商銳分開一周,沒忍住。周末晚上收工后借著路過的名義,順便看一眼商銳拍戲,商銳今晚有夜戲。
沒有驚任何人,悄悄的進了場,混在場工中看向片場中間。
商銳一漉漉的黑無領襯,頭發也著,拎著一把槍站在燈下。周圍很安靜,劇組所有人各司其職。
“給你十分鐘調整時間。”榮喊道,“你要是還進不去,我們就在這里淋一夜。”
這一場有雨戲,NG一次淋一次。他不知道NG了多次,上服早就了。雖然西州的溫度不低,可一直在淋雨絕不是什麼好的事。
驕矜的小爺沒有罷工也沒有苦累,他很平靜的垂著眼站在原地,在調整緒。
他是真的想演好這場戲。
這是很殘暴的一段殺戲份,蔣嘯生發現手底下重用很久的一個人是臥底,他親手清理門戶。
這段戲商銳做了很長時間的心理建設,他很努力的把自己代到蔣嘯生的緒里。殺伐果斷的大毒梟,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是螻蟻。人命如草芥,他殺人如麻。他在那種環境中長大,他沒有道德也沒有人。
商銳握著槍在原地緩慢的走,每一步都走的十分沉重。著槍的重量,蔣嘯生的緒。
他懂姚緋說的表演方式,他雖然沒把書本上的東西運用到職業里,但他記在腦海里。從盛夏劇組,他就把那些表演課程全部翻了出來,一遍遍的練習,他當時只是不想在姚緋面前丟臉。
他到寒雨劇組后,是真的想演好。他把丟掉的東西全部撿了回來,他做了人設,用姚緋的方式來理解蔣嘯生這個人。
榮為了真實,部分道是真槍。他手里這把就是,九二式手槍,國部分警用槍就是九二式。這把槍是鄭則的警用槍,蔣嘯生故意拿這把槍殺臥底警察,誣陷給鄭則。
他很小就接過槍,知道槍這種東西有多危險。他見過一次子彈打穿膛,很多流出來。他很早前就見過死亡,越是清楚的認識死亡,越是敬畏生命。
榮的劇組場景太真了,他想到腦震回來第一天看姚緋拍戲。
他在姚緋眼里也看到了恐懼。
姚緋害怕死亡,那天的恐懼很真實。他站在榮后看去克服,每一遍都更好,一直到最后一遍。冷靜的殺人,那就是活著站在那里的景白。
商銳環視四周,忽然跟一雙悉的目對上。穿著最普通的T恤牛仔,戴著帽子,融人群不會有人發現,會刻意的改變形態。
劇組很多人戴口罩,姚緋戴口罩也不突兀。
商銳焦躁的心漸漸沉了下去,他有了安全,那種置曠野的覺越來越淡。他看著姚緋,站在那里,一切黯淡無,只有在。
用信任的目看著他,會等他回來。無論他走的多遠,都在那里。
姚緋信任他,傾注了全部的信任。
商銳收回目,看向榮說道,“導演,我準備好了,再來一次。”
他要接住姚緋的信任。
猜你喜歡
-
完結3579 章

韓先生情謀已久
“收留我,讓我做什麼都行!”前世她被繼妹和渣男陷害入獄,出獄後留給她的隻剩親生母親的墓碑。看著渣男賤女和親爹後媽一家團圓,她一把大火與渣男和繼妹同歸於盡。再醒來,重新回到被陷害的那天,她果斷跳窗爬到隔壁,抱緊隔壁男人的大長腿。卻沒想到,大長腿的主人竟是上一世那讓她遙不可及的絕色男神。這一次,她一定擦亮眼睛,讓 韓先生情謀已久,恍若晨曦,
354.7萬字8 51935 -
完結397 章

豪門二嫁:只偏愛她
她是見不得光的小三的女兒。也是一個二嫁的女人。聲名狼藉的她卻在全城人的目光中嫁給了風頭正盛的沈家大少。豪門世家,恩怨糾葛。再嫁的身份,如何讓她在夾縫中努力生存。而他沈彥遲終是她的良人嗎?
85.6萬字8 8906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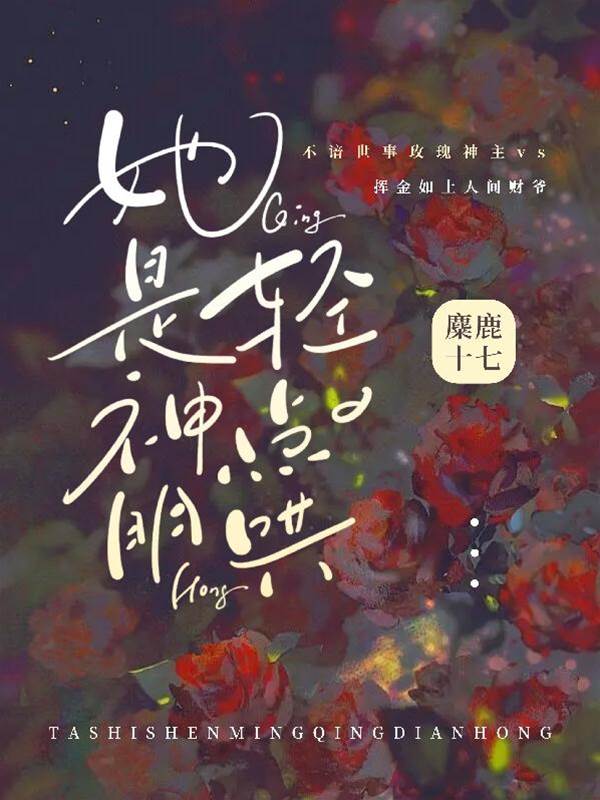
她是神明輕點哄
[不諳世事玫瑰神主VS揮金如土人間財爺][先婚後愛 雙潔+情有獨鍾+高甜]“她牽掛萬物,而我隻牽掛她。”——柏聿“愛眾生,卻隻鍾情一人。”——雲窈雲窈有個好的生辰八字,擋災的本事一流。不僅讓她被靈蕪城的豪門喬家收留,還被遠在異國,家財萬貫的柏老爺給選中做了柏家大少爺柏聿的未婚妻。—雲窈喜歡亮晶晶的寶石和鑽戒,豪門貴胄笑話她沒見過世麵,柏總頓時大手一揮,寶石鑽戒一車一車地往家裏送。—雲窈有了寶石,想找個合適的房子專門存放,不靠譜的房產中介找上門,柏太太當機立斷,出天價買下了一棟爛尾樓。助理:“柏總,太太花了十幾億買了一棟爛尾樓。”男人麵不改色,“嗯,也該讓她買個教訓了。”過了一段時間後,新項目投資,就在那片爛尾樓。柏聿:“……”—柏聿的失眠癥是在雲窈來了之後才慢慢好轉的,女人身上有與生俱來的玫瑰香,他習慣懷裏有她的味道。雲窈卻不樂意了,生長在雪峰上的玫瑰神主嫌棄男人的懷抱太熱。某天清晨,柏太太忍無可忍,變成玫瑰花瓣飄到了花盆裏,瞬間長成了一朵顏色嬌豔的紅玫瑰。殊不知,在她離開他懷抱的那一瞬就已經醒過來的男人將這一切盡收眼底…他的玫瑰,真的成精了。
23.9萬字8 71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