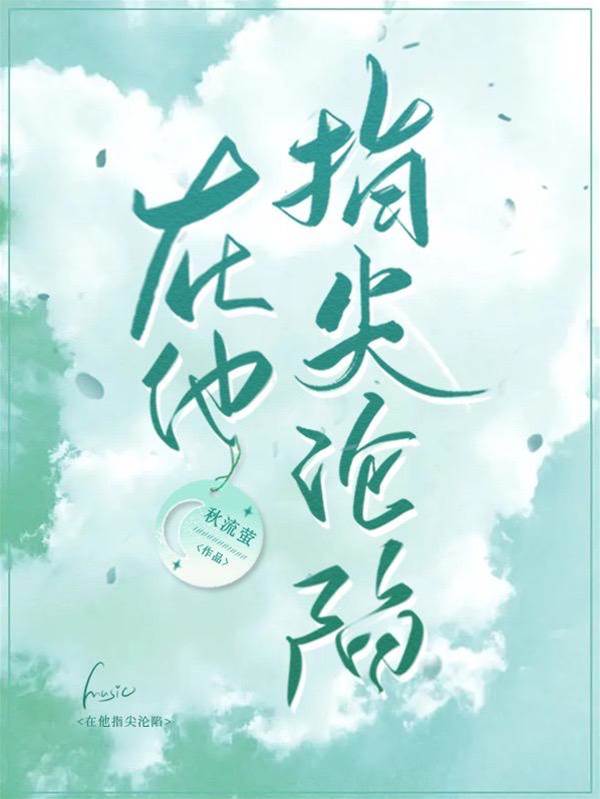《反派同窗他命帶錦鯉》 第35章
傅子獻道, “無事,只要你向書院說明你昨日在李夫子那里,就不會有人懷疑你了。”
聞硯桐沉片刻,而后道, “呆會兒到了那邊你別說話, 不要牽扯進來。”
傅子獻只以為要親自解釋,便答應了。
兩人一路趕到窩附近,老遠就看見那周圍聚著一大批人, 里里外外的將窩給圈住。
其中除了學生之外, 還有幾個夫子。有人眼尖,看見聞硯桐來,當即便道,“罪魁禍首來了!”
這一聲便將眾人的注意力拉到聞硯桐上, 所有人一同看來,開始低聲議論, 懷疑的目在上打轉。
聞硯桐皮笑不笑,“這話不對吧?我這才剛來, 怎麼就罪魁禍首了?”
走到人群里, 眾人自往后避讓, 好似不大像跟接。這倒給讓出一條道路來,讓得以走到窩邊上。
就見無惰的尸扔在窩邊,兩只爪子翹得老高,上沾了很多,經過了大半夜早已凍得邦邦的。
頭連著脖子整被斬斷, 隨意的撂在旁邊。
狗東西,你終于歸西了。聞硯桐心中長嘆。
看這模樣,似乎也是某個夠了這只的荼毒,忍耐到了極點才殺了泄憤的。
“聞硯桐,有人說昨夜只看見你在這附近轉,你還說不是你殺的?”有人站出來質問。
聞硯桐起眼皮看他一眼,“我起夜,不可以?”
“就算是起夜,時間哪會這麼趕巧?”那人道,“你分明就是狡辯?”
聞硯桐翻一個白眼,沒有搭理他,覺得跟一個完全不臉的人爭吵就是浪費口舌。走到的旁邊,蹲下細看,卻發現這只的眼睛是閉著的。
的半個子都泡在了中,早已凝結,呈一片暗。的目在周圍轉了一圈,只看見了紛的腳印和晨霜。
Advertisement
“他不說話了,就是心虛。”
“肯定是他,前些日子他就想殺這只,現在看來是死不改。”
“這可是院長的啊,他竟然敢下手……”
這只不僅有名字,而且還有一個在窩中算是豪宅的住房,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這只是院長親自帶來的。還有一個,則是無惰每日早上六點半準時打鳴,有時候準確到跟朝歌的晨鐘同時響起。
這才是無惰珍貴的緣由。這只在書院的地位不低,側面代表了莘莘學子的勤自檢。把殺了,要背負的罪名可不止一個兩個,所以傅子獻才說是一件大事。
大到足以將殺之人逐出頌海書院,甚至獄。
周圍的人議論紛紛,指責此起彼伏,聲音越來越大,好似想給聞硯桐施加力,著認罪一般。
傅子獻在一旁聽得拳頭握,想站出來為聞硯桐說公道話,卻想起自己答應過不在這說話,不卷這件事,只好強忍下出頭的念頭。
聞硯桐仿佛充耳不聞,低頭細細的查看。
隨后又有人趕來,眾人又跟著看去,就見幾位夫子腳步匆匆而來,其中就有趙夫子。
后來的這幾位夫子都是書院中有些威的,趙夫子算是其中分量最小的了。趙夫子本名趙鈺,金榜狀元出,居六品在朝中干了大半輩子,后來自請來書院教書。
他一見聞硯桐站在無惰的尸旁,就立馬幾個大步上前,將從地上拽起,低聲問,“你又在干什麼?”
“夫子,我正研究這怎麼死的呢。”聞硯桐說道。
趙鈺將往后推了兩步,“你先往后站站。”
那幾個夫子中,有個孫逑的,乃是前任禮部尚書,卸任后被皇帝指來管理書院,在書院有絕對話語權。他往那一站,周遭的學生自退開。
Advertisement
他看了地上的一眼,沉聲道,“這是誰做的?”
馬上就有人站出來告狀,“是聞硯桐,他昨夜殺了。”
聞硯桐立即反駁,“不是我殺的!大家都是文人,說話要講究證據的,你憑什麼空口誣賴?”
孫逑轉頭看向,那雙眼睛沉淀了朝廷的勾心斗角,爾虞我詐,是這樣掃一眼,就令人心頭一沉,不自覺到迫。
“你就是聞硯桐?”孫逑問。
聞硯桐作揖,“正是學生。”
“你倒是出名。”孫逑的語氣平穩,聽不出是嘲諷還是調侃,聞硯桐不敢隨意接話。
周遭一群人死死的盯著看熱鬧,大氣不敢出一個。
正是安靜時,牧楊卻不知從何時躥出來,愣著頭問道,“哪兒呢哪兒呢?死哪兒去了?”
他撥開人群,一眼就看見地上的尸,咧一樂,“喲,這死法可真不一般啊!”
四周一片死寂,唯獨牧楊樂呵呵的聲音極其突兀,偏偏還沒人敢說什麼。聞硯桐朝他使了個眼神,讓他趕快閉別樂了。
牧楊卻沒看懂,上來拍了拍的肩膀,“是你殺的嗎?你這手法可以啊!”
聞硯桐眼睛一瞪,“你說啥呢!”
“哎呀開個玩笑。”牧楊笑道,“我自然知道不是你殺的。”
他的目朝周圍轉一圈,笑容中忽然浮上冷意,說道,“不會真有傻子懷疑是你殺的吧?”
聞硯桐松一口氣,聽出來牧楊這是在為出頭,不由心中一暖。雖然牧楊憨的一批,但有有義的人設倒是還在。
“牧楊。”孫逑出聲制止。
牧楊看見他,倒沒多害怕,笑著行禮,“方才沒看見孫夫子,是學生失禮。”
孫逑也沒有追究,只板著一張臉,問先前狀告聞硯桐的那人,“你說是聞硯桐所為,可有依據?”
Advertisement
那人有些忌憚牧楊,幾次朝他看了看,言又止。孫逑看出來,便道,“說,一切有我做主。”
“是、是昨夜守夜的下人說看見聞硯桐后半夜在此地躥,那時候大家都在睡覺,只有他一人……”
孫逑問道,“昨日守夜的下人是誰?”
人群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男子站出來,說道,“昨夜是小人守后半夜的班。”
“他說的都實屬?”孫逑問那守夜下人。
下人道,“確有此事。”
眾人又低低的議論起來。孫逑便看向聞硯桐,“你對此有什麼想說的?”
聞硯桐道,“我想問他幾個問題。”
孫逑道,“你問。”
便對那下人道,“你昨夜什麼時候看見我的?”
“丑時末刻,將近寅時。”下人回答。
“黑燈瞎火,你確定你看見的人是我?”又問。
“我看得真切,書院中只有你一人腳不便。”下人便道,“著面白氅,提著黃燈籠。”
聞硯桐點頭,“是我不錯。”
話音一落,便有人急著跳出來,“果然是你!”
聞硯桐瞅他一眼,“著什麼急,我還沒問完。”
繼續道,“你為什麼會這那個時間看見我?你平日在這一片守夜?”
“并非,小人那時正好來接替守夜,便在這附近的茅房如廁,剛出來就看見了你。”下人答。
“最后一個問題。”聞硯桐道,“你說你看見我在這附近躥,當真如此?”
下人前幾個問題答的流暢,但最后一個問題時卻像卡住一般。聞硯桐趁著他沉默的時候突然厲聲道,“書院夫子皆在,你若敢說謊作偽證,仔細你的小命!”
下人子一僵,“并不,我只是看見你提著燈籠從那邊走過去,躥什麼的都是那些學生擅自加的。”
Advertisement
聞硯桐滿意的點頭,對孫逑道,“孫夫子,我問完了。”
“那你現在有什麼想說的?”孫逑問。
聞硯桐道,“學生慚愧,昨夜我因為字太丑在李夫子那練字,一直到丑時才回來,是以那人看見我的時候,正是我趕回寢房,并未來到這片地方,也沒有過這只。”
“剩下的時間,我都在房中睡覺,一直到今早被人醒,來到這里就莫名被潑上了殺的臟水。”聞硯桐道,“學生著實冤枉。”
“不可能!李夫子怎麼會留人那麼長時間?”有人質疑。
“此事我不敢撒謊,若是不信,可詢問李夫子。”聞硯桐坦坦。
“難怪禧哥今日沒來上課。”牧楊了然道,“原來是昨兒回去太晚了。”
“不錯,昨日小侯爺也在,若是你們不信,也可以找小侯爺核實。”聞硯桐說這話的時候甚至有一些小得意。
這盆臟水潑得簡直太是時候。
若是擱在平常任何一個夜晚,聞硯桐自個在寢房中睡覺,本找不出足以擺嫌疑的證據。但是恰恰就在去練字的這一晚,如此一來,李博遠和池京禧都可以為的證人。
且是沒人敢質疑的證人。
把池京禧一搬出來,就不敢有人再爭辯前半夜的事了。于是又有人道,“或許你后半夜行兇。”
聞硯桐嗤笑一聲,看個傻子似的看著那人,“你是想誣陷我想瘋了吧?這后半夜有人守夜,我一個瘸子,如何在黑夜大搖大擺過來殺?”
“那若是你提著燈籠來的呢?”又有人追問。
聞硯桐這回都不屑回答了。那守夜的下人道,“小人在此守夜,方圓之若是有燈出現,小人必定會發現。”
“聽清楚了嗎?”聞硯桐看著那人問道,“還有什麼理由?”
已將眾人的質疑一一解答,若是還有人不相信,則應該去尋李博遠或者是池京禧核實,無論如何也沒有理由一個勁的認定殺的人是了。
孫逑看了看眾人,說道,“無惰乃是書院莘莘學子勤學的象征,如今它被人惡意殺死,實乃一樁令人不恥的罪事,即日起書院下人早晚兩次點卯,不得有一人離開,我等定要徹查此事。”
聞硯桐驚訝,沒想到書院竟真的因為一只大費周章,暗自慶幸當初那一刀沒能剁下去。
孫逑下完令之后就離開了,夫子們相繼離開。趙鈺似乎想對聞硯桐說些什麼,但思及那麼多人在場,還是先離開。
學生一哄而散,沒了看熱鬧的興致。聞硯桐見先前不斷質疑的人要走,便出聲喊道,“你站住!”
那學生本不想搭理,卻見牧楊兩三步上前將人按住,“想上哪去啊?方才你皮子溜啊,讓我看看你這一排牙長得如何。”
說著就要去掰扯人家的。
牧楊跟池京禧玩得時間長了,脾氣也有幾分相似,擱這一杵,上的氣就出來了。那人嚇得不敢彈,連連求饒,“牧爺饒了我吧,我不過也是人所托……”
聞硯桐走上前去,站在那人的對面。只可惜矮了一頭,完全沒有氣勢。
道,“我知道,是吳玉田吧?肯定是他指使一個勁的誣賴我。”
那人瞬間就把吳玉田賣了,“是是是,吳玉田早就記恨你,聽說了今早的事之后,就指使我多誣賴你兩句,這并非是我本意……”
“你不必跟我狡辯那麼多,我也不想聽。”聞硯桐說道,“你回去告訴吳玉田,我已經知道殺的人是誰了,讓他走夜路的時候小心點。”
那人現在是刀架在脖子上,自然說什麼話都應著,忙不迭的點頭。
聞硯桐舉起一個握的拳頭,“你看看我手心里有什麼東西。”
那人不明所以,低頭湊到拳頭便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往里看。
聞硯桐另一只手揚起,掄一個大圓,掄足了力氣,一掌打在那人的側臉,罵道,“吃我一個大脖溜子!讓你他娘的空口造謠。”
聞硯桐的掌其實沒有那麼重,但是特別響亮,一下子把那人給打蒙圈了。
就連傅子獻和牧楊也嚇了一跳。
“哼。”聞硯桐心道,惹不起吳玉田一個七品小,我還能惹不起你?
猜你喜歡
-
完結324 章

軍閥權寵:大帥,你過來!
民國年,烽火亂相生,軍帥各領占地為王。 蘇城被攻陷那日,喬綰像個貨物,被獻給西北三省的新主人。 傳聞中,季九爺冷血陰狠,克死三房夫人,是天煞孤星。 季世延自垂花門下溜達出來,自墨鏡余光里撩了一眼.... 春光明媚,少女眉目如畫,身段娉婷,像朵飄零無依的菟絲花。 季九爺舌尖頂了頂腮,招寵般抬了抬手,矜貴優雅。 多年后,喬綰站在垂花門下,沖著院子里跪了一個正午的挺拔身影,嬌慵喚道,“大帥,你過來。”
60.2萬字8 2645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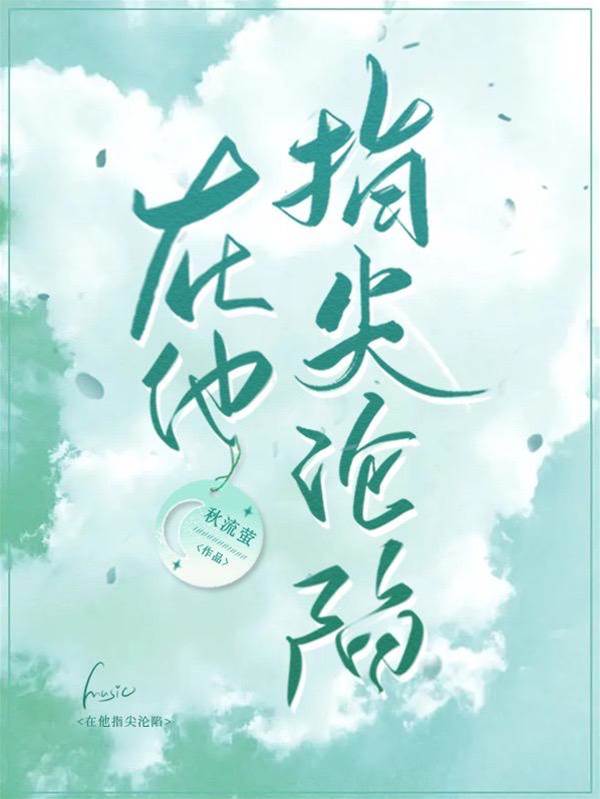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 20496 -
完結222 章

許愿
虞粒喜歡程宗遖,從14歲開始。 那天,他在舞臺上彈奏貝斯,張揚肆意。只是驚鴻一瞥,她再也沒能忘卻。 幾年後重逢,他已成爲商場大亨。西裝革履,氣質矜貴凜然。 她終於按耐不住心中愛慕,鼓起勇氣上前搭訕:“程叔叔,你這個年紀的人,應該不用微信吧?” 他饒有趣味看她兩眼,將手機遞給她:“加上看看不就知道了?” 18歲生日那晚,她從家裏跑出來,失魂落魄地撥打他的電話:“程叔叔,我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他聞訊而來,揉揉她腦袋,憐惜中透着蠱惑:“跟我走嗎?”
33.7萬字8 3961 -
完結199 章

瀝青
文徵剛住宋家那年,宋南津去美國長居。人爸媽在國外開企業,文徵被他姑母收留,兩人沒什麼交集。 後來宋南津回國,兩人被迫共居一室。 文徵知他不好相處,不敢招惹,處處小心。 可後來才知道,其實宋南津心裏想她想很久了。 男人慢條斯理繫着袖釦,聲音溫柔又淡薄:“文徵討厭我,爲什麼勾引我。” - 在宋南津面前,文徵向來處於一個弱勢地位。 他是她在宋家的哥哥,文徵從不敢隨便僭越。 轉變皆來自那天。 所有人眼裏井水不犯河水的二人依舊安然做自己的事,天際暗淡,文徵無意和宋南津在逼仄過道相遇。 客廳傳來家裏其他人的講話聲。 文徵從他身旁經過,手指卻悄然被他勾住:“這次準備和他談多久?該分了,文徵。” 和男友分手的夜,他們最後攤牌,宋南津說要結婚,文徵冷靜表示自己不太能無縫接軌。 男人指間掐煙,口吻淡然。 “我要你,你覺得自己還有選擇嗎。” - 文徵貧瘠的世界觀裏,隨遇而安是她的生存法則。 而宋南津是衆星拱月的目光焦點,資本子弟。 他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可那些她孤獨又沉默的歲月。 他也想成爲她的全世界,爲她依託。
33.1萬字8.25 61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