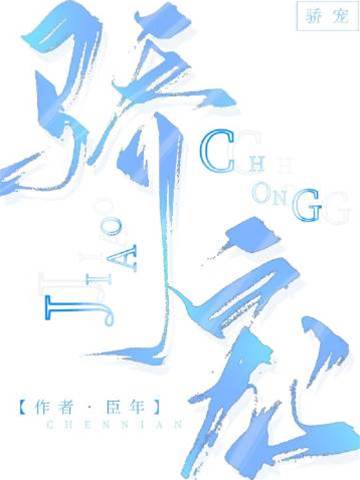《不斷作死后我成了白月光》 第34章
然后他把視線挪開,看向另一邊的桌面:“嗯。”
“如果只是石灰加水,不管是誰都會被燙到吧。”
賀知洲了下,若有所思:“但陳搖卻表現得輕輕松松,這豈不就證明他在刻意騙人?”
“陳府里的怪事,主要有三個疑點。”
寧寧完了藥,習慣地往裴寂手中吹了口冷氣,惹得后者耳一熱,渾僵地把手臂回。
承影恨鐵不鋼:“你還行不行了裴寂?就吹一口氣而已,至于這麼大反應嗎?”
裴寂不想理它,面不改地在心里回了句:“至于。”
“第一個疑點,之所以會傳出‘夫人是妖’的流言,是一名家仆深夜前往井邊,親眼目睹了將畫皮放井中清洗。”
寧寧道:“但這未免也太過巧合了吧?先不說兩人為何會那樣巧地剛好遇到,畫魅作為一個深思慮想要取代原的妖,當真會犯下‘大搖大擺去井邊褪下畫皮,還被旁人無意窺見’這麼低級的錯誤嗎?”
“對哦。”
鄭薇綺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如果我是畫魅,一定不會采用那麼危險的法子。清洗畫皮還不簡單?等陳搖出門后打一盆水,自己在房中就能解決。”
“不錯。如果我們換個思路,將之前的推測一并舍棄,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
寧寧頓了頓,杏眼中漾起一抹亮:“要是畫魅被那家仆發現并非偶然,而是有意為之呢?”
這回到賀知洲坐不住了:“有意而為之?圖啥啊?生怕別人不知道是個妖怪?”
哪知寧寧竟瞇眼笑了笑:“如果你口中的這個‘’是指夫人,那就的確如此。”
……想要讓別人知道,夫人是個妖怪?
Advertisement
“你是說,”他怔了怔,“有人想要嫁禍?”
“假設家仆所言不虛,那宅子里必然棲息著一名妖魔。至于那妖究竟是誰,就要說到第二個疑點。”
寧寧說著一眼裴寂,沒想到對方也在淡淡看著,于是勾笑笑,繼續說:“據裴寂的說法,畫魅披的畫皮是按照原一筆一劃描繪而出。如果夫人并未被替換,那畫魅究竟是以怎樣的份與接,才能對的模樣爛于心,將畫得那麼惟妙惟肖呢?”
“不、不會吧。”
賀知洲終于出了震驚的神:“你是說……枕邊人?”
——那豈不就是陳搖了嗎?!
“第三個疑點。”
寧寧比了個“三”的手勢,言談間不不慢:“雖然我們與陳搖本人接甚,但從他妹妹陳白的話里,還是能找到許多不對勁的地方。”
從寧寧開始出聲說話起,陳白的臉就一直慘白一片。此時雙上下抖個不停,聽見自己的名字,更是下意識往后瑟了一步。
“對啊!有件事我納悶了很久。陳姑娘說過,兄長雖然極嫂嫂,出了這檔子事后,卻一直拒絕開壇做法,甚至杜絕了外人與趙云落的全部接。”
鄭薇綺沒做多想,口而出:“他難道就一點也不擔心,如今的趙云落當真是妖,而真正的夫人危在旦夕嗎?”
“沒錯!”
賀知洲附和著點頭:“如果喜歡一個人,就算無條件信任,可一旦得知很可能危險境地,還是會想方設法地把一切調查清楚。”
兩個名副其實的單狗,在談論與不的問題上,倒是思維敏捷、穩如老狗。
“正因為他心里有鬼,所以才帶著夫人閉門不出。為什麼謝絕家人探,更不愿意讓修道之人進屋調查?”
Advertisement
寧寧抿笑笑:“表面上看起來,是不想讓夫人的靜養到侵擾。可一旦掀開這層遮布,要是被誰不經意間發現,原來有問題的是他而非趙云落,那一切可就全完了。”
說著頓了頓,喝了口桌上的龍井茶:“線索還不止這些。記得陳姑娘說過的一句話嗎?‘爹爹趁兄長不在家時,特意請來道長開壇做法,卻并未發現府里有妖魔的行跡’。”
這絕對是最有分量的石錘,簡直是一句再明顯不過的提示。
既然家中確有妖,而道長卻并未察覺任何蛛馬跡——
賀知洲心頭一驚:“正因為他不在……所以才沒能找到妖魔行蹤!”
鄭薇綺面微沉:“還有之前賀師兄向夫人問話,問到‘近日邊可有蹊蹺之事’,陳搖便火急火燎打斷了對話。或許……正是因為害怕夫人提及他最近的異常,從而暴份。”
“也就是說,被畫魅取代的并非趙云落,而是陳府里的大爺陳搖。”
寧寧一眼陳白頹敗的臉,口中繼續道:“畫魅為禍一方,往往害得原家破人亡。他先是幻化陳搖的模樣,再繪制出一張與夫人一模一樣的面皮,把嫌疑盡數嫁禍給。到時候趙云落百口莫辯,與陳老爺陳姑娘一同被它汲取氣、疲力竭而死……”
“到那時候陳家獨剩他一人,哪里還有誰能分辨出來,他本不是真正的大爺陳搖?”
話音緩緩落地,在場所有人皆是后背一涼。
煞費苦心想要找尋的妖竟一直都潛藏在邊,眾人不久前還與它有過近距離的談。
而對于病榻上的趙云落而言,恩有加的枕邊人居然心懷不軌,看似對百般呵護,實則每一步棋,都是在把往死路上。
Advertisement
一想到近在咫尺的單薄皮之下,竟然藏著那樣一副心機深沉、殺氣騰騰的骨架,就讓人難以抑制地頭皮發麻。
“我本來只是懷疑,沒有確切證據。于是趁著賀知洲吸引了陳搖注意力的時間,從儲袋里拿出石灰與水混合,并編造了所謂‘化妖水’的謊言。”
寧寧又喝了口水:“陳搖為畫魅,必然不可能讓我把化妖水用在趙云落上——畢竟一旦證明并非妖,矛頭就會轉向府里的其他人,對于他來說大為不利。”
“所以你猜中他會故意摔破瓶子!你他娘——”
鄭薇綺把接下來的話吞回肚子里,斟酌一番詞句:“你真是個人才啊,師妹!如果他心里沒鬼,被灼燒后一定會立刻說出來,但要是有事瞞著我們,就會刻意表現得若無其事!”
寧寧點頭:“他以為自己憑借演技躲過一劫,其實是親自踏進了陷阱里。為了讓陳搖相信那些水的確不會對凡人造損害,我本來打算把瓶子撿起來,沒想到裴寂他……”
說著頓了頓,有些哭笑不得:“謝謝啊。疼的吧?”
“小師弟居然看懂了寧寧的意圖麼?”
鄭薇綺“哇”了一聲:“這都能想到一起,你們還有緣的嘛。”
承影嘚瑟得不行:“繼續夸繼續夸,我聽。”
“不過畫魅的這一招也太損了吧!”
賀知洲很是憤憤不平:“害得好端端的一家人相互猜忌、彼此憎惡,他卻一直假惺惺地扮演害者角。要是不被揭,說不定哪天陳府被害得家破人亡,旁人還會覺得他是最可憐的那個。”
“這種食人骨的魑魅魍魎,鮮有良知存在的時候。”
鄭薇綺說著勾笑笑,揚高了聲調:“你說是不是啊?陳公子。在門外聽這麼久,是時候進來休息休息了吧?”
Advertisement
陳白臉上的震驚之仍未褪去,聞言迅速抬頭,向門邊去。
木門被鄭薇綺催靈力轟然推開,站在門外的陳搖面鐵青、雙目紅,哪里還有半分儒雅隨和的氣質。
“看破又如何。”
陳搖冷聲笑笑,里竟發出骨骼時的干聲響。那張披著的面皮如同被水浸泡的紙張,開始出現一條條上下起伏的褶皺,褶皺越來越長、越來越多,最終居然整個落下來,出被畫皮層層包裹的骨骼。
而他的聲音亦是變得非男非,雌雄莫辨,比起人聲,更像是金銀鐵相互撞發出的刺耳雜音:“一群鼠輩!既然見了我的真,那就別想離開!”
[沒想到畫魅竟然直接亮出原型,眾人皆是大駭!
那妖魔神態兇惡、殺氣盡,狠戾如煉獄修羅。在場幾人的腦海中不約而同劃過同一個念頭:若是不能戰勝他,今日必定死無葬之——]
最后那個“地”字還沒念完,旁白就又又又一次陷了尷尬的死機狀態。
它真的好氣。
你們這群人能不能讓它順順利利把臺詞念完一遍?!
——只見原本端坐在桌前的黑年突然起,拔劍抬手之際,冷冽寒刺破濛濛雨。
裴寂速度很快,比起癡癡狂笑的畫魅,周凜冽的侵略要顯得更加濃郁。
長劍出鞘,直指門外妖魔命門,帶起凌厲如刀刃的縷縷劍風。畫魅萬萬沒想到這人的殺意比自己還恐怖,一時間變了臉,由于來不及躲閃,只能倉皇向側邊閃躲。
而裴寂似乎早就料到了他的作,出另一只手狠狠扼住骷髏咽,將其不由分說地按在走廊旁的長柱上。
畫魅好懵。
明明按照陳白的說法,這群人不過是小門小派出,看一眼就能知道沒什麼能耐,不過下山混口飯吃。
可現在是個什麼況。
他是誰,他在哪兒,他要怎麼辦。
“說。”
裴寂的眉宇之間浸了殺意與冷,聲音同樣冰涼,宛如真正的反派大boss,只要稍有不順心,便會一劍取他首級:“真正的陳搖在哪里。”
旁白沉默了很久。
仿佛是為了挽回自己所剩不多的面,那道悉的男音再度響起。
[沒想到裴寂竟然直接拔劍而起,畫魅心中大駭!
眼看那劍修神態兇惡、殺氣盡,狠戾如煉獄修羅。畫魅腦海中忍不住劃過一個念頭:若是不能讓他滿意,今日必定死無葬之地!]
猜你喜歡
-
完結63 章

我和大佬離婚后
一句話介紹:離婚一時爽,追妻火葬場。 一朝穿書, 顧北音多了一個人人艷羨的大佬老公。 大佬英俊優雅、溫潤紳士、潔身自好,個人魅力正無窮,完美滿足了她對男神的終極幻想。 只除了, 兩人是商業聯姻,毫無感情、相敬如冰。 被漠然以對一個月后,她直接將離婚協議拍在了大佬辦公桌上。 簽字離婚時,秦清越內心毫無波瀾,甚至有種解脫感。 直到一年后—— 盯著頒獎典禮上對顧北音大獻殷勤的男人, 他無意識捏斷了手中的筆。 食用指南: 蘇爽文,涉及娛樂圈,男主前期冷淡,后期會被狠狠打臉,喜歡男二的寶寶一定要慎重;
16.6萬字8.18 17800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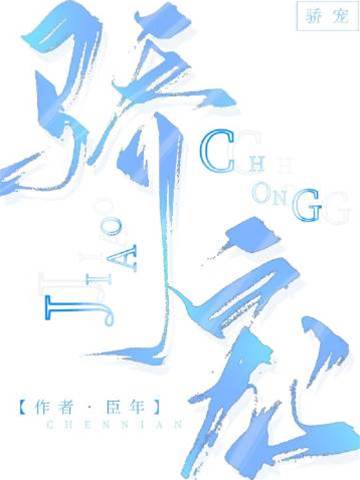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3923 -
完結123 章

偏吻荊棘
段西珩17歲時,曾在阮家借住。 阮蘇茉見他的第一眼,少女心思便如野草瘋長。 可惜少年寄人籬下,清冷寡言,不大愛理人。 阮蘇茉總鬧他,欺負他,來惹他注意,像鞋帶散了這樣的小事,都要喊他。 而每每這種時候,身着校服高挺如松柏的少年,總會一言不發,彎身蹲下,替嬌縱的女孩系上鞋帶。 他很聽話,卻好像不怎麽喜歡她。 阮蘇茉的暗戀随着段西珩畢業出國戛然而止。 沒想到幾年後再見,是被長輩安排結婚。 少年已經長大成人,西服熨帖,斯文清貴。面對她時,仍如從前般沉默。 婚後,阮蘇茉與段西珩的關系屬于白天冷淡偶爾夜晚熱烈,感情一直不溫不火,直到她高中沒送出去的情書被段西珩看到。 阮蘇茉本以為他會奚落嘲笑自己一番,高高在上的她也曾有過卑微的暗戀。 卻沒想到,他只是沉默地将沒拆開的信封還給她,什麽都沒說。 而那個夜晚,段西珩第一次埋首在她肩窩,呼吸不定: “幸好他瞎。” 阮蘇茉:? 你為什麽罵自己?
17.6萬字8.18 48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