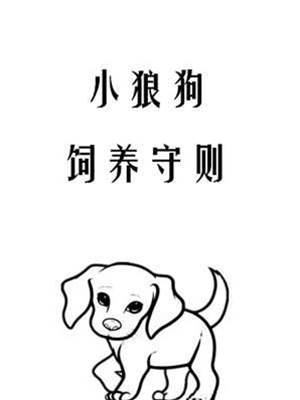《不斷作死后我成了白月光》 第51章
等那陣灼熱的火風漸漸消散, 裴寂才收斂了劍氣, 與寧寧再度拉開一段距離。
殘余的熱度被散在空氣里, 好似滯留在沙灘之上的余, 悄悄浸潤進每一粒沙礫間微不可見的隙, 讓里的所有都為之一窒。
寧寧低聲音:“當心, 里有靜。”
正如所言,在一片人提心吊膽的沉默里,自深傳來一陣極其微弱的窸窣聲響。
火凰所居的山深邃幽寂, 四周盡是凌堆砌的嶙峋石塊。那聲音順著甬道而來, 起初只是類似于低低的鳴啼, 和山巔之上涌的風一起劃過耳, 到后來越發尖銳響亮,幾乎震得邊石塊齊齊。
天邊澄亮的線點綴于口,依靠著這道,巖壁之上緩緩出現一抹濃郁的漆黑影子。
“是火凰!”
喬驚道:“它定是察覺到了生人氣息……諸位當心!”
寧寧死死盯著口,下意識握住星痕劍劍柄。
他們之前在小重山里遇見過玄鳥,并與之有過一番接, 總經過勉強算是有驚無險——除開事發之后賀知洲被天羨子狠狠揍了一頓,了個重癥傷殘。
然而此地的火凰卻與玄鳥一族截然不同,屬于未開靈智的惡, 只懂得一味搶奪與殺戮,否則也不會把西山禍害這副模樣,并在大戰之中趁喬父親死,搶去狐族世代相傳的玉佩, 以供自修煉。
隨著一道鋒利如刀刃的尖嘯刺破熱浪,那道影子終于從之中現而出。
火凰通赤紅、態優,長足足有十多尺高,巨大的雙翼在離開后倏地張開,任由滿羽勾勒出流水般的線條,每一片羽翼之下都蘊藏著勢不可擋的力量。
Advertisement
最先吸引了寧寧全部注意的,是它一雙鷙渾濁的眼瞳。
它的瞳孔亦是暗沉的紅,比起火焰,更像是浸了層層跡,滿是抑與癲狂的緒,讓人只需看上一眼,就下意識后背發涼。
這是猛掠奪食時的眼神,不帶任何理智,只剩下最為純粹的。
火凰的脾氣不比玄鳥小,還沒把在場的所有人通通掃視一遍,剛打了照面,便從嚨深猛地發出一道嘶吼——
洶涌烈焰聚火球,借由山頂的獵獵風勢,如利劍出鞘般徑直向眾人襲去!
火凰之焰并非凡俗之,不但來勢洶洶,還裹挾著大量靈。
寧寧是頭一回與它有正面鋒,若是熱上涌、稀里糊涂地拔劍去擋,很有可能當場加燒烤豪華晚餐。斟酌一瞬后,還是決定輕盈后躍,先看看它的實力究竟如何。
疾風攜著火浪,頗有種將西山焚燒殆盡的氣勢,鋪天蓋地地席卷而來。
山頂的碎石到這風浪侵襲,竟被狂風呼嘯著卷上半空,有如萬箭齊發般向眾人落去。
賀知洲傻了那麼久,總算當了一回人,當即調全靈力,以劍氣護,在自己與柳螢邊架起護盾,帶著藏至一塊碩大的磐石之后。
“多謝……多謝賀哥哥。”
柳螢說得吃力,本就白皙的臉頰此時失了,與單薄紙張沒什麼兩樣。
賀知洲見發抖、直冒冷汗,立馬就明白事不妙,順著柳姑娘低垂的視線看去,見到了鮮淋漓的肩膀。
——那場疾風來得猝不及防,在他還沒來得及展開劍氣的時候,一塊尖利的錐形石片便徑直刺了柳螢的右肩。
修臉蒼白,看著賀知洲倉皇的模樣,在心底暗自冷哼。
Advertisement
把《西宮》和《草百骨》這倆話本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早就明白了一個道理:男人就是如此,一切安好時不懂得珍惜,如今等了傷,才會從心底升起一點點憐惜,悔不當初。
——哪怕他功名就、頤養天年,可他失去了寶貴的,多慘啊多啊!
此時此刻,就是重傷的主角,看賀知洲那憐惜又慕的眼神,必定已經回心轉意,從此對百般呵護與疼。
賀知洲對的所思所想一無所知。
他只覺得柳姑娘穿著白服,那些像是不要錢的番茄醬,啪嘰一下被拍在白紙上。
這讓他想起遠在他鄉的薯條和漢堡,有點懷念,也有點。
“柳姑娘!”
眼見柳螢肩頭的一個勁往外流,賀知洲只覺肩膀也隨著發痛。他心下慌,一把將石片從胳膊上扯出來,聽得旁的孩痛哼一聲。
“別——”
柳螢從牙里努力出這個字,話音出口的剎那,石錐便已經離開了。
在心里罵了這蠢貨一遍又一遍,卻礙于人設定,只能氣若游地說一句:“賀哥哥,若是不將它取出來,或許還能止一止。”
賀知洲手里如同握著把兇,聽這樣說,心里愧疚不已,趕忙道歉補救:“對不住對不住!我也是一時心急!”
柳螢本打算、可憐兮兮地回他一聲“好”。
然而話沒出口就一腦全哽在嚨,聲音了回去,兩顆眼珠子倒是猛地朝外邊蹦,差點竄出眼眶——
草!!!
這白癡看不樂意,居然直接把石柱給捅回去了,捅回去了!!!
痛得目眥裂,真的好想說一句,你這小腦發育不完全的白癡,何至于此。
Advertisement
可不行啊,只是朵天真無邪弱懵懂的小白花,哪怕被他捅了一次又一次,也只能淚眼汪汪地咬住:“賀哥哥,你在做什麼?”
賀知洲有點尷尬。
他還沒傻到我殺我隊友,奈何之前被火凰嚇得了分寸,又聽柳螢哭哭啼啼一直在耳邊說,慌張之中一個下意識,才又將石錐放了進去。
可他當然不能告訴實話,那樣只會顯得自己活像個傻子。
他默了半晌,雖然底氣不足,但還是努力表現出浩然正氣的模樣:“柳姑娘莫怕,如今形勢危急,只能采取此等下下之策止。等咱們離險境,我再仔細為你療傷。”
柳螢的眼角,劃過一滴清淚。
——那你,也麻煩,請捅在同一個地方啊。
之前上只有一道口,現在被賀知洲又捅一次,買一送一,直接了倆。
若是今日死了,罪魁禍首必然不是火凰,而是這位蠢鈍如豬的好隊友。
柳螢拼命忍住嚨里的一口氣,淚眼朦朧地問他:“賀哥哥,有沒有人曾告訴你?”
賀知洲茫然接話:“呃……我很你?”
“不是啊。”
被這人給氣笑了:“你的腦子,真的和平常人很不一樣。”
賀知洲這回聽明白了。
這人在罵他呢。
“柳道友傷了嗎?”
寧寧以劍氣斬去一簇火,匆匆朝他倆這邊看了一眼:“況如何,可有大礙?”這才是真實意的關心啊!
一切全靠同行襯托,在賀知洲與許曳的反襯下,寧寧揮劍敵的姿是那麼麗又可靠,讓柳螢鼻尖一酸:“不用管我,我沒事!”
寧寧這才回一個淡淡的笑。
劍與火氤氳在白皙致的臉龐,漆黑杏眼里恍如盛有滿天星辰,只需輕輕一彎,便有萬千劍意與流轉其間,人心甘愿沉溺其中。
Advertisement
柳螢愣愣地想,為什麼在最初時候,選擇接近的人不是寧寧呢?
“我的水符已經不多了!”
他們雖是劍修,卻也大概懂些符篆知識。許曳第不知多次用水龍沖散火勢,奈何符咒有限,火凰掀起的烈焰卻是無窮,一來二去,家底都快被搬空。
西山的溫度本就灼熱,被它這樣肆無忌憚地燒來燒去,連空氣和泥土都能被蒸。許曳斗得焦頭爛額,一旁的裴寂亦是眉頭蹙。
火凰不但攻勢兇猛,護的羽翼更是麻煩。
與普通鳥禽不同,這類百年兇早已強筋固,周火紅的羽看似,實則聚了一副十足堅固的盔甲,將它全然籠罩其中。
裴寂打架從來不講花里胡哨,拔了劍就是干,然而好不容易劈開重重烈焰,讓所剩不多的劍氣勉強及火凰,那單薄的劍氣卻難以將它傷及分毫。
寧寧多數時候都在飛速閃躲,偶爾用星痕劍斬開迎面而來的滾燙腥風,自始至終盯著火凰所在的方向。
在觀察。
這只大鳥攻防兼備,若是只有那層堅固的羽,或許還能用蠻力劈開;可如今熊熊烈焰不止,環繞在它周時,形了最難破除的護盾,他們連接近都難,更別提拔劍一決高下。
——那倘若不靠近呢?
寧寧眸微沉,形一晃,靈巧躍至火凰側的巨巖之上。恰逢火勢被裴寂斬去,站在這地理位置,能清楚看見它吐出火焰時的模樣。
不對。
不是“吐出火焰”,而是將的天地靈氣引至前,化出一道灼熱白之后,再用力吐息,將其吹向四周。
虧之前還在因為火凰焦頭爛額,像這樣的話……不就好辦多了嘛。
許曳沒了水符,只能手忙腳地斬去陣陣火風,哪想抬頭一瞟,就見寧寧躍上前,直直往火凰吐出的烈焰前跳。
他被嚇得三魂沒了七魄,唯恐這姑娘被熱昏了頭,扯開嗓子喊:“寧寧,你做什麼?”
哪知寧寧飛快他一眼,散落的黑發如霧如紗,將眉眼遮掩小半,出噙了笑的淺薄。
居然朗聲笑了笑,聲線清脆得像是風鈴搖擺撞,與周遭景象實在格格不:“對付火,可不能用水。”
許曳愣了一下。
滅火不用水,那應該用什麼?
寧寧沒再說話,因為逐漸靠近了洶涌火,連呼吸都有些困難。曾用傳音告訴裴寂先行撤離,這樣一來,與火凰對峙的便只剩下一人。
所有的火勢,都將朝著一人而來。
與想象中相差無幾,自從其余敵手紛紛退下,火凰只得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不遠的小姑娘上。
更何況還迎著火而立,它只需要稍一用力,就能把燒得連骨頭也不剩。
紅瞳孔中殺機暗涌,通火紅的巨鳥長鳴一聲,環繞于邊的大半烈焰應勢而起,徑直沖向那抹一不的影子。
寧寧握手中的星痕劍,在心底默念倒數。
如果火凰是從口中直接噴出烈焰,就表明它并不畏火,擁有很強的火抗屬;但若像現在這樣只是在半空悄咪咪火球,那它就有大半幾率,同樣害怕被火燒。
既然火凰的烈焰毒暴烈,絕非凡俗之;而它的羽翼又偏偏刀槍不,堅固非常。
若是這最為毒辣的火焰撞上了最難以破開的羽,屆時會變怎樣?
寧寧屏住呼吸,從儲袋里拿出幾張符咒,暗暗念口訣,旋即在數張符篆的加持下拔劍而起,劍所及之,星痕陣陣。
對付火不能用水。
要用風。
古有諸葛孔明赤壁借東風,如今沒有天時地利,那就用一堆風符、一片橫沖直撞的火風和一把劍——
親手把風造出來。
“這是……!”
柳螢忍了疼痛,在灼目的火之中睜大雙眼,凝視著不遠的淡影,指尖不由一。
四野八荒,風聲大起。
的長被吹得獵獵作響,長劍嗡然如巨龍長,在锃然清響后猛然一落——
霎時劍風激、連綿不絕。
雪白劍影滿蘊星辰之,化作一道勢若洪流飛瀑的奪目亮,連穹頂之上的烈日也為之一黯。
站立于星河中央的寧寧眉目如畫,向來笑意盈盈的面龐上,頭一回顯出了冷冽的決意與劍息。
符篆引來的疾風凜然作響,由火凰掀起的烈風回旋如流,更為勢如破竹的,是長劍之下襲來的劍風。
猜你喜歡
-
完結10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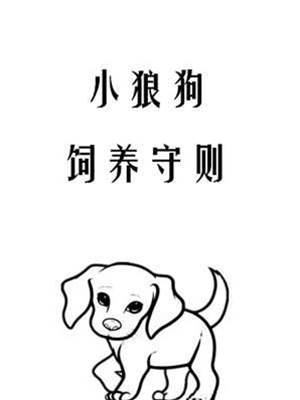
小狼狗飼養守則
江南邊陲有個清溪鎮,鎮上有個小姑娘名叫林羨,先克死了爹,后克死了娘, 末了竟連訂過娃娃親的前未婚夫婿也差點不能免俗,從此惡名遠揚。 外頭冷言冷語撲面來,林羨站渾不在意的低頭看看乖巧抱著她手臂,唇紅面嫩的小男娃, 安慰他,“婚姻之事有就有了,沒有也不強求的。” 小男娃抹抹眼淚開口軟糯,“阿羨嫁我便是了。” 林羨哄他不哭,胡亂點頭,卻不想沒幾年這話就成了砸自己腳的石頭。 女主假軟妹CP男主真病嬌。 女主:論如何把生意做成全國連鎖的小甜文。 男主:為媳婦兒不斷打怪升級成為boss的大寵文。
26萬字8 6492 -
完結296 章

失明后認錯夫君
成婚前夕,阿姒意外失明。某日,他們居住山間小院來了羣官兵,稱要抓暗殺晏氏一族長公子的刺客。 夫君未歸,阿姒慌不擇路藏身櫃中。 忽而,外頭傳來一個清潤的聲音,如深潭墜玉,獨一無二的好聽:“沒尋到人?” 阿姒認得,這是她的夫君。 她鑽出櫃中,循聲牽住青年袖擺,怯怯喚他:“夫君,我在這。” 那人稍頓,良久,輕笑一聲,隔着衣袖握住她腕子。 他把她帶下山,安置到別處。 從前疏離寡言的人,日漸溫柔,爲她讀書解悶、弄弦撫琴,甚至浣布擦身。唯獨對給她治眼疾一事,不甚熱絡。 阿姒漸漸習慣了眼盲的日子,二人也從初成婚時的生分到日漸親密,可就在他們圓房時,她忽然看見了。 燭火搖曳,上方青年清雅溫潤,面若冠玉,一雙含情目笑意和煦如春。 可這並非她那劍客夫君,而是那位權傾朝野的晏氏長公子,晏書珩。 她掙扎着想逃,卻被晏書珩抓住手,十指緊扣,青年手背青筋蚺起。 一滴熱汗落在阿姒眼角,他低頭吻去,與她額頭相抵,目光交纏:“現在,你是我的妻了。” “阿姒,喚我夫君。”
45萬字8.33 12775 -
完結140 章

嬌軟美人和她的三個哥哥
沈家滿門英烈,只剩下雲黛一個小姑娘。 晉國公感念沈父的救命之恩,將九歲的小云黛收爲養女,接進府中。 入府當天,晉國公領着雲黛,對他三個兒子說:“以後這就是你們的小妹妹,你們要寵着她,護着她。” 謝大高冷寡言,看她一眼:“嗯,知道了。” 謝二溫柔儒雅,輕搖紙扇:“小妹好。” 謝三鮮衣怒馬,擠眉弄眼:“以後哥哥罩着你!” 面對性格各異的三位兄長,寄人籬下的雲黛怯怯行禮:“兄長萬福。” * 時光荏苒,雲黛出落得昳麗嬌媚,絕色傾城,無數世家公子爲之神魂顛倒。 謝二爲她寫情詩,謝三爲她跟其他公子打架。 他們私心裏,都不想再拿她當妹妹。 就在各路桃花氾濫之際,有大淵戰神之稱的晉國公長子謝伯縉攬過雲黛的腰,帶到謝二謝三面前,平靜宣佈:“叫大嫂。” 謝二謝三:???
61.5萬字8.18 134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