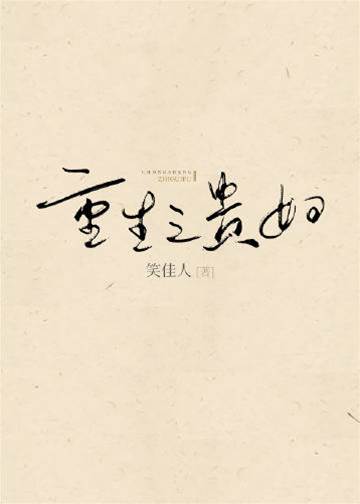《九重紫》 第496章 成事
因孀居而大歸的曾孫要再醮?!
紀老太爺聽著一口氣沒有上來,昏死過去。
紀頌和紀頎嚇得手腳冰涼,慌慌張張地上前,一個掐著紀老太爺的人中,一個高聲喝斥著小廝去請大夫。
半晌,紀老太爺才幽幽地醒了過來,開口就問紀詠去了哪里:“……他常在貓兒胡同走,不可能不知道這件事!”
紀頎忙為兒子辯護:“見明剛到詹事府,這些日子一直忙著應酬同僚,本就沒有著過家,他怎麼會知道院的事?就是我們,也不知道令則出去買個頭花人就會不見了……”
紀老太爺一掌打在了紀頌的臉上:“沒用的東西,連宅的事也弄不清楚,難怪會被竇老五給下來。你這輩子也就是個當侍郎的命!”
京都玉橋胡同的紀宅,是由紀頌的妻子主持中饋。
紀頌捂著臉,一句辯解的話也不敢說。
紀老太爺怒道:“只要我活著一天,紀家就沒有再嫁婦!你去告訴竇家,他們不要臉,我們紀家還要做人,他們要娶,就娶了紀令則的牌位回去……不,我們紀家沒有再嫁之,他們家的事,與我們紀家沒有任何關系!”又指了紀頎,“你把紀令則給我帶回宜興去沉塘。娘老子那里,自我有頂著——想當初,是他們說兒在韓家的日子不好過,我憐惜小小年紀就守了寡,這才和韓家據理力爭地把接回了家,倒好,竟然私相授,勾引起自己的表弟來,這不要臉的東西,人人得而誅之!”
大哥都被打了,紀頎自然更不敢說話了,匆匆應“是”,去和竇家涉。
紀詠聞言卻是大驚,道:“你說子賢和堂姐已經找到了?怎麼這麼快?”
Advertisement
子息小心翼翼地道:“是英國公世子爺出面幫著找到的,帶著竇家的七老爺,把表爺和小姐都帶回了靜安寺胡同。姑剛剛請了過來為表爺向小姐提親,老太爺氣壞了,連大老爺都挨了老太爺一耳……老太爺還說,要把小姐沉塘,竇家要娶,就娶了小姐的牌位回去……”
“你怎麼這麼多話?!”紀詠不耐煩地道,“我問你一句,你倒能說出十句來。你再去趟竇家,幫我打聽打聽竇家怎麼會應了這門親事的?”
子息恭應“是”,出了紀府。
紀詠在書房里打著轉。
竇德昌還沒有這本事能讓竇家的人同意這門親事,要不然他也不會先斬后奏和紀令則躲到大相國寺去了。能把事攪和到這個地步的,只有可能是宋墨。
他順勢而為,讓竇家不得不答應竇德昌娶紀令則,既討好了竇德昌,又在竇世英面前表現了自己的能力和手段……還有竇昭,平日里看著和竇世英針尖對麥芒似的,實際上最看重自己的父親,出了這樣的事,竇世英肯定是惶恐而不知所措,宋墨為竇世英解了難,竇昭知道了還不知道要怎樣激他呢!
媽的宋墨,真是狡猾!
他一掌就拍在了茶幾上。
茶盅茶壺嘭嘭作響,他的手疼得發麻。
紀詠忍不住低聲地罵了一句。
子上進來問紀詠晚膳擺在哪里。
紀詠想了想,道:“我去陪老太爺用晚膳好了!”
他大步去了紀老太爺的書房。
紀老太爺正在那里咆哮:“什麼?竇家不愿意放人?你們都是吃素的?他們說不放人你們就乖乖地回來了,聽憑竇家把人給扣住不放……”
“曾祖父,”紀詠閑庭信步地走了進去,“您也是古稀之年了,火氣太大,容易傷肝!”
Advertisement
紀老太爺看到紀詠,氣得更厲害了,撇下了紀頎,訓起紀詠來:“你這些日子跑到哪里去了?總是不見人影!紀令則和竇十二私奔了,你可知道?這要是傳了出去,我們紀家的臉面要往哪里擱?”
紀詠輕快地笑,道:“竇家都不怕丟臉,我們有什麼好怕的?再說了,子賢也不錯,您一個守寡的曾孫,竟然能再醮個兩榜進士當原配嫡妻,還有比這更劃算的嗎?我真不知道您在氣些什麼!要是我,早就給令則堂姐準備嫁妝了!反正竇家是鐵了心要娶令則堂姐過門,您又何必非要做惡人?”
一席話說得紀老太爺啞口無言,若有所思。
一旁的紀頎忍不住提醒紀詠:“韓六雖然不在了,可令則依舊是他的妻子、韓家的媳婦,就算我們答應,韓家恐怕也不會答應吧?”
那就是宋墨的事了!
紀詠撇了撇,臉上閃過一幸災樂禍的笑容:“所以我說曾祖父老糊涂了,初嫁由父,再嫁由已。紀家放著好人不做,卻非要給韓家出面打頭陣,兩面不討好,白白錯過了這次機會。”
紀老太爺閉著眼睛不說話。
紀頎卻知道祖父是醒悟自己錯了,下不了臺而不愿意向紀詠低頭。
這幾年紀詠在仕途上一步一個腳印,算無策,上雖然一如從前那樣的刻薄毒舌,可一旦有好事,卻知道照顧自家人了,他又勝在年輕,在紀家聲日隆,很多人都不由都高看他一眼,而紀老太爺的影響力卻開始漸漸地減弱。
他道:“照你說,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
“自然是由我出面去和姑母涉。”紀詠大言不慚地道,“只要韓家答應了,我們紀家還有什麼不答應的?”
Advertisement
紀老太爺聽著睜開了眼睛,冷冷地瞥了紀詠一眼,道:“我看你是想去竇家討好賣乖吧?”
“給您看出來了。”紀詠不以為意地道,“我好歹也姓紀。你們去唱了紅臉,我現在去唱白臉,竇家韓家兩不得罪,豈不是更好?”
紀老太爺冷“哼”一聲。
紀詠笑道:“這件事就這樣說定了。我這就去趟貓兒胡同,免得姑母今天晚上睡不著覺。”然后也不顧紀老太爺的臉得像要下雨似的,徑直出了門。
紀氏聽紀詠說,紀家之所以這麼鬧一場是做給韓家看的,實際上紀家是樂見紀竇兩家再結親的,紀氏頓時喜出外。知道,祖父是不可能突然想通的,能有這樣的結果,肯定是紀詠從中周旋的結果,紅著眼睛拉了紀詠的手,哽咽道:“我這也是不想毀了子賢的前程!”
“我知道。”紀詠道,“我實際上為子賢可惜的。天下何無芳草,他又何必非要娶了令則堂姐?不過事已至此,我們也只能想辦法不讓事態擴大,免得壞了子賢的名聲。”
紀氏連連點頭,覺得紀詠前所未有的心。
慨道:“竇家的長輩們原也不同意,全仗了硯堂從中說和,韓家的事,恐怕還得麻煩硯堂了。”
“他在勛貴圈子中是有名的足智多謀,”紀詠的眼睛亮閃閃的,“您把這件事給他去辦,最合適不過了。”
紀氏連連點頭,第二天親自去了英國公府,把事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宋墨。
竇昭聽著直皺眉,道:“硯堂是婿,由他出面合適嗎?”
韓家若是通達理,當初韓六爺病危的時候就不會著紀令則過門了。
紀氏面紅耳赤,道:“我這也是怕夜長夢多,偏生你六伯父不愿意管這件事……”
Advertisement
“沒事。”宋墨打斷了紀氏的話,他輕輕地了竇昭的手,道,“總不能讓岳父去跟韓家的人談吧?這件事由我出面好了!”
“硯堂!”紀氏滿臉的激。
竇昭則地握住了宋墨的手。
想讓他低三下四地去求韓家,這恐怕是紀詠的主意吧?
宋墨在心里冷哼一聲,給了竇昭一個有竹的微笑。
他就沒想過和韓家和平解決這件事,而是派了人去查韓家的事。
韓家是江南的名門族,興族百余年,子弟眾多,怎麼會沒有點私之事?
宋墨給韓家送了一封信,韓家很快就同意了紀令則的婚事。然后宋墨就開始忙著辦竇德昌的婚事。從確定全福人到請欽天監的幫著算吉日,他忙得團團轉。
竇世英逢人就夸:“要不是我這個婿,家里早就了套了。”
大家都知道竇德昌被人綁架又被宋墨救了回來的事,紛紛夸獎宋墨孝順、能干。
竇世英就趁機請大家去喝喜酒:“日子定在六月初二。欽天監的說這是個好日子。娶得是紀家的姑娘,子賢的表妹。”至于是誰,翰林院的那些夫子就不好多打聽了。
消息傳出來,紀詠氣得肝痛,暗想,倒便宜了竇德昌這個笨蛋!
偏偏又被哭得傷心絕的紀母拉著訴苦:“你舅舅們怪我沒有約束令則,可我畢竟只是個嬸嬸,難道還能眼也不眨地盯著不?我那六叔父良為娼鬧出了人命,自己做了天怒人怨的事被人捉住了把柄,不自我檢討,反說是我們紀家不幫他……那個宋硯堂也是,手段這麼狠干什麼?他就不怕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哪天到韓家人手里?”
“您就說兩句吧!”紀詠厭惡地道,“韓家照這樣下去,只有落魄的份,還想和宋墨斗?做夢去吧的!”
紀母聽著不高興了,嗔道:“你這孩子,不為你舅舅們說話反站在宋硯堂的那邊,你到底姓什麼啊?”
紀詠翻著白眼,丟下母親一個人走了。
紀母忙追了出來。
紀詠已不見了人影。
紀母困地問子息:“他這是怎麼了?”
子息只得道:“許是詹事府的事太多了!”
他再也沒有那膽量給紀母報信了。
※
姐妹兄弟們,送上今天的更新。
PS:求紅票!
※
猜你喜歡
-
完結205 章
棄女農妃
穿越而來發現身下有個孩子,還是"她"剛生下來的.被好心人救起,面對著土培瓦房,破窗爛牆,還有手上嗷嗷想吃的粉嫩孩子,安夏咬牙,好歹是從農村出來的,也有經驗,一定能在這農村幹番大事業.身無分文,沒有屋舍,她就伐木建房;山林找食,勞動換吃,孩子也餓不死;手藝豐富,也能開店賺錢,買田種地;新技術帶動,竟也能致富.看著日漸帥氣的兒子,再看看眼前和兒子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男人,安夏挑挑眉,"坦言"道:"你長的和我兒子可真像啊,記憶中,我丟過一個兒子,該不會是閣下吧?"男人挑眉道:"你確定你生的出來?"當單親窮媽變身富甲一方的富婆,再次踏進那個曾經丟棄自己的家,有時如何的一番場景呢?當曾經嘲笑辱罵她的人對她跪地求饒,他們應該沒有想到會有那麼一天吧?腰包越來越鼓,那些眼饞的人也越來越大,想盡辦法上門拜訪,還賄賂她的兒子?【片段一】"孃親,你看,這是周叔叔給的牌子,說能號令千軍萬馬,給你當聘禮的."兒子雙手捧上將軍令牌,說道.某女嫌棄,"兒子,這令牌硬蹦蹦的,不能吃不能花,有個屁用,一個令牌想奪我的錢?休想!"……"
78.7萬字8 77308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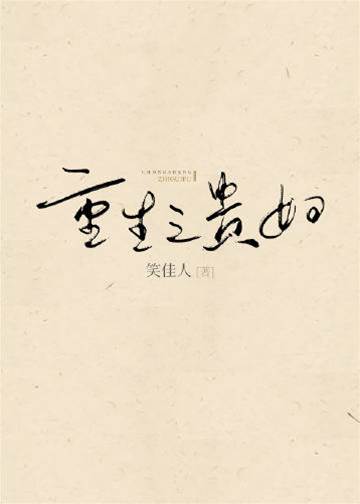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87698 -
完結556 章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0227 -
完結115 章
朕甚是心累
主角:沈玉方睿。簡介:朕被掰彎後才知道對象是個女人! 朕重生之後一直知道自己的臣子是個女兒身,卻要裝做不知道。 朕繼位多年,還是個童子身。 大總管捧著幾張牌子,問:“陛下,今晚要翻哪一位小主的牌子。” 朕看了眼那幾張玉簡,幽幽的道:“能翻沈愛卿的牌子麼?” 大總管:“……”陛下,沈大人是男人呀! ~~~~~~~~~ 正要解開束胸沐浴的沈玉:總覺得一直有人在窺探她。。。。 屋頂之上的陛下:愛卿呀,愛卿,你倒是快點進行下一步呀。
32.3萬字8 1324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