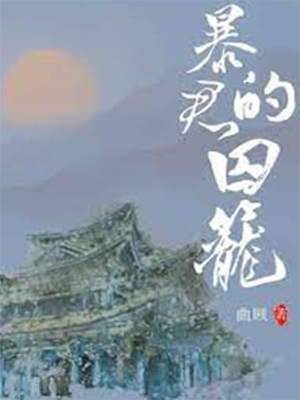《重生之貴婦》 第197章 追妻番外4
溫如月萬萬沒有想到, 表哥寧可在飯點趕走也要與姑母商量的事,竟然是的婚事,而且還是要將嫁給一個出平平的衛所小兵!
別說現在住在燕王府, 與燕王是親戚,就算還留在溫家, 的父親也做了京了,也不至于嫁給一個小兵吧?
溫如月與姑母哭了一場, 可知道,姑母子,全都聽表哥的!
所以, 翌日傍晚, 溫如月就來了澄心堂。
魏曕神如常地來見表妹, 而他如常的神,便是清冷一片。
溫如月咬了咬, 表哥這子,怕是沒有姑娘會喜歡, 可表哥長得俊,又是皇孫貴胄,如果能嫁給表哥,將來就可以做郡王妃了, 在燕地吃香喝辣百姓羨慕。
溫如月想嫁給表哥,兩人是表兄妹,親上加親不是很正常嗎?
“安順兒,你先出去吧。”溫如月瞥眼站在表哥邊的安順兒,不太高興地道。
安順兒看向主子。
魏曕點點頭。
安順兒就退下了, 堂屋的門大開,夕灑了滿院。
見溫如月只是神復雜地著自己, 魏曕道:“表妹有話不妨直說。”
溫如月咬咬,攥著帕子道:“我才十四,表哥怎麼就想到要我嫁人了?”
魏曕道:“等父王回來,很快也就過年了,十五出嫁剛剛好。”
溫如月急了:“可我不喜歡表哥挑的那人!”
魏曕皺眉,問:“那你喜歡什麼樣的?”
溫如月就又不說話了,瞥他一眼,面上出紅來。
如果魏曕只是十九歲的魏曕,一個從未會過兒長的孤僻皇孫,他或許還看不出溫如月的心思,可他是從景和二年回來的,他有過一個對他意綿綿的妻子,一個也曾這般臉頰紅語還休地凝他的妻子。
Advertisement
所以,表妹竟然喜歡他?
念頭一起,魏曕一下子想明白了很多事。
他終于知道,為何上輩子他與殷蕙定親不久,表妹就去京城投奔舅父了,原來是表妹發現嫁他無。
既然表妹對他有,后來紹興重逢,表妹口口聲聲要給他做妾,說什麼不圖寵,又怎麼可能是真的?
再有,殷蕙為何會誤會他心里一直藏著一個好表妹,肯定也是二嫂、二妹看出了表妹的心思,故意在殷蕙面前搬弄過口舌。
最可笑的還是他,親手將表妹帶回王府,還想著讓表妹給殷蕙作伴,可這樣的表妹,怪不得殷蕙會說寧可養只烏。
“既然表妹不滿意我為你挑選的人,那表妹回去收拾收拾行囊,過幾日我便送你去京城,讓舅父替你挑選良婿。”
魏曕面無表地道。
溫如月難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魏曕徑直安順兒進來,送客。
如果說溫如月昨晚飯點被攆只是一場尷尬,現在親耳聽表哥說要送去京城,溫如月便覺得無地自容,暗示地那麼明顯,表哥不喜歡也就罷了,竟然都不允許再繼續留在燕王府!
回到姑母這里,溫如月狠狠地哭了一場,溫夫人安不好,只好跑來問兒子究竟是怎麼回事。
魏曕冷聲道:“您深居王府,無法為表妹選婿,我選的又看不上,與其繼續耽誤表妹,不如讓舅父替做主。”
溫夫人把侄當兒看,很舍不得,再說了,哥哥娶了續弦,誰知道那續弦的嫂子會如何對待侄?
溫夫人猶豫再猶豫,試著道:“那,我請王爺替如月一個?”
魏曕不怪母親心疼表妹,這麼多年,他很去陪母親,都是表妹在母親邊盡孝。
Advertisement
魏曕心平氣和地給母親講道理:“父王公務繁忙,他愿意接表妹進府已經是憐惜您了,哪還有閑暇替表妹選婿?”
溫夫人低下頭,一副又不敢煩擾燕王又不忍與侄分別的樣子。
魏曕見了,只好說出真相:“表妹真正想嫁的是我,可我對無意,不可能娶,送走,也是讓死心。”
溫夫人震驚道:“,親口跟你說的?”
魏曕看眼母親,道:“是。”
溫夫人徹底明白了,換喜歡一個人,卻被對方冷冷拒絕,也要大哭一場的。
表兄妹倆都僵這樣了,侄繼續留在王府,以后見了表哥,如何抬得起頭?真的不如去京城。
溫夫人嘆口氣,回去安侄。
不用別人勸,溫如月已經萌生了去意,嫁不得表哥,燕王就算肯替選夫大概也不會挑什麼名門子弟,與其繼續在燕王府蹉跎歲月,不如去京城。金陵那地方,那麼多名門世家,以的容貌,就不信嫁不得高門!
想到做到,溫如月只說做夢夢見父親病了,心中焦急,然后就在溫夫人的陪伴下給徐王妃磕頭謝恩,隨即乘車離去。
魏曕派了澄心堂的一個小太監去送表妹,他還給舅父寫了一封信,囑咐舅父不要與金陵世家、勛貴子弟結親。
到底表兄妹一場,魏曕不想溫如月再重蹈上輩子的覆轍,嫁給薛煥那種心狠手辣之人。
但這封信,也是他能為溫如月做的最后一步,如果溫如月非要嫁薛煥,如果舅父不聽他的,魏曕也沒有辦法。
.
溫如月離開平城時,已經是十月了,北風呼嘯,冷得人不想出門。
轉眼到了黃昏,汪平在殷家附近盯了一天,確定二小姐不會再出門了,只好回了燕王府,向三爺復命。
Advertisement
魏曕讓汪平退下,一個人在堂屋坐了片刻,魏曕去了書房。
翌日清晨,魏曕將一個畫匣給汪平,囑咐道:“你親手送到二小姐手上,不得假托旁人。”
汪平鄭重應下,憑借腰牌離開燕王府,他門路地來到了殷宅。
汪平才十二三歲,容貌清秀,紅齒白的,在外人看來,這就是個儀表堂堂的年郎,倒看不出他是個太監。
所以汪平來殷宅這邊叩門,周圍的街坊也見怪不怪,沒有過多留意。
門房看見汪平手里的燕王府腰牌,不敢不讓人進,趕把德叔請了過來。
殷墉出門了,德叔也不敢做殷蕙的主,讓小丫鬟去稟報二小姐。
殷蕙知道汪平,是魏曕邊第二得用的太監,在澄心堂的地位僅次于長風、安順兒。
但不想再與魏曕有任何牽扯,所以只讓小丫鬟回了兩個字:不見。
小丫鬟跑回前面回話,汪平一聽,眼睛一轉,抱著畫匣子在門廳跪下了,對德叔道:“二小姐不見我,我便在此長跪不起。”
再沒有人比他更知道三爺多看重這位二小姐了,平時三爺多守規矩啊,一年到頭也不會他們離開王府去跑做什麼,可自從王爺做了月老,姻緣的紅線差點將三爺與二小姐綁在一起,三爺就天天派他出門盯著二小姐的向,想得跟著了魔似的。
這匣子里面裝著的肯定是三爺討好二小姐的禮,說不定二小姐見了就心了,所以,他必須辦好這次的差事!
德叔又不好將汪平丟出殷家大門,勸說不,德叔只好親自來了蕙香居。
“他還沒走?”殷蕙意外地問。
德叔愁道:“跪著呢,說什麼二小姐不見他,他就在咱們家長跪不起。”
Advertisement
殷蕙皺眉,魏曕的人,居然也會如此無賴?
德叔道:“我看他懷里抱著一個匣子,既然是三爺待他的,他見不到您肯定也不敢回去當差。”
殷蕙就想到了魏曕的冷臉,汪平不怕才怪。
“罷了,您帶他過來吧。”殷蕙也有點好奇魏曕這般折騰究竟要做什麼。
德叔離開后,金盞湊到殷蕙邊,笑嘻嘻道:“小姐長得,連燕王府的皇孫都被您迷得神魂顛倒的。”
可還記得在東山,三爺親自騎馬去堵小姐呢,與那些被小姐迷住的風流子弟沒差多。
殷蕙瞪了金盞一眼,沒出息的丫頭,真見到魏曕的時候,金盞、銀盞都變了骨頭,大氣都不敢一下,這會兒倒是敢編排起魏曕來。
外面,汪平跟著德叔一路往里走,他可是燕王府里的人,殷家大宅在他眼里也就是普普通通,一直到進了二小姐的蕙香居,汪平才如突然開了眼一樣,看哪里都像看到了一堆銀子,著貴氣,與這里相比,三爺的澄心堂真是太寒酸了!
進廳堂,汪平再次見到了殷蕙。
上次殷蕙去東山,汪平只是遠遠地看見上了馬車,沒看清楚模樣,此刻近距離地撞上,汪平的心便是一,只覺得艷如二爺的夫人紀氏,在這位殷家二小姐面前也張揚不起來,難怪三爺喜歡得如癡如狂,仿佛變了一個人。
看了一眼,汪平便彎下腰,雙手托著匣子來到殷蕙面前,恭聲道:“二小姐,這是我們三爺所贈,還您笑納。”
殷蕙看眼金盞。
金盞接過匣子,再捧到殷蕙面前。
殷蕙沒接,讓放到桌子上,然后對汪平道:“無功不祿,還請公公轉告三爺,以后不要再送了,你若再來,殷家也不會再放你進來。”
汪平覺得二小姐可真夠傲的,但誰讓二小姐長得仙一般,仙可不就是這樣,高高在上。
“是,小的一定轉告三爺。”
至于三爺聽不聽,他可不敢管。
德叔去送汪平出門,殷蕙無視金盞、銀盞好奇的視線,自己拿著匣子去了室。
坐到窗邊,殷蕙對著匣子出了會兒神,才意興闌珊地打開蓋子。
里面是一卷畫軸,畫軸下著一封信。
殷蕙先拿出了信。
拆開信封,取出……厚厚一疊信紙。
這信紙的數量讓殷蕙又陷了回憶。
魏曕惜字如金,口筆都如此,以前他在戰場寫家書回來,全都是兩三句話,可能上輩子幾封家書加起來,都沒有這里一張信紙上的容多。
恍然過后,殷蕙諷刺地笑了笑,開始看信。
信的開頭,他居然寫的是“吾妻阿蕙”。
殷蕙微微咬牙,那是上輩子,這輩子還沒嫁人,與他沒有半點關系!
接著往下看。
“東山一面,時間倉促,很多事未能盡言,今日特來答卿四問。”
“答卿第一問。你我婚,乃是三六聘,我從未將你視作暖床人。誠然,我冷淡,沉默寡言,待你亦不夠溫,可那絕非刻意,只是委實不知如何開口,你幾次抱恙,我亦憂心。”
跟著,魏曕開始列舉他記憶中殷蕙的幾次生病,甚至將生衡哥兒的那次虛弱也算了進去。
這番回憶就占了五張信紙。
他像記賬似的一次次列下來,還會將他記得的一些藥方所用藥材寫上。
如果真的不曾關心,又哪里能將十年里的事記得這麼清楚,有的甚至連殷蕙自己都忘了。
“答卿第二問。你我婚,門第有別,我的確心存抗拒,一切皆是年輕氣盛,卻絕非針對殷家,而是慮及自……”
這條魏曕著墨不多,但殷蕙明白他的意思。
他是庶子,生母低微的庶子,本來就被兄長、下人們看輕,燕王再給他安排一門商戶妻子,可想而知那段時間魏曕承了多來自旁人的嘲弄與同。
殷蕙有多被親戚們羨慕,魏曕就會多被皇親國戚們鄙夷。
換個人,可能不會給殷蕙什麼好臉,甚至輒打罵,魏曕沒有這樣對殷蕙,他的冷臉也不是獨獨針對。
“答卿第三問,我與溫如月,沒有任何私。”
這一條,其實那天見面魏曕就解釋過了,所以說過的話魏曕沒有再重復,只告訴溫如月已經去了京城,婚事將由的父親親自做主。
殷蕙怔了怔。
魏曕明知溫如月上輩子在京城過什麼苦,還敢讓溫如月過去,是這點,就足以證明魏曕對溫如月不但沒有私,連兄妹都只是薄薄一層。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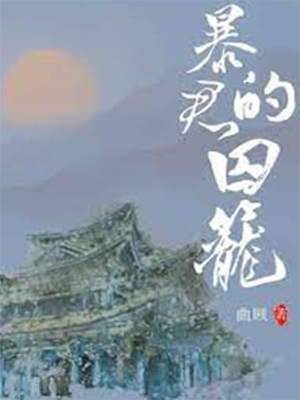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8976 -
完結283 章

凰權至上
謝晏和作為一個被當朝太子退過婚的貴女,人生陷入了死局。 前未婚夫:太子 敵人:太子妃 敵對指數:不死不休 好在,這盤死棋被謝晏和盤活了。 現任是皇帝,盟友是公主,她重新走出了一條通天大道。 這就是個披著宮斗皮的老夫少妻的甜寵文。
77.4萬字5 9355 -
完結705 章

殿下又在塌前罰跪了
她重生醒來,第一件事便是撕毀婚書恢複自由身,自此在家人的擁護跟自己預知未來的能力發光發熱,成為了京城刺手可熱的存在,渣男後悔求上來,她轉身投入太子爺的懷抱,“不好意思,本小姐名花有主。”
66萬字8 24175 -
完結183 章

風流債
沈初姒當年嫁給謝容珏的時候,還是先帝寵愛的九公主。縱然知曉謝容珏生來薄情,也以爲他們少年相遇,總有捂熱他的那日。 直到後來父皇病逝,兄長登基,沈初姒就成了沒人撐腰的落魄公主。 京中不少人私底下嘲笑她,跟在謝容珏身後跑了這麼久,也沒得到那位的半分垂憐。 沈初姒恍然想起當年初見。原來這麼多年,終究只是她一個人的癡心妄想。 謝容珏生來就是天之驕子,直到他和沈初姒的賜婚旨意突然落下。 這場婚事來得荒唐,所以等到沈初姒說起和離的時候,謝容珏也只是挑眉問道:“可想好了?” 沈初姒將和離書遞給他,只道:“願世子今後,得償所願。” 直到後來的一次春日宴中,兩人不期而遇。 沈初姒面色如常,言笑晏晏,正逢彼時的盛京有流言傳出,說沈初姒的二嫁大概是大理寺少卿林霽。 衆人豔羨,紛紛感慨這也是一樁不可多得的好姻緣。 卻無人可見,那位生來薄情的鎮國公世子,在假山後拉着沈初姒,“殿下準備另嫁林霽?” 沈初姒擡了擡頭,掙開被他拉着的手,瞳仁如點墨般不含情緒。 “……謝容珏。” 她頓了頓,看着他接着道: “你我早已和離,我另嫁何人,與你又有什麼關係?”
29.6萬字8 10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