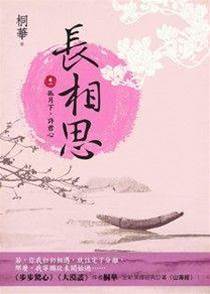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夫人是京城一霸》 第69章 七歲不同席
母親能不能歸來,和攆走幾個刁奴沒什麼關系,展懷遷心里是明白的,但既然說了要送朱嬤嬤回家鄉養老,就不能讓七姜白惦記著。
他們再要回去,只見大院嬤嬤出來,和氣地說:“叔叔大哥房里的事,哥兒和夫人都是孩子,不該手。已經很晚了,早些回去歇著,莫再給老太太和大老爺添煩惱。”
展懷遷知道是父親的意思,就怕七姜不明白,可邊的人竟然應道:“是,我們這就回去。”
他和嬤嬤都呆了一下,直等七姜走了,嬤嬤才催他:“哥兒也去吧,有什麼事,自然會有人傳話。”
展懷遷辭過嬤嬤,跟上了七姜,新奇地問:“難得,怎麼讓走就走了?”
七姜說:“張嬤嬤教過我,有些話大老爺不方便開口,因為他要威嚴有氣度,所以那幾位嬤嬤就會替他開口。剛剛那幾句,應該就是你父親的意思,他不讓留著,我們就走唄。”
展懷遷莫名有些不服氣:“你就這麼聽我爹的話?”
七姜說:“這不是有求于他嗎,我好歹要在你們家呆兩年,我可不想忍這些個刁奴兩年,你們都不想過好日子,可我想。”
“現在去哪兒?”
“去你父親屋里等著,等他回來說明白。”
七姜說罷,小跑著就往前去,展懷遷不得不叮囑:“黑燈瞎火,你別絆著……”
Advertisement
大晚上的,二公子和夫人突然來等著見父親,不得驚這里的下人,大院里丫鬟婆子極,大多是伺候蕭姨娘的,展懷遷便命眾人都退下,不必有人在跟前。
可是沒多久,懷逸穿著寢裹了裳跑來,說他還沒睡著,要來向哥哥嫂嫂問安。
“誰要你起來了,趕去睡。”展懷遷一派長兄的威嚴,嗔道,“冠不整就來見兄嫂,何統?”
懷逸不敢頂,但見嫂嫂笑瞇瞇的,心里就歡喜,彼此高興地換了眼神,他才趕跑了。
叔嫂之間的默契,展懷遷都看在眼里,不問:“你和懷逸很了嗎?”
七姜應道:“我這幾天都來給老爺請安,弟弟會陪我說說話,一來二去自然就了。”
展懷遷有些不自在,問道:“婚禮那天,你見過懷逸嗎?”
七姜搖搖頭:“一整天蓋著喜帕,誰也沒見著,我第一個見的人,是張嬤嬤。”
展懷遷說:“那就好。”
七姜不明白那有什麼好的,等得有些著急了,沒了耐心,便起在屋子里轉轉。
這里是大老爺臥房的外室,雖十分闊氣,并沒有像侯爵府那樣奢華的擺設,連瓷都是一水兒的白地青花瓷,不像甄家那大花瓶子,五彩斑斕,辦白事都不住的張揚。
“別壞了,你就不能靜著坐會兒?”展懷遷見七姜晃來晃去、晃來晃去,心里明明覺得很活潑可,到了邊卻說,“你在家做針線活,是不是也坐不住?”
Advertisement
七姜白他一眼:“我只是看看,又沒手,也是啊,我一個窮人家的孩子,不配看你們家的好東西。”
展懷遷忙道:“我怎麼是這個意思,是說晚上看不清,你不小心倒了,也不是故意,但心里愧疚,大家都沒意思。你若喜歡,改日讓張嬤嬤帶你去庫房里挑,喜歡什麼,自己拿回去擺放。”
七姜不理他,負手站到門前去,正好明月當空,不過這大院不像觀瀾閣視野開闊,是四四方方,所謂院子不過就是個天井,夜空也自然被框住了。
“大夫人在家的時候,住這里嗎?”
“只住了沒多久,就去城外了,而我更小的時候,全家還沒搬進這宅子。”展懷遷說,“這家里,幾乎沒有我娘留下的回憶。”
七姜問:“你盼著爹娘和好嗎?”
展懷遷走來,一同看向四四方方的夜空,說道:“十年多了,我幾乎不再想,正如你說的,我娘在那里自由自在,并不是個被拋棄的怨婦,何苦強求回來。”
七姜說:“我甚至想過,要是幫你把母親勸回來,你會不會一高興就放我走。可看多了你們家的破事兒,我再也不這麼想了,大夫人要是回家來,天應付婆婆和妯娌,就不會那麼麗了。你知道嗎,我長這麼大,見過最最的子,就是你的母親。”
展懷遷看向七姜,在察覺之前,又將目轉向夜空。
Advertisement
七姜繼續道:“也許因為,大夫人愿意放我走,在我心里就像神。”
展懷遷問:“你不是說,兩年后消了氣,與我相互悉,可能就不想走了嗎?”
七姜說:“這麼一想而已,我可不了你們家的規矩,放心,你若有了喜歡的姑娘,我立馬就把夫人的位置讓出來,絕不耽誤你們。”
展懷遷一臉嚴肅地說:“除了外祖家的表姐妹們,我從不去結識別家的千金,便是自家姐妹,亦是七歲不同席,圣賢書說男有別,不能壞了禮儀規矩。”
七姜聽著不對勁,氣道:“那你怎麼跟我睡一張床,我不是的嗎?”
此時,大老爺回來了,二人上前相迎,展敬忠沒往里走,說道:“這麼晚了,有什麼事明天再說。”
七姜輕輕扯了一下展懷遷的袖子,自己則安靜地站在一旁,展懷遷不得不開口:“父親,我想將朱嬤嬤送回的老家,還有嬸母房里的雁珠,最是挑唆惹事的,也從不把大嫂嫂放在眼里。”
展敬忠看了看倆孩子,說道:“這是眷的務,不該我過問,何況朱嬤嬤和雁珠都是老太太與你嬸嬸最的人,服侍多年,這麼送出去合適嗎?”
“兒子和媳婦都覺得合適,若想家宅安寧,先要攆走這些興風作浪的刁奴。”展懷遷毫不猶豫地回答,“媳婦既然進了門,也該學著料理家務,既然父親說是眷務,那就由七姜做主裁奪,只是多討父親一個示下,也好有底氣。”
Advertisement
大老爺看向兒媳婦,和善地笑問:“姜兒,這燙手的山芋,你愿意接?”
七姜點頭,要裝得穩重些,便只說:“是,我想為您分憂。”
大老爺想了想,說道:“就這麼辦吧,不要鬧得太難看,若外人說我們刻薄下人,會丟了家里的臉。”
展懷遷道:“置幾個刁奴,是府里的家事,與外人并不相干,父親不必多慮。”
這句話本沒什麼,且有理有據,展敬忠卻見兒媳婦突然看向兒子,姑娘眼底那小小的驚喜和意外,已是他這個公爹,看不懂的兒之事。
今晚本是心極差,見了這雙孩子,心里的火氣都散了,笑道:“你們去辦吧,說過多遍,如今已了家,不要事事都來問我,你們該自己做主。”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廢後謀
那年,看見他,仿佛就已經中了她的毒,日日思念不得見,最後她嫁給了他的兄弟,他只望她能幸福,哪成想,她的夫君一登基,就將她打入皇陵守孝,既然如此,他不會在放過與她相守的每一個機會了,就算全天下人反對,又如何,他只要她。
17.4萬字8 9476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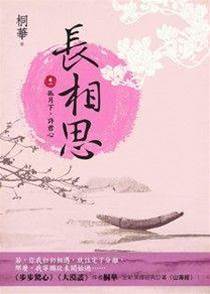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17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752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