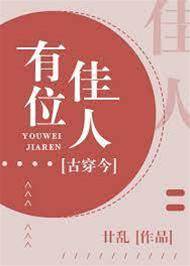《南鄰錦里》 14
吳醞看他不走,又趕他,“你還賴著不走了是吧?”
他扯不過他,丟下一句,“我走了。”氣勢洶洶地出門,正好遇見吳醞他爸,提著兩個三層高的寬食盒進來,“吳叔叔好。”
吳遠亭是個很俊秀的男人,帶著金屬邊眼鏡顯得溫雅秀氣,他生得很白,并不顯老,外面熱,他來得急了,白潤的臉上有層薄薄的細汗,他看了眼方杳安,一貫的溫和,“小安來了,一起吃飯吧。”
他在門口和吳遠亭寒暄了幾句,吳醞就不耐煩地喊,“爸,快來,我死了。”聽起來像個嗷嗷待哺的巨嬰。
他道了再見,和吳遠亭而過,嗅到他上淡淡的,似蘭非草的香,暖烘烘的,很好聞。
他想,其實比起說季正則是媽寶,其實吳醞是爸寶才更恰當一點。
他當天回了家,洗澡的時候,再一次打開放水的龍頭往下澆,一邊擼著一邊沖著,他在一片滅頂的高中,魂飛魄散地想,季正則再不回來,他可能就要求不滿而死了。
開了空調的教室乏悶且人困頓,數學的第一復習無聊頂,他低著頭,躲在一垛書后邊,玩昨天吳醞給他的賓館小卡片,來來回回地折出一道道痕。
冥冥之中,他忽然抬起頭,一眼就看到站了在教室外邊的季正則,他懷疑自己看錯了。
怎麼會呢,不是明天下午才回來嗎?使勁炸了眨眼,再看時季正則還在那,筆直地立著,又高又帥,笑著朝他招手。
他心里咚咚撞,幾乎跳到嗓子眼了,腦子里像有線斷了,“嘩啦——”一聲開桌椅站起來。他口干舌燥,結滾一下,對上數學老師探究的眼神,“老師,我不舒服,要去醫務室。”
Advertisement
說完不等老師反應過來,拿著書包就往外跑,坐在第二座的蘇蓓,過窗戶看見他牽著另一個人的手飛快狂奔,莫名其妙地站起來,往外喊,“方杳安!”
“小安,我們去哪里?”季正則被他拽得顛簸。
去哪里,這個混蛋竟然問他去哪里?
看見季正則那一刻他就了,水流了一子,黏得都著屁了,他現在渾滾熱,火焚,四肢都不協調了,恨不得就地把人推倒。
他們一路出了校門,拐了幾個彎,進了條暗巷,再出來到一條街上,推開了一張老舊黃漬的玻璃門。
他敲響了前臺,“麻煩給我一個大床房。”這是他第一次開房,來的吳醞卡片上說的小賓館,因為,他微微有些夾,臉腮通紅,聲腔啞。
前臺的姑娘在玩手機,見怪不怪地掃他一眼,“份證,押金150。”
他剛把份證抵過去,季正則就把200塊上去了,前臺給他一把鑰匙,十分冷地,“二樓第三間。”
兩個人腳步飛快,上樓梯的時候又牽在一起,他手抖得幾乎不進鑰匙孔,季正則握著他的手,開了門。
這是個仄陳舊的小房間,墻皮染了黃,微微有些發霉的味,讓人心里發悶。他一把將季正則甩到床上,丟了書包,下得溜溜的,也爬上了床。
季正則呆滯地躺著,后腦被床磕了一下,暈暈乎乎地有些震,方杳安解了他的拉鏈,把他放出來,兩分開坐在他上。
用那條細窄的在他還未全的上,方杳安仰著頭,腰部不斷,泛濫的意蹭在他圓的柱上,撐開那條并的,猙獰的柱燙得他屁一一的,紅著臉,像騎著一匹聽話的馬。
Advertisement
他覺得自己上又又熱,像有無數條蟲子在他皮里拱爬,手進上抓,張得圓圓地,陶醉又滿足地,“好熱,唔,好爽。”
他一只手下去,握著那堅全的火,用頭自己充敏的,舒爽得渾哆嗦。
這是真的東西,不是冰冷的涼水,也不是晚上的春夢,又又大的,這是季正則的。
里水潺潺,把那澆得漉漉的,紫黑發亮,筋盤虬,看起來格外滲人。他快活得一刻也忍不住了,用頭抵住的道口就要往里,被季正則急忙拉了一把。
他被拖得撲下來,間熱的坐上季正則結實的腹部,季正則拽著他的手腕,將他拉到前,“現在不能,會把它漲破的。”
季正則把他的屁托舉起來,看了看他泥濘得不樣子的間,那白胖腫,的并著,像一顆飽滿多的鮮漿果,飄出一攝人心神的香。
他惡狠狠地盯著,像一個垂涎已久的兇徒,聲音啞,“我給你松點。”
說完猝不及防地上去,連帶嘬地吮吸著,方杳安的腰一下就了,癱坐在他臉上,逃無可逃,被得丟盔棄甲,又哭又。
那條舌頭卷著他的,干燥的不停磨在他的上,吸得嘖嘖有聲,他瘋狂抖,覺得自己賤的下馬上要化在季正則像巖漿一樣高溫的口腔里。
他一邊哭著,一邊往下頭看,自己扳開了被吸得腫胖的,里的話說得顛三倒四,“好熱,啊,爽,不行了,往里面,唔,好深。”他看見季正則黑亮的眼睛,短刺的頭發,舌頭在他里回來刺,又率直地狠嘬著,像要把他吸干,“舌頭,不要,哦!好爽.......”
Advertisement
季正則按著他的往臉上堆,下半張臉都是他里粘膩而甜的水,舌頭繞著外掃一圈,連他的指尖也沒有放過,嘬著狠吸數次。
一波波急促的失向他襲來,方杳安松了分開下的手,扣住他的頭,下腹搐,渾痙攣,眼淚和唾一起在淌,癡態畢,“不要,不要,我要尿,季正則,唔,不要吸,啊!”他捂住,簌簌發抖,下陡然一松,聲嘶力竭地喊,“我,我死了!”
沒頂的快了所有的力氣,他像一個笨重的機械,遲緩又僵地倒下來,額頭磕在床上,季正則抱著他的腰,把他搐的心食干凈。
他被吮得兩條不停打著哆嗦,眼淚暈了旅館有些不明氣味的床單,意迷地,沉溺在這種污穢的,糜爛的,自甘墮落的里。
這個play有點長,畢竟兩人算旱了兩星期...
等我上完晚課回來改改吧
第二十章
季正則把他抱下來,著他親吻,咸而黏的味在他里發酵,像攙了興劑的毒藥,他舒爽得全戰栗,閉著眼嗚咽。季正則含著他的重重唆吮著,舌頭被吸出口腔,合不攏,唾流滿了他的下。
他的綿綿地大敞著,季正則的冠頭順著他間的來回磨蹭,間或握著沉甸甸的柱狠重地在高腫的上拍打著,那乎乎的每挨一下重的鞭,方杳安就像被電一下,抖著子哭一聲。
他惡劣地方杳安這種茫然的慌措,握著巨碩的,不停在他的上弄著,把方杳安爽得腳趾蜷著床單,渾哆嗦不止,滿口春,“唔,別,好爽。”。
Advertisement
他得意地悶笑了一聲,從方杳安滲汗的額頭下移,他的眼皮,吻他的鼻子,再含著他的輕輕地舐吻,開兩片的花,著方杳安的來回挲,通知他,“小安,我進來了哦。”
說完,下深深一,撐開窄的壁,緩緩到最深,方杳安隨著他的深,提高腰來迎。那東西又又熱,像杵火鐵,把他撐得滿滿的,快要漲開,他這些天積在得不到發泄的,隨著那的釘,全被出外了,他整個都被溢滿,有種充實,下賤的滿足。
“唔,好滿。”他偏著頭滿足地長呼出一口氣,手下去,到兩個人的下,季正則的囊袋又鼓又漲,蓄滿了男。他了把順著流下去的水,全在自己熱的口,嚨里發出急切的念,膛劇烈起伏,“快點,快點。”
季正則沉著聲,著他干起來,握著白細的腳踝把他的提上來,在小上各親了兩下,放到肩上,腰腹使力,在他甬道里一下下狠頂著。
兩片艷的被得翻開,像朵鮮滴的花,熱的襞絞著長的男,像個出不去的套子,一點也舍不得松,又又,直嘬得他筋骨,一渾氣穿過脊梁,只沖后腦。
他被夾得眼前一黑,嘖了一聲,手撐在方杳安兩邊,用力地撞頂,出來時帶出一圈紅的,還纏著他的怎麼也不肯放。
方杳安像連著魂一并被他拔出來了,跟著一起上,手掌捂住自己的,哭得泣不聲,狼狽又下賤地朝他張開手求歡,“唔,別出去,別,進來,我要.......”
季正則居高臨下地看著他意迷的臉,忽然生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扭曲的快意,好像他頃刻間主宰了下這個人的全部,在床上,他讓他哭,讓他笑,他得狠一點他就張著戰栗不止,他拔出來一些他就哭著說我要,那副的樣子,看起來離了他那東西就會死。
他彎下去,含著方杳安水津津的小吮吸著,下突突地弄,在那窄的里大肆驅馳,下瘋狂,把那白花花的屁撞得。
方杳安被得仙死,快頻率的撞頂讓他連呼吸都困難,一句話也說不出口,那火的得又深又兇,輕而易舉進他宮頸,狠撞了數百下,重得像要把他腹腔搗爛。
他流著口水哭得狼狽不堪,指甲掐進季正則的里,“哦,好深,季正則,爛了,唔,爛了。”
心被快速地著,像要起火,他的小翹起來,隨著頂不斷哆嗦,那巨不斷破開他的甬道,次次搗進他花心,他滿熱汗,像過了一遍水,白潤的臉上泛起不正常的紅。
季正則上的汗淌下來落到他臉上,像滴了一顆熱蠟,沉重火燙,在他頰上慢慢膠固。他被縛在兩臂之間,接季正則充滿支配的雄征伐,這種像火一樣燒灼炙熱的,讓他像只飛蛾,盲目的,污穢的,不知恥地投其中。
兇狠的像可怕的刑,一次次無又兇悍地釘進他最的心,又猛又狠,把他靈魂都撞碎了,化了一聲聲溢出口的。他手背上青筋出,梗著脖子,抖若篩糠,“去,要,要去了,啊!”
他哭抖著噴出來,季正則同時把狠狠一撞,滾燙的進他子宮里,又熱又燙,一波波地灌進來,像不完似的。
他們很快開始第二波媾的戰役,季正則躺在床上,讓他坐在自己上,間的自下而上進他膩的里,扣著他細的腰,上下顛。
方杳安含著那尺度驚人的,逃無可逃,腫胖的和季正則下糙的著,又扎又刺,麻得他抖。
他不斷被顛起來,又墜下去,這種殘忍又甜的酷刑折磨著他,他不想離開那任何一秒,卻又實在不堪這種飄空的煎熬。
裹著落下來的一瞬間,他像變了一片薄薄的紙,飄進滿是尖茅的槍林里,頃刻間將他捅穿。他被干得子宮發麻,兩條得幾乎不了了,他哭得慘歷,趴著季正則堅實的膛上不停求饒,“不來了,我來不了了,別來,唔......”
季正則卻把他顛得更狠,雜沓的使他的聲音顯得格外沙,“是你我別停的。”他的手進方杳安的里,繞著舌頭攪弄著,“我當然聽你的啊,小安。”
他那樣親呢地他,下卻本恨不得將他死,猙獰的不斷暴深頂,像要連著他的五臟六腑一并搗爛。
猜你喜歡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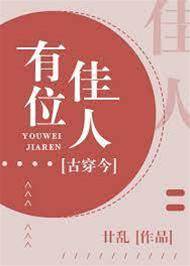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241 -
完結107 章

終于不再愛你
“這一生命運多舛,兜兜轉轉到頭來愛的只剩自己。”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簡雨曾固執、撕心裂肺的愛著一個男人,流云匆忙的二十年,終于有一天,他放下了。 邢青鋒終于明白,當一個人真正心死時,可以拋棄一切頭也不回,再也不會出現。 前期渣到死后期悔青腸攻x前期溫柔后期抑郁受
15.9萬字8.18 10167 -
完結263 章

完了,少將彎了[星際]
當少年發現自己來到未來星際世界的時候,他是有點小懵逼的。 嗯,懵逼程度請參考原始人穿越到現代社會。 現在他成了這個原始人。 還好抱上一個超級粗的金大腿,膚白貌美大長腿的高冷星際少將閣下帶你裝逼帶你飛。 可是大腿想要把你丟在領地星球裏混吃等死做紈絝,還得履行為家族開枝散葉的義務做種豬怎麼辦? “不、用、了……我,喜歡男人。” 絕對是純直的少年挖了一個坑,然後用了自己一輩子去埋。 嗯,這其實就是一個披著星際皮的霸道元帥(少將一路晉級)愛上我的狗血文。 又名《全宇宙都認為是我這個被掰彎的直男掰彎了他們的男神閣下》 每天上班都要在戰艦上被少將閣下強行塞狗糧的部下們一邊強勢圍觀一邊冷笑。 撩了少將大人你還想跑?呵呵。
107.6萬字8 73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