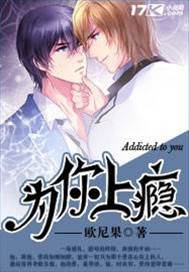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酷丫頭的貼身霸道總裁》 第75章 開學了,他似有些不爽
說到防備,我想,還是要看況。
我不能因為可能的傷害而停下學習,去研究我父親和殷亦桀背後所有的故事,然後排出危險,讓自己安全。
其實,世上又何來真正的危險和安全呢?
如果能麵對和解決,危險,也不在危險。
如果心裏沒有一點兒安全,就算呆在皇宮,大概也是不安全的。
我當然知道,這是在為自己懶惰找借口。可我不覺得有什麽不好。
我們的時間都很有限,一定要用來學習最有用的東西,做最該做的事。
我不知道世上都有些什麽人總想著算計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什麽大的價值值得他們這麽做,人心險惡,我總得為自己活著吧。
“想什麽呢?”殷亦桀端著果放在我手上,問我。
我慢慢的喝了一口,抬頭看看他,搖搖頭。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胡思想些什麽。
有時候累了,就會這樣冥想片刻,然後繼續學習,或者玩。
“是不是覺得那邊才是咱們的家?”殷亦桀在我旁坐下,點了一支煙,沒。
在家的時候,他煙好像不多,或者出去的時候也不多。
他的手總要忙,比如打電腦或者邊打電話邊喝酒,或者,像現在一樣,我的頭。
我想了一下,搖搖頭,說:“覺吧,好像是。”
殷亦桀無聲的笑笑,吸了口煙,慢慢的吐著眼圈,在薄霧中漸漸迷離。
殷亦桀的聲音有些遙遠,說:“那咱們明天就回去。要開學了。離學校近點兒。”
我點頭,不過為什麽他突然變得這麽深沉呢?
似有些不悅。
難道我覺得這邊不太像我家,讓他很為難嗎?
我低聲地問他:“是不是那裏離你工作的地方比較遠,不方便?”
以前他說加班的時候會在那裏休息一下,可他工作哪裏講時間啊,經常想去就去,不想去就在家裏工作。
Advertisement
一兩件事打電話,事多了開電話會議,似乎還可以連著電視,但沒見他用過。
我......也搞不清楚了。
還是因為那邊太簡陋,不像他的宮殿,住在那邊會降低他的份?
殷亦桀繼續吞雲吐霧,但是很慢;呼吸很重,很沉,慢條斯理的理著我的頭發,無聲的笑笑。
殷亦桀說:“沒什麽。咱們住餅去吧。可兒把書都看完了,這個學期也能輕鬆點兒。”
我看看他,搖頭道:“不一定啊,我可以學的更好一點,如果有時間,我還可以看看下學期的書。或者,學點兒別的。或者......如果你忙的話,我可以幫你。”
殷亦桀搖頭笑笑,熄了煙,說道:“做自己喜歡做的。對了......那天電話的事,已經查出來了,我會理的。”
開學,幾家歡喜幾家愁。
我也說不清楚自己是喜還是愁。反正就是變換不同的狀態,稍微有些不適應,也很正常。
不過回家,一定是件高興的事。
拖來拖去,直到報名的時候我們才搬回來住。殷亦桀愁了那一回,覺好多了,和我們回來,看到家裏的一切依舊,有種和我一樣的欣喜。
是啊,回家。打開窗戶,跑到臺,曬著暖暖的春,一切都顯得那麽好。
我們沒在家的時候,工人依舊每周來二次收拾灑掃。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幹淨整齊的家,仿佛一早去上學的樣子。這會兒回來,覺很好。
臥室裏夢之境已經幹淨,襯著臺折進來的,熠熠生輝。臺上綠植了好多,和客廳一樣,隻留下一些別致的,別的都挪走了。
年的氣息淡了些,過日子的覺又回來了。而這種日子,就像夢之境,很幹淨,很安靜。
Advertisement
“不要鬧了,我要做飯。你先出去。”我輕輕的卻是無比堅決地推開那個手腳的男人。
殷亦桀看著我,半天,皺著眉頭,悻悻然離開。
我不知道哪裏又得罪他了。這家夥很有意思,今兒開學,他要送我,所以,又不去工作了。
恕我年,實在不知道他到底做什麽工作的。
就算是個大老板,也不能這麽隨意吧。這年頭,我搖頭,誰知道。除了親媽似乎還能確認,別的,越來越不肯定了。
懶得理他,我繼續收拾。報名兩天,不著急。
先收拾一頓中午的飯菜出來,盛的做一大桌,純當慶賀。
是啊,得好好慶賀慶賀,回到這裏,連空氣都會覺自有得多。
從臥室到書房再到廚房,腳步也是輕快的,心也和一樣好。
春天到了,隻有在這裏,最深刻。
客廳門口的金桔上依舊掛滿紅包,我一高興,就把那張購卡用紅包包起來,送給殷亦桀。
反正是他當家,需要什麽他去買,那麽大額的東西,自然也給家裏統一調配。
嗬,管他,沒準,他也會像玉壺冰一樣,隨手又送了第四者。
餐廳桌子支好,殷亦桀抱著電話扛著本子坐在那裏,辦公。
我無語。
平時我占用書房,他在客廳,也還罷了。
其實我們家書房不小,兩人能坐下。
可這會兒,他......他想做什麽?
監工?
用得著嗎?
我難不還能把夾生的牛吃了,還是把菜沒炒上桌?
偶爾到客廳接純淨水,看一下他,連眼皮都不抬,貌似和我生氣了。
再瞧一眼,他臉很不好看,黑的像鍋底。
當然,不是我家現在這個鍋。這個鍋的鍋底很幹淨,拿鋼球幹淨了估計能當鏡子照。他的臉黑的像農村燒柴的鍋底,很惡!
Advertisement
我回廚房,把菜刀放在隨手可及的地方,不怕他!
他家在那邊,這邊是我家,生氣就回去。
仔細想想,他究竟生什麽氣呢?
到底是為什麽呢?
我慶祝搬回來,他不樂意?
不知道緣故。還是我在弄冰箱裏存著的剩菜,讓人不高興?可我說的實話,他真的很敗家,以後不容許他在我家腐敗。糟蹋糧食食,是要遭雷劈的。
別以為有幾個錢就看不起不值幾個錢的米飯胡蘿卜,的時候管用著呢。而且......哈喲,不告訴你一回你未必相信,聽了準嚇一大跳。
就在玉壺冰家吃那一會年夜飯,桌上自然都是玉氏年青一代太子公主們。食是很盛,不過他們都隻取被自己吃的分量,弄到自己盤子裏就要吃幹淨,一樣沒吃完絕不下一樣。那吃相,既優雅又覺很有涵養。到最後吃飽離席的時候,誰的盤子都不會有剩餘的食。
當時沒太在意,為殷亦桀擔心。後來回家吃了幾回飯才發現,真的非常難得。比如我吃青菜吃葉子,吃蒜苗不吃蒜頭,所以多多會咬一些剩下來。殷亦桀更是,蔬菜稍微老一點不吃,黃的不吃,焦了也不吃......雖然最後盤子裏幹淨,但碟子裏會剩好多。
所以,今天回到自己家,我第一件事,就是不許扔掉那些還很新鮮的菜。當時就收拾好放在冷凍室,這會兒拿出來,一解凍,和新鮮的沒什麽區別。
再瞅瞅某人的臭臉,決定,不理他。
沒想到,他還能耐,午飯是吃了,紅棗羊脛骨糯米粥也喝了二大碗,但就是臭著臉,不和我說話。
舒服也不知道他家的爺發什麽脾氣,沒敢惹他。
我也不理他,吃完飯人洗碗,我去書房整理寒假作業,下午報名的時候了,完任務。
Advertisement
站在沙發跟前,我背著書包,提著袋子,看著他。
早起還高高興興的要送我去報名,這會兒還早跟電腦較勁兒,我看著他,看他要不要送我去,還是讓別人送我,或者我自己去。
自己去?自從被他監護,我還沒自己出去過,好像也沒在清醒的時候自己回來過。
看來還蠻有挑戰的。不知道我要不要問他一下,還是繼續等他安排。
殷亦桀低著頭,不理我,我就站著,不想走。反正明天去也不晚,我等著他決定。
過了大概一刻鍾,他回了有二三十個郵件,準備喝茶,抬頭,然後看見我,眼裏有些驚訝。
我兩眼衝天,笑。
他的眼睛太會說話,我都知道了。
他自己下不來臺,就裝,還像。
“要去學校了?”殷亦桀額角,問。
他現在的意思是他很累,才停下來,是疑問句,純屬無心,需要我回答。
我......抿著,點點頭,我想還是配合一下,否則他更下不來臺。
不過,看樣子他,隻是不想弄得太尷尬,心裏可沒放開,我還是不知道他在生什麽氣,因此無從勸解和認錯。
“舒服呢?”殷亦桀點點頭,不時看看電腦,新郵件不停的提示,看來真的很忙。
我更弄不懂狀況了,就這麽大屋子,他找舒服向來喊一聲就是了,或者似乎有種特殊的氣息,隻要他想到,舒服就會出現在他跟前。
今兒......看來是他的問題,連舒服也沒出現在他眼前。
我瞄了瞄,舒服在我臥室,正在對著線小心的拭水晶,保持它們最晶亮的狀態。
“......”殷亦桀回了個郵件,抬頭,氣惱的看著我,臉要多臭有多臭。
傳說,男人,和人一樣,每個月都有那麽幾天,焦躁、易怒、甚至不講理。
以前很和殷亦桀連續相這麽久,還真不知道。
不過,他......生氣起來是很可怕的。
但,也沒這麽,這麽......
就是有點孩子氣,像是在跟誰賭氣,讓我覺怪怪的。
我實在不知道自己哪裏做錯了,得罪了他。
不過,我才是孩子麽,他賭什麽氣?
還是真的生氣了,又不想讓我難堪,所以做出這副樣子?
百思不得其解,我想,還是算了吧。
這個問題,我不是太有興趣知道,總覺得如果他想說,自己就會說的。
如果不想說,非要我上去,那麽,至今為止,我還做不到。
這種覺有時候很奇怪。就像當初我很想回家,他不肯。
我猜測如果我上去,撒,或者堅持,或者再采用一些更加低俗的手段,他可能就同意了。
但是,我沒有人的習慣。
就算心裏再想,我也做不出來。
委曲求全是一種不錯的品質,不過我是不會擁有了。
因為我知道,很多時候就算你很委屈,也未必能全得了。
更多的時候,當你委屈時,就已經碎了,何來的全?
除非遇到反派威利要我供出地下黨名單,或許會考慮一下委曲求全。
否則,很多時候,這種英雄氣節會演變曲意奉承,往往得不償失。
其實我和殷亦桀之間還沒這麽嚴重。不過我就是做不到。
小時候沒吃的曾求過人,然後就是白眼和施舍般的丟出來點兒吃的。
我甚至連富人的寵都比不上。從那時候開始,我就失去了撒的潛質和委曲求全的YU。
我的耐心和忍耐,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養的。
這麽多年,隻有加強的趨勢,沒有削弱的跡象。
對富人,我不敵視也沒任何好。
所以,殷亦桀如果對我甩臭臉,我絕對不理他。
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到底和別人不一樣,我不求他,但也不會甩袖而去。
麵對他的臭臉,我抿了下,
不知道該怎麽說,隻能繼續安靜的站在那裏,等著,他的下文。
殷亦桀有些氣惱,過了一會子,才著額角對我說:
“讓舒服送你去。我還有事。”
他的口氣勉強能聽,臉也變了許多,雲布改多雲。
不過我可不想再看他擺臭臉。
書包很重,因為還有借來的下學期的書。不過我覺得需要一些抑把我的心實。
舒服抬頭看看我,眉心微皺一下,顯然沒料到會發生這種狀況。遲疑了二秒鍾,停下手裏的事兒,過來拿著我書包,提著袋子,給我一個安的眼神,然後我們出門。
殷亦桀繼續埋頭工作,一會兒電話就響起來,他嚴厲的指責、冷酷的下令,比對我還厲害。
可能他真的有事兒吧。站在電梯裏,我抿著,想。
其實也是,他在家陪我十多天,雖然工作不斷,但哪裏比得上去現場理?
有許多事說的一個樣做的一個樣,當麵一套背後一套,他應該比我清楚。
現在我要上學了,他,是不是也該給自己解放了?
或者該進另一場戰鬥了?
這麽說起來,似乎是我關心他不夠。哪裏有一個大老板老總在家關上十來天的?
他好像都是為照顧我,可我不知道為什麽。
不過,他的臉也徹底好了......
恩,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臉破相,覺得丟人,不想出門;卻編了個理由說陪我、做寒假任務。哼,差點兒被他蒙蔽了。倒是說的夠冠冕堂皇,卻是為自己。
害得我一廂願以為有人真這麽疼我,所以留在家裏。
可見得,腦子不多轉轉,要吃多大的虧。
坐在舒服的車裏,我很快就緩過來,不理那個口是心非口腹劍的家夥。
他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我搞不過來。
而且,他自己好像也覺得不妥,想找臺階下,我等著他好了。
學校裏人好多,學生和家長摻雜其間,比平時能多上一半。
舒服從側門開進學校,停在教學樓前。那裏還停了幾輛車,大概是剛開學報道的關係吧。我沒多想,反正在學校裏麵下車我也習慣了。
一大書包一大袋子,舒服幫我提著,去辦公樓找班主任。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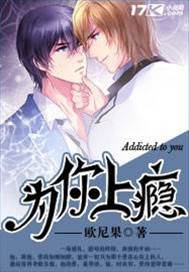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6931 -
完結2513 章

前夫請彆念念不忘
離婚前——阮星晚在周辭深眼裡就是一個心思歹毒,為達目的不折手段的女人。離婚後——周辭深冷靜道:“如果你反悔了,我可以考慮再給你一次機會。”阮星晚:“?”“謝謝,不需要。”
211.8萬字8 93746 -
完結268 章

心肝,別不要我了好不好
初遇時,你是南邊寒冷中的笙歌,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治愈著處于地獄的我。七歲的南笙在寒冷的夜晚撿到了巷子角落里的殷寒,向他伸出了白皙溫暖的手,她說的第一句話:“小哥哥,你好好看呀!愿意跟我回家做我的老公嗎?”殷寒不知道的是當他握住那寒冷中的那抹溫暖的時候,他命運的齒輪開始了轉動。南笙帶殷寒回家八年,六年里每次叫他,他都說我在,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后面的兩年里,她卻變了,一次又一次的滾,你好臟,你別碰我都 ...
48.7萬字8 26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