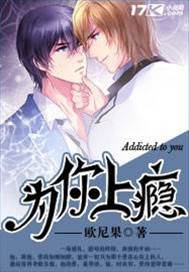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酷丫頭的貼身霸道總裁》 第76章 開學了
我趕拿穩筆記本,手。
心裏掠過一影。
我的本子就在手上,還來拉,是三角眼無視還是故意?故意又是想做什麽?戒備的看著,搖頭,不想理。
自從殷亦桀的事後,經他那一番提醒,還有冉樺提到苗苗寒假約我逛街,我對什麽都更加敏。就連以前毫不在意的事,也能留心起來。比如剛才發現舒服的異樣。這個世界太難以捉,所以我們需要多個心眼,時刻提防。
提防和簡單的懷疑不盡相同,但也有些相似。我戒備的看著苗苗,希能和我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否則我不能保證不自衛。兜裏的刀子一直都在,惹了我會發飆的,相信我。
“走走,出去走走,請你吃甜不辣。寒假給你打電話,沒人接,躲得真牢。聽說你生病了,本來還想去看你的,又怕你家門檻高,進不去。”苗苗對我的戒備視無睹,拉著我胳膊,覺想念我很久了。臉上的笑容很明,仿佛借來春二三鬥,看著很舒服,很刺眼。
我搖頭,趕把本子收好,調整狀態,至三級戒備。
對於的如此熱,我非常困。說實在的,我沒有一點兒好,相反,覺得擔心。
和苗苗這種人往,以前還罷了,但自廖亮的事之後,我就知道,沒那麽簡單,卻也著實太簡單。
的心思,其實表的很白,稍微一用心就能看出來。
或者也不能怪簡單,可能是我對這類的見多了,所以,駕輕就,我心裏有譜。
和殷亦桀比,要看懂想做什麽......嗬,我忽然覺得好笑,真想謝殷亦桀給我的教育,全麵,實用。
“走吧,這會兒又沒事,小花園裏迎春開的可好了,咱們去照個相,回頭放到博客裏,點擊一定高。”苗苗搜腸刮肚,極力要把我連遊說帶綁架的弄走。
Advertisement
“我還要開班會。”我冰冷的瞅著,心裏有些無奈,當著這麽多同學,我還不能太過,否則,對我更不利。
人之,是個很可笑的東西,有時候。
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了路。
經典名言。存在即真理。現在換個說法,其實也是真理。那就是:世人本來都很無,裝的人多了,也就了人。世上本無此事,說的人多了,便了真事......
“班會有什麽要,聽不聽都那樣,個班費,發個書,不就完了?”苗苗嘟起菱,不以為然,手下用力,準備拖我。的眼裏,有種堅決,出賣了的熱。
我在想辦法,如何擺,又能稍微顯得不那麽不近人。
我甚至無法悍然推開苗苗,然後大吼一聲。就算我有一百二十個理,隻要我強悍,那就錯了。可磨纏我很不耐煩,還不像殷亦桀,會很客氣很禮貌的和我比耐心;而是直接上手,像街頭賣白菜的潑婦,讓秀才很難對付。
這會兒想想,我的監護人確實夠難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堅持,要客氣的讓步和容忍對方,有時候很難。但他昨天就表現的很不錯,今天......就太勉強了。不過我是不是也太強了,一點兒沒考慮他的?那也不行呢,我還小,要我像主持那樣哄他,耶,我吐!
扭頭四顧,我想看看有沒有柱子,可以一頭死;或者有沒有地,讓我鑽進去,從此離遠遠的。其實我也不是不可以揍,但總覺得這樣會讓人愈發坐實對我的猜測,進而影響我本來就不大好的形象並破壞殷亦桀的教育之功勞。
看,我多偉大,都被如此糾纏了還為他著想,死家夥,竟然還在家生我氣,鄙視!
Advertisement
眼角餘看到,冉樺正在一旁有意無意的和趙昀嚼舌,趙昀有些不樂意。
我沒理,繼續想折,一邊應付:“你有什麽事兒嗎?我走了,誰替我班費?”
“請你吃東西,不是事兒嗎?”苗苗愈發抓住我胳膊,準備生拉拽。
“一會兒還要選班幹部。去年大家不認識,選的班幹部有人不滿意,要改選。”趙昀蹭到我們跟前,臉不是太好看,話也說得很生。
呃......嗬......有意思。大人玩深奧的遊戲;我們玩淺顯的把戲。就是不知道,為什麽又牽扯上我。如果我姓香,一定會當自己是餑餑;如果我姓唐,一定會當自己是僧。
挑挑眉,看著苗苗,等著退場。對於趙昀,我現在還不知道該怎麽謝。不過他能開口,我還是非常激的。至讓我不太難看,就算一會兒吵翻了,也不太失人心。
嗬,人心......人心正在四周的角落裏嘀嘀咕咕各自寒假的趣事,一邊兒用眼角切關注我這邊的事況。我突然覺得,人一旦得到了些什麽,或者過的幸福了,就會有忌諱的東西,比如這無厘頭的從來沒對我好過的人心。真要被這虛無的東西束縛手腳,我還活不活了?
想到這裏,我臉冰冷,用力而堅決的推開苗苗,和人心。
“妝可人不會想當班幹部吧?一票有什麽要?”苗苗不樂意的看著趙昀,反駁,一邊手拉我。看著我數九寒冬臉,鼻孔微微嗤笑一下,又趕掩飾。
我白了一眼。我的一票也是一票,你說不要就不要了?誰要你替我做主?
“我想。我需要的一票。”趙昀紅了臉,麵紅耳赤。顯然是初次說謊經驗不足,連口齒都不大伶俐。說完看著我,問,“你會投我一票嗎?”
Advertisement
呃......太狗了!
我暈死,趙昀的演技太差了!要不是在幫我,估計我會笑場。看看他認真的表,我覺得,這一票,在他和苗苗中間,我顯然應該投他。這也太明顯了。
唯一讓我到疑的,就是冉樺為什麽不出麵,是他覺得和我關係不足以與苗苗抗衡嗎?
還是有別的緣故?
又或者,像上次一樣,他勸我,別和苗苗出去?
也許,我似乎該接他的好意,想方設法別跟苗苗出去。
還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和苗苗出去一回,看看到底有什麽危險,或者究竟是誰在故弄玄虛?
我現在大概能猜到苗苗應給無好意,但不能確認冉樺究竟何意。
嗬,我很能相信誰,因為沒有誰會無緣無故的幫別人,甚至不惜冒犯其他人。
見到殷亦桀和布萊恩之後,我更覺得有些人指不定就有極複雜的背景,很多事都不能輕信。
但不論如何,現在,我更不相信苗苗,所以,決定不出去。
對趙昀點點頭:“我選你。”
趙昀本來就紅的臉,現在整個是......興的兩眼發亮,差點兒跳起來,剛才的鬱沒了。
“妝可人......”苗苗似乎看到失,非常不願意、不忍心。
“我們要開班會了,你不介意旁聽吧?”我冷冷的看著。
我們班的同學,剛小斑了一下,很快冷靜下來,頭接耳、竊竊私語。
苗苗非常不甘心,左顧右盼,眼裏狠毒一掃而過,非常好心的看著我,低聲音勸我、剛好讓大家都能聽見:“你已經有了殷總,怎麽還可以和別人好?這樣對你和別人都很危險的。他們那種人,最不喜歡自己的人在外麵勾三搭四,一旦鬧起來,你怎麽辦?”
Advertisement
“啪......”我很利落的甩了一掌,冷冷的盯著,一個字兒都沒有。
所有人都看著我,我收到他們探究和嘲弄的目,不想理。
苗苗也愣了,過了好一會兒,嗚嗚咽咽的哭出來,泣道:“你這種孩,從小沒個人教你,將來長大了一定會吃大虧的。我好心和你說,你竟然......算我白費心了......”
我很想再甩一掌,因為果然如我所料,在煽,然後讓所有人都以為,我惱怒、做賊心虛。但我不能,因為再打,我真的會辜負所有對我好的人,玷汙他們的名節,讓人以為我真的很沒教養。所以,我隻能吃下這個啞虧,冷冷的看著:真讓我失!
不過我腦子還沒那麽暈,我很好奇:為什麽這麽對我?我們曾經的友誼,竟然一文不值?
苗苗說完話,發現我沒有毫悔改的意思,反而眼冷得能凍死人,隻好嗚嗚咽咽走了。
我不覺得那一掌有多痛,如果說痛,也許我心裏比還痛。但哭的那麽哀傷做什麽?上次和流氓打架,也沒怎麽喊痛,所以,的用心......
我搖頭,無語。
“妝可人,你......”冉樺站在我前,眼神鬱,不複剛才的熱。
我繼續搖頭,無語。
“別理。我一會兒告訴你。”冉樺非常輕微的說了一句,就到講臺前,那裏正在發書。
暫新的課本,散發著濃鬱的墨香,有種含蓄的優雅。
這世上,能到的氣質已經不多了,能品讀的底蘊更。到都是虛無的浮華,帶著低劣的奢靡,也許不用多久,就能侵占整個世界。因為課本裏,錯別字也漸漸多起來,各種各樣的疏,在手可及的地方。甚至還有個堂而皇的名字,“時代”。
不知道,我們的時代,到底想讓我們到些什麽?還是我未老先衰,在我父親和母親的畸形教育中,以及我的喋喋不休中,過早的離了時代?
當然相對說來,我還是比較喜歡課本,尤其是嶄新的課本。相對於同學、相對於環境、相對於別的地方幾乎滅絕的文化來說,我,選擇課本。這也是我整個寒假都在家看書的原因之一。
捧著厚厚的一摞書,回到自己坐位,慢慢的挲,借這種,平息心頭的點點煩躁和不安。
猜你喜歡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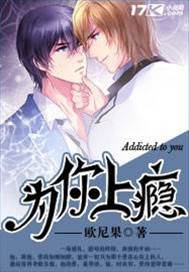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6931 -
完結2513 章

前夫請彆念念不忘
離婚前——阮星晚在周辭深眼裡就是一個心思歹毒,為達目的不折手段的女人。離婚後——周辭深冷靜道:“如果你反悔了,我可以考慮再給你一次機會。”阮星晚:“?”“謝謝,不需要。”
211.8萬字8 93746 -
完結268 章

心肝,別不要我了好不好
初遇時,你是南邊寒冷中的笙歌,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治愈著處于地獄的我。七歲的南笙在寒冷的夜晚撿到了巷子角落里的殷寒,向他伸出了白皙溫暖的手,她說的第一句話:“小哥哥,你好好看呀!愿意跟我回家做我的老公嗎?”殷寒不知道的是當他握住那寒冷中的那抹溫暖的時候,他命運的齒輪開始了轉動。南笙帶殷寒回家八年,六年里每次叫他,他都說我在,但是他不知道為什麼,后面的兩年里,她卻變了,一次又一次的滾,你好臟,你別碰我都 ...
48.7萬字8 26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