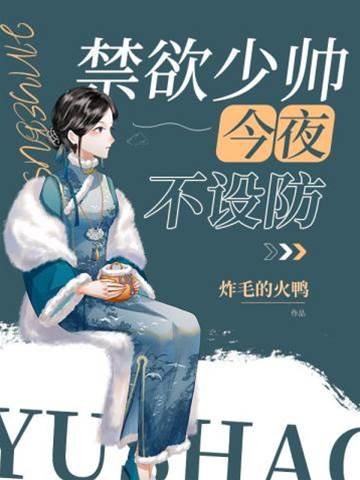《藺先生一往情深》 第94章 094.手指上的血,不是第一次
天不喜酒吧這樣的地方,除開本喜靜,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
太過嘈雜的環境,容易令到不適,來自的。
如果說以前是個人喜好原因,那麼,自從兩年前之後,更多是為了自己的而不踏足。
腦子嗡嗡作響,太又脹又沉,閉上眼,彷彿天地都在轉。
好在洗手間隔音效果不錯,自門合上,裡麵安靜得可以讓人神暫緩。
一晚上連著穿梭好幾個酒吧尋找沐堂,那些逐漸升起的不適都暫且被下,但或許是極限了。
在門外撐著與沐堂通時,以為清寒的夜風能減輕的不適,卻不曾想,隻是讓更難而已。
不想讓他們擔心,所以冇有表現出任何的異樣,強撐,也隻撐到洗手間的門關上。
噁心乾嘔的覺持續了好一會,什麼都冇能吐出來,但總歸是下了一些,擰開水龍頭要掬水洗臉。
Advertisement
一個拿著清潔用的阿姨正要離開,看到鏡前的子模樣素雅,不像是酒吧常客,便問了句:“小姐,還好嗎?”
天對輕輕點個頭。
待清潔阿姨剛走,低頭,潔白的洗手池盆裡,清澈明的水流中,赫然落一點紅。
暈開的明豔紅,瞬間隨著水流不見了,彷彿隻是燈影投在眸中的斑,是幻覺。
天鼻下微,似有鼻水流下,怕不是夜風吹多了冒又犯。
手指抹掉的同時,抬首看麵前寬大的鏡子,燈下白皙到幾近有些明的小臉,鼻下卻是一片約淡淡的紅,而手指上,是粘稠未乾的跡。
一滴,兩滴,白瓷盆潔淨,襯著那滴落的點點,像是盛開的一朵朵紅小花,頃刻就消散了。
看著水池裡,怔了片刻。
幸好此刻洗手間無人,不然彆人該是投以多訝異的目?
Advertisement
角牽起似無奈的一笑,從旁了張麵紙,在鼻下,微微仰起頭。
如此平靜從容,毫冇有初初見的心慌……仿似,已經不是第一次。
等待鼻止住的時刻,閉著眼,濃黑的羽睫偶爾微,在影裡停佇極細的微塵。
鼻一流,頭變得更暈,天靠著鏡邊的隔斷牆,背對了燈,隻能用呼吸。
不知過了多久,手裡換過兩次的麵紙上,紅漬不再目驚心,想是止住了。
纔對著鏡子洗了把臉,仿若無事一般推門出去。
向添就等在不遠,冇差幾步就要走到時,旁側暗一道影卻攔下了的去路:“沐小姐——”
天狀態不好,流轉閃爍的五彩影裡,勉強看清麵前的人,正是早前出現在包間裡,最先了手的餘力。
“藺董請沐小姐移步,說幾句話。”
他的語氣很客氣,看向側門的方向。
Advertisement
天本拒絕的話到邊,眸黯了黯,沉默邁步往側門去。
向添轉頭看到了,似乎要跟上,看向他,對他搖了搖頭。
……
出了側門,穿過一條花圃小徑,有幽香隨。
再往外走,安靜的馬路段,夜下,靠邊停著一輛黑的卡宴。
猜你喜歡
-
完結558 章

隱婚老公太神秘
傳聞榮家二少天生殘疾,奇醜無比,無人願嫁,所以花重金娶她進門。而結婚兩年她都未成見過自己的丈夫,還遭人陷害與商界奇才宋臨南有了糾葛。她陷入自責中,宋臨南卻對她窮追不捨,還以此威脅她離婚。她逃,他追;她誠惶誠恐,他樂在其中。直到她發現,自己的殘疾丈夫和宋臨南竟是同一人……輿論、欺騙、陰謀讓這段婚姻走到了儘頭。四年後,一個酷似他的小男孩找他談判:“這位大叔,追我媽的人排到國外了,但你要是資金到位的話,我可以幫你插個隊。”他這才知道,什麼叫做“坑爹”。
98.8萬字8 106431 -
完結10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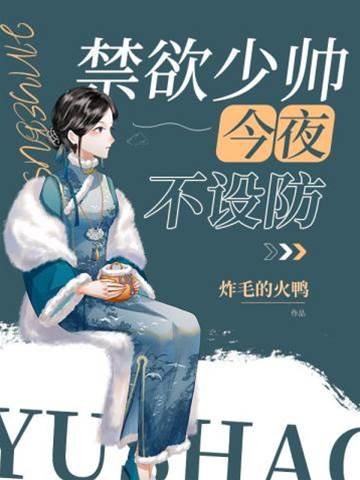
禁欲少帥今夜不設防
一朝身死,她被家人斷開屍骨,抽幹鮮血,還被用符紙鎮壓,無法投胎轉世。她原以為自己會一直作為魂魄遊蕩下去,沒想到她曾經最害怕的男人會將她屍骨挖出,小心珍藏。他散盡家財保她屍身不腐;他與她拜堂成親日日相對;直到有一天,他誤信讒言,剔骨削肉,為她而死。……所幸老天待她不薄,她重活一世,卷土而來,與鬼崽崽結下血契,得到了斬天滅地的力量。她奪家產、鬥惡母、賺大錢,還要保護那個對她至死不渝的愛人。而那個上輩子手段狠戾,殺伐果決的少帥,現在卻夜夜將她摟在懷中,低聲呢喃:“太太救了我,我無以為報,隻能以身相許了。”
193.2萬字8 20524 -
完結141 章

錯嫁瘋批老公後,我直接帶球死遁
夏鳶穿進一本瘋批文,成爲了下場悽慘的惡毒女配,只有抱緊瘋批男主的大腿才能苟活。 系統:“攻略瘋批男主,你就能回家!”夏鳶笑容乖巧:“我會讓瘋批男主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瘋批男主手焊金絲籠。 夏鳶:“金閃閃的好漂亮,你昨天給我買的小鈴鐺可以掛上去嗎?”她鑽進去一秒入睡,愛得不行。 瘋批男主默默拆掉金絲籠,佔有慾十足抱着她哄睡。瘋批男主送給她安裝了追蹤器的手錶。 夏鳶:“你怎麼知道我缺手錶?”她二十四小時戴在手上,瘋批男主偷偷扔掉了手錶,罵它不要碧蓮。 當夏鳶拿下瘋批男主後,系統發出尖銳的爆鳴聲:“宿主,你攻略錯人了!”夏鳶摸了摸鼓起的孕肚:要不……帶球死遁?
26萬字8.18 28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