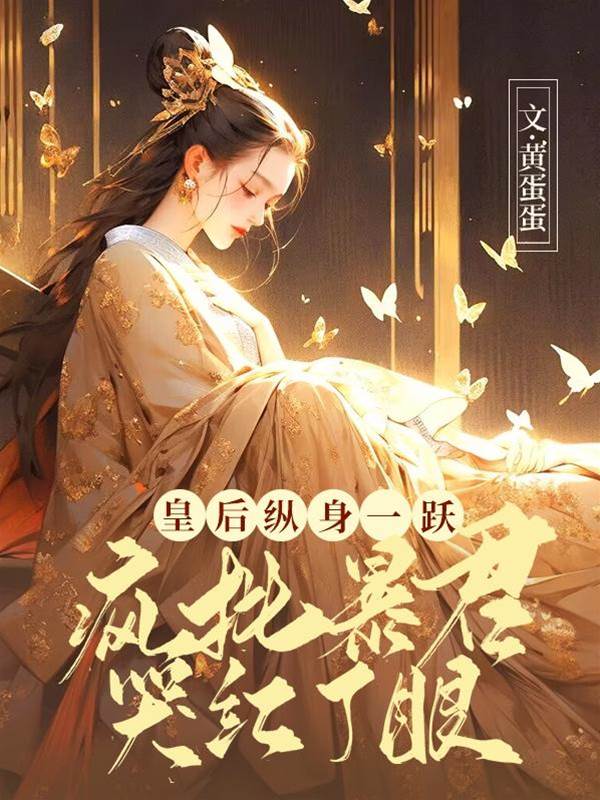《重生之庶女歸來》 第6章 錦衣衛斗山道
這些人從著氣度到言談行止,與其說是「差」,倒不如說是「錦衛」更恰當些……何當歸的背後冒起一層薄薄的冷汗,幸好剛才沒再和真靜談論過林中的傷者。心念百轉之間,何當歸搖頭道:「回爺的話,我二人並未見過您口中的重犯。之前民不知爺份,狂言造次,還請爺莫怪。」真靜也忙點頭附和。
「哦,既然如此……」緋男子略一思忖,灑然笑道,「不知二位姑娘在哪個道觀清修,能否引我們過去看看?」
何當歸聞言惶然低下頭:「回爺的話,適才民不慎扭傷了腳,行遲緩不便,怕會耽誤爺的腳程。您要找的道觀名喚『水商觀』,就在山道的盡頭,只好請爺自行過去了。」
緋男子見談吐大方,聲音婉轉悅耳,不由得產生了親切,攀談道:「普通子見了差,大多都會臊的口不能言,怎麼你小小年紀,看到我們非但沒有畏懼,還能這般對答如流呢?」
何當歸垂頭微笑:「爺抬舉了,其實民心中對爺也是又敬又畏,完全是鼓足了勇氣,才能堅持說話到現在。」
「哈哈,我頭一次見像你這樣有趣的小丫頭。」緋男子失笑道,「你說你的腳傷了,那走路一定非常辛苦吧?反正我們同路上山,不如我背……」他後的黑男子突然發出一聲響亮的咳嗽,毫不掩飾地打斷了他的話。
何當歸平靜地了他們一眼,不著痕跡地解圍:「山中天氣多變,暴雨說來就來,到時會加大搜查的難度,各位爺何不儘快起程?」
黑男子聲道:「這位姑娘言之有理,段七,區區一個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你也不懂,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說完拂袖而去。何當歸方才發現,不知何時前面那些人全都走了。緋男子尷尬地揮手告別,慌忙抬腳去追前面的人了。
Advertisement
瞧見他們走遠,真靜略鬆了口氣,剛想要張口說什麼,卻見何當歸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頓時瞪大眼睛,用雙手捂住。
段曉樓幾步追上前面的人,沒好氣地對黑男子道:「喂!姓高的,在人家姑娘面前,你好歹給我留點面子!」
高絕冷著臉不說話,陸江北見狀,笑著打圓場道:「好啦好啦,大伙兒走了一天都乏了,怎麼你們還有心鬥氣!」說著,陸江北前一步走到兩人中間,隔開了這對鬥氣冤家。
廖之遠嘲笑道:「我看曉樓是老病又犯了!我對他真真服氣,他的關懷對象,下至十幾歲的小妹妹,上至四十幾歲的大嫂子,比大殿上那尊歡喜佛還博……」
「死山貓,你打住打住!」段曉樓揚手推了他一把,「人家是清清靜靜的出家人,又不曾得罪過你,幹嘛在背後這樣編排人家!」
廖之遠「撲哧」一笑:「段小將軍,你哪只耳朵聽見我提了?我說的是蓮兒姑娘和娘!反倒是你,一定是見人家生得漂亮,生出了非分之想,轉頭又遷怒於我,這卻是何道理?」
段曉樓越聽越急,大喝一聲,飛出一腳就向廖之遠的下盤踢去。
廖之遠一邊跳著腳躲到高絕後,一邊咧著大笑道:「可惜那道姑的年紀也太小了點兒,領回家就只能當妹妹了。不過敢問段兄,你這次下揚州已經尋了幾位妹妹了?那輛赤蓬馬車還能得下嗎?」
段曉樓俊臉漲紅,拳腳上立時了真格的,口中為自己辯解道:「我講過很多次了,那個雪娘世可憐,被相公賭錢輸給了醉香院,抵死不從,被那混蛋打得遍鱗傷,一心要投河自盡,我看不下去才出手相救的。而那個蓮兒更令人同了,父親死後就被的叔父霸佔了家產,和娘只能在煤窯里挖煤討生活,那混蛋還打算將賣給一個老頭子做小妾,我看不下去……」
Advertisement
「所以,段大你就把們母倆照單全收了!」廖之遠替他接著說道,同時探手把高絕拉到前當盾牌,化險為夷地擋住了段曉樓的一招「有來儀」和一招「烏龍擺尾」。
高絕正好端端低頭走自己的路,卻無緣無故被一陣拳風掃到了鼻子,立刻就像被點著的炮仗,左拳橫打廖之遠的下,右腳斜掃段曉樓的後腦。段曉樓夷然不懼,變指為掌,接招的同時,仍不忘繼續教訓罪魁禍首。
於是,廖之遠兩面敵,口中大呼不公平,轉頭朝其他同伴看去。被他眼瞄到的人,紛紛大笑著躲避到山道兩側,毫無同心地拒絕提供援手。
「喂,蔣邳,我上個月才救過你一次!你不懂得什麼知恩圖報嗎?」廖之遠厚著臉皮,討起了人,「小子,現在你報恩的時候到了,快來幫你的救命恩人我!」
沒想到,蔣邳閑閑挖著鼻孔,無恥地反問道:「你不懂得什麼施恩莫報嗎?」
廖之遠氣炸,因這番對話分了神,他腳下的步法了路數,差點兒被高絕的鐵拳到,連忙一個晃,僅以一毫之差避過。這樣幾十個回合下來,段曉樓終於一掌打在了廖之遠的小腹上,而他自己又不幸被高絕的大腳給踢飛——戰局最終以高絕的勝出而結束。
段曉樓側飛出幾丈,撞歪了一棵大楊樹,仰倒在地。他的眼睛卻仍瞪著廖之遠,憤慨道:「以後不準你再扯這件事!我只是為救人而救人,無關風月,本就不像你想的那樣!」
廖之遠被揍得那一記也不輕,他捂住小腹,皺著臉說:「你大爺的,真不逗,隨口說說你就急了!我又沒有一個待字閨中的妹妹要嫁給你,你急地沖我解釋個什麼勁兒啊!再者說襄王無夢,神可未必無心,那蓮兒瞧你的眼神,連瞎子的骨頭都發,難道你渾然不知?這樣下去,只怕你永遠都討不到夫人了……瞧瞧瞧,每次一說這個你就黑臉!哎呦呦,疼死小爺了……算了,真是懶得說你了。」
Advertisement
原來,這段曉樓雖然家世不俗,但無論段母如何努力,都不能給兒子定下一門門當戶對的親事。但凡是王公府第家的兒,甚至包括庶,都不肯與段家議親。
而段家的門第,又不是一般小門小戶的子能進去的。畢竟,段曉樓是家裡唯一的嫡子,將來的妻子定然要找一個能撐門立戶、掌家理事的,小戶之總歸底氣不足,難登大場面。因此段曉樓的婚事一直被擱置,直到二十三歲還是獨行俠,為段母的一塊大心病。
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段曉樓的天中對子有一種特殊的,每每只要瞧見了子在苦,便立刻按捺不住要去「解救」。如今經他的手「解救」的子,沒有一百也有八十,這些弱子全被他帶回了家,安排在段府的各個院落里做工,安排不下的就送去段記的綢緞莊、錢莊和酒樓。
雖然段曉樓對這些子只是寄予無限的同,並沒起別樣的心思,但那些被他帶回家的子,卻未必不解風。於是三天兩頭的,這個送綉帕、鞋墊,那個贈香囊、腰帶,這位走路時「剛好」暈倒在他的腳下,那位看見他經過荷花池就「意外」落水,驚慌地掙扎呼救……凡此種種,段母屢不止,於是整個應天府的高門府第,漸漸開始流傳段家公子的風流事跡。
自從段曉樓名聲大噪之後,就再也沒有哪位公侯小姐願意嫁給他了。畢竟為子,乍一聽聞自己尚未過門,就已經有一支極為壯觀的「敵大軍」在等著自己去「消滅」,膽小點的嚇得心肝兒都了。所以,人家寧可委屈自己地嫁給一個老男人做填房,也斷斷不敢做他段家的媳婦。
而段大本人不知是真傻還是裝傻,不但不去設法修補一下損的形象,還在以平均每月四五人的速度,孜孜不倦地給未來媳婦添「敵」,同時也很不孝地為自己母親的「議親大業」增進難度。
Advertisement
其實平心而論,也不能怪那些被拯救的子得寸進尺。試想,哪個子能對一個救自己於水火的男子毫不心?何況,那人還是一個俊無匹的翩翩年郎,年有為的貴公子。們都相信誠所至,金石為開,所以堅持不懈地用自己的「繞指」去化「頑石」。
「夠了!再吵吵天都黑了,我們是來查案,又不是出來遊山玩水的。」高絕冷冷道,「段曉樓,如果你把那些七八糟的心思多放幾分在案子上,又何至於放跑了最重要的線索!」
不等段曉樓作出回應,陸江北又忙不迭地跳出來當和事佬:「好啦好啦,此事不能單怪曉樓一人,那廝比泥鰍還溜,咱們不是都著了他的道嗎?大夥的腳都走乏了,你們就一人說一句,留些力氣趕路吧!如今,下山之路已被我們的人重重封鎖,嗯……我看不如這樣,今晚我們就在道觀里借宿,養蓄銳之後,明日再徹底搜山。」說罷,轉頭請示藍袍人,「耿大人,你說呢?」
耿大人略一思忖,沉聲道:「不,不只是今晚,我們要在道觀中,一直住到離開揚州的時候。」
「啊?為什麼?」所有人都大奇怪,齊聲發問。
耿大人負手而立,遠眺著一朵雲說:「捉逃犯只是順便,其實此次揚州之行,我們是另有目的。此事的來龍去脈,越人知道越好,到了需要你們知道的時候,我自然會告訴你們的。」
陸江北和高絕換了一個疑的眼神,卻也不再多問。老實說,對這位新任的錦衛指揮僉事的脾氣秉,他們到現在也看不。
說他待人溫和、事寬鬆吧,又總是覺跟他難以親近,彷彿他的周圍自有一道氣牆能把他與旁人隔絕。說他格孤傲、不近人吧,實際況又並非如此。在他的手底下做事,自由度高得令人咂舌。
別的不說,單看段、廖之間荒誕不經的打鬥,時不時就會在耿指揮僉事大人的面前活現世一遭,他卻連半句斥責之詞,或者一個不悅的眼神都欠奉。事實上,他既不以長的份加以約束,也不跟大伙兒一起看熱鬧,就彷彿一個不存在的人……總之,耿僉事此人,讓他們這幾個常年遊走於皇宮、場和民間,自認閱人無數的老江湖也不到底。
想到了這裡,不知為何,陸江北的心底突然升起一莫名的寒意,連忙轉移話題道:「話說回來,那兩個小道姑走路真的很慢啊。」說著舉目朝山下了,「咱們大伙兒在這邊耽擱了這麼長時間,卻還沒看見們走上來,而且一點蹤影也無,真奇怪啊!」
段曉樓也覺得不尋常,忙運功於雙耳,靜聽一會兒,皺起了劍眉:「的確,連們的腳步聲也聽不到了,喂,們不會出事了吧?不如我們去找找……」
高絕板著一張臉催道:「快上山,我了。」
陸江北拍一下段曉樓的肩頭,忍俊不道:「你何必瞎心,或許人家是不願與咱們同路,所以故意落在後面了。你忘了,剛才咱們跟在人家後面,擅自聽了半晌孩家的悄悄話,你還出聲笑人家,心中一定是惱了咱們。快走吧,彼此都在一個道觀里,還怕以後見不著麼?」
於是,段曉樓安分地閉上,一行人繼續前進。
誰知走了一會兒,廖之遠又不安分了,他用手肘捅了捅段曉樓的腰,斜目道:「喂喂段,對那一位容貌清麗、談吐雅緻的小道姑……你也是純屬好奇,『無關風月』嗎?」
段曉樓的耳朵發熱,沒好氣地冷哼道:「沒完沒了了你,又提幹嘛!」
「嗷嗷嗷!」廖之遠狼一聲,「段,你的耳朵都紅了!你不會真看上人家了吧?」
「你胡說夠了嗎?再胡說八道吃我一拳!」
「依兄弟我瞧,這小丫頭真不錯的。喂,把頭轉過來,別不理我嘛!我覺得,起碼比你從前領回家的那些都強,帶回去給你母親見了,一定會喜歡的。再等上幾年出落得亭亭玉立了,給你做一房小妾倒是綽綽有餘。嗯,你把從清苦的道觀中『救』走,也算是的恩人,一激說不定就以相許了……」
「滾!越說越離譜,有個影兒你就蹦出個子兒來!你怎麼不帶回去見你娘!」
「哈,大伙兒聽啊,段終於招供了!他心裡……已經有個影兒了!」
「野山貓,你還想找打是吧!」
「小逸,為什麼咱們又要返回去?之前你不是說,我們不能去找那個傷的人嗎?而且剛剛那些人是差,那林子里的傷者不就是他們要捉的壞人嗎?」
「別問這麼多了,看,這種形狀的草,你也幫我在附近找一找。」何當歸一揚手中的圓葉草。
「哦。」真靜聽話地彎腰幫忙去找。
找了片刻,兩人得了五六株那種圓葉草。「好了,有這些也夠了。」何當歸拉起真靜,微微一笑,「走,咱們去救人。」
「救人?好啊!不過咱們幫助壞人,沒關係嗎?」真靜眨眨眼。
何當歸的手攥拳,指甲把手中的草掐出了,目若寒星,臉上似笑非笑:「真靜啊,世間之事,不是非善即惡的,就像你們出家人常說的,善惡均在一念之間。」
猜你喜歡
-
完結247 章

崔氏玉華
早當家的本地女的故事 崔氏玉華,她是尊貴的崔氏女,也是低賤的胡漢雜種,決絕的親娘從小苛求,讓她早熟懂事,格外機敏,欺壓利用都無所懼,娘讓我好好的活著,我便要好好的活著......
74.5萬字8 11803 -
完結488 章

踹翻渣男后,全京城排隊求娶
上輩子,顧櫻為了一個江隱,放棄東平伯府嫡女的尊嚴,死纏爛打,終于嫁他為妻。后來,江隱位極人臣,先謀國,后殺她父,滅她族。而她被渣男渣姐合謀打斷雙腿,扔在破廟,受盡侮辱,整整十年。重生后,顧櫻浴血歸來,占盡先機。復仇第一步,抱住“未婚夫永安小侯爺”大腿,踹渣男,斗渣姐,將汴京世家勛貴玩兒得團團轉!復仇第二步,跟“未婚夫”退婚,遠走邊疆,帶著幼弟去找父親!復仇第三步,找個“三從四德”的聽話男人把自己嫁了,遠離渣男,會不幸!可她萬萬沒想到,自己陰差陽錯抱住的大腿,竟然不是小侯爺,而是傳說中神秘狠辣的...
86.8萬字8.18 145079 -
完結403 章
盛寵醫妃世無雙
神醫殺手雲念一朝身死,再次睜眼時成為了駱家人人可欺的軟包子二姑娘。 駱晴看著滿屋子利欲薰心的“家人”們,決定手起刀落一個不留。 順便再帶著家產,回到京城去找她的仇人們。 殘暴皇帝愛煉丹? 那就讓他中丹毒而亡! 仇人臨江王中了蠱? 那就讓他蠱毒發作爆體! 世人皆說平陽王深情,亡妻過世以後仍然娶了一個牌位當王妃。 可是直到有一天,他遇見了駱晴。
95.2萬字8 18984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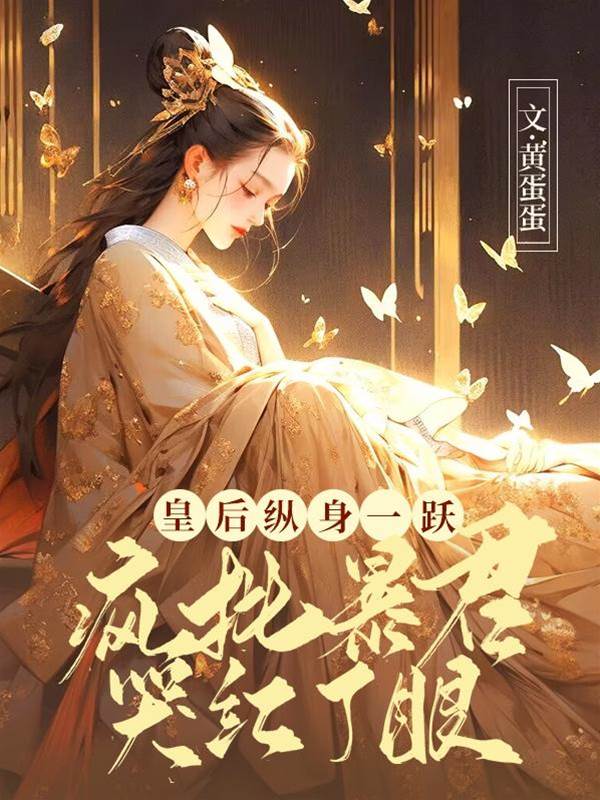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