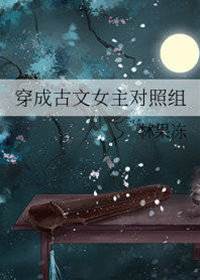《廢后重生:腹黑二小姐》 第三十一章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2)
盡管如此,大夫好似下定了決心,仍是一口咬定蕭塵霜確實有喜。
昭云無奈的搖搖頭,還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于是讓趙嬤嬤帶蕭塵霜進去檢查,雖然此舉有些侮辱,可若能當著眾人的面還一個清白,那這件事不管再丟人,再辱,那都是值得的。
大家都在外面等著,蕭義的臉也是越發的臭,這幫人平日里還看不出來,如今一出了事,卻都等著看他相府的笑話!
與此同時昭云也確實讓太醫速速出宮來診治。
沒一會兒,門開了,趙嬤嬤走了出來,每走一步態端莊,肅然道:“丞相夫人,子名節關乎大小,這樣的事以后還是查清楚再說,二小姐仍是清白之,在皇恩面前,老不敢有半句假話。”
“不可能!明明嘔吐不止,大夫也說是喜脈,怎可能是清白之!”連蓉兒幾乎快要暈了過去,本來設了一場好戲,可最后自己卻了這戲中人。
“事實擺在眼前,蕭丞相,家風不純,對您的仕途可是極有影響。”昭云面沉的看著他。
蕭義此時如同吃了死蟑螂一樣惡心難,咬牙道:“公主說的是,此事微臣必定徹查,絕不姑息!”
連蓉兒連忙跪了下來,哭訴道:“老爺,問題真的被賣到木家村,真的是黃家的共妻啊,老爺你信我!”
“如此我更想問問母親,您怎麼如此清楚,還是說你承認是你將我賣到木家村的?”蕭塵霜饒有趣味的看向連蓉兒。
一霎間,連蓉兒慌了,全張的像石頭,心像是灌滿了鉛,面發白,急道:“我不知道你在胡說什麼,老爺,你相信我,我不知道,我也是聽說……”
蕭塵霜面微沉,語氣十分冷酷:“云嬤嬤來接我,半道上卻將我丟棄荒野,若非遇到云林寺高僧搭救,我早就死了,母親,你倒是真的狠心,毫沒有半點主母該有的樣子,妒婦罪犯七出,理應休之!”
Advertisement
連蓉兒險些栽倒在地,幸而云嬤嬤及時攙扶,這才穩住形,心悸不已,卻強作鎮定,“一派胡言,我這里還有你與婁知縣勾結的書信,是你讓他幫你封鎖木家村的,誰知道你們有什麼勾當!”說到此,讓云嬤嬤將信箋拿出,直接遞給了蕭義。
信……
聽得此話,蕭塵霜面容平靜,可雙手卻攥著袖子,是如何得知的?可轉念一想,就算真的知道什麼,事沒鬧大之前,也大可否認。
可當蕭義打開信一看,卻赫然見到上面有人的手指印,幾行小字無不著連蓉兒的狠毒辣,竟將蕭塵霜賣到木家村,難怪他幾乎把淮安翻遍都找不到,原來這才是真相!
蕭義深吸一口氣,竭力抑怒火,沉聲道:“你自己看!”
他一甩手,把信紙甩了過去,其實信箋很輕,可真正砸到臉上的時候,多有些覺。連蓉兒手忙腳的撿起信紙匆匆一覽,卻見臉迅速變化,瞳孔不由放大,子不住地抖。
“不……怎麼會……老爺你信我,我不知道使了什麼妖法,昨天看到信本不是這樣,為什麼會變賣契……”
眼下是真的看到這封信,白紙黑字拭不掉,也只好朝著別的方向解釋,可惜這番辯詞聽起來更像是在推。
在場之人也不是泛泛之輩,誰黑誰白一眼就看得出來,何況從夫婦二人的表和對話來看,這確實是賣契。
這位嫡母也實在太喪心病狂了,一個庶出的兒罷了,就當養條狗也好,至于將往死里打嗎?
這種做法實在令人發指,每個人看向的眼神像是一道強,著厭惡和諷刺。
昭云端起杯盞,嗅了嗅茶香,開口道:“那這幫造謠生事,顛倒黑白,無中生有的刁民應當如何置?”說到此,一臉嚴肅的看向宋大人,“宋大人,本宮想請教一二,應該以什麼刑法?”
Advertisement
“按律當行拔舌之刑。”
這都是什麼事?
眼下連蓉兒徹底倒了,這十幾個人心里也頓時慌了起來,他們當了一輩子農民哪里經歷過這些事,又聽說要拔舌,就差沒嚇得尿子。
于是為首的人趕磕頭道:“公主饒命啊,冤枉啊,小人冤枉啊,都是指使的……!”說著他便指著連蓉兒,余下的人包括剛才的李大嬸也指著連蓉兒,“對,就是,說要是不出來作證就要殺了我們全家啊,還請公主為我們做主啊!”
“不,不是這樣的,老爺你信我……”的大腦已經失去指揮自己行的能力,木頭一般癱坐在地上不,楞著兩只眼睛發癡地看著這些人。
怎麼會變這樣,剛才明明是蕭塵霜陷絕境,可為何現在深陷泥潭的卻是自己,到底哪里錯了?
蕭義死死攥著拳頭,本不想再多看連蓉兒一眼,低了聲音:“給我帶下去!”
他鐵青的臉并無半點緩和,反而越來越沉,他直了腰板,無奈道:“今日的事,是我蕭某人治家不嚴,讓諸位見笑了,只是如今還需清理門戶,請各位先回,來日必定登門造訪。”
誰能想到這麼一出,竟是曲折至極,峰回路轉,真真讓人看了好大一出戲。
“哎,可總算真相大白了,這孩子倒是可憐……”
楊夫人眼帶嘲諷,溫溫的說:“這丫頭我看著歡喜,若是丞相實在不喜歡,便送到我們楊家來,剛好與我家芝兒做個伴。”
聽得這話蕭義更是氣的角搐,他蕭家怎會連個孩子都養不起?這分明就是在打他的臉!可這一切都是這個賤婦搞出來的。
“楊大人真是治家有方,夫人此番話,實在讓本相驚詫。”
Advertisement
楊夫人豈會不明白,他這話的意思便是說楊則達過于縱容了自己,欠了欠,失了一禮便和其余的賓客相繼離去。
賓客離開之后,蕭義立馬下令將連蓉兒綁起來,扔到柴房等候發落。
云嬤嬤見此,立馬撲了過去,摔倒在他腳邊,哀求道:“老爺,都是我的主意,這一切都是老奴出的主意,您饒了夫人,夫人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蕭義狠狠一腳將踹開,“賤奴,就是你干的好事!來人,把這老東西拖下去重打五十大板!”
“老爺……老奴的錯,都是老奴的錯,放過夫人吧……”云嬤嬤被府兵拖了下去,老遠就聽到板子落在皮上的聲音,并未慘,仍只是幫連蓉兒求。
老夫人只覺得子異常沉重,今日的事是無法善了了,蕭家只會為笑柄,若是死了又該如何面對祖先列宗。
柳盈和眾丫鬟將老夫人送了回去。
李若蘭和蕭錦繡也是繃著一張臉,不敢多說半句,明眼人都看得出,連蓉兒這一遭怕是徹底完了。
現在想想拿靜安寺的事,也不余力的幫忙,如今連蓉兒遭殃,下一個會不會是自己?
李若蘭下意識的抬頭,看了看蕭塵霜,卻不料也正好看著自己,角帶著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意,可如今這抹笑意看起來就更顯詭異了。
心里一慌,忙低下了頭,這個小子實在不簡單,心機未免太重,還是一直在等的機會,便也是今日?如果真是如此,那……此不除,恐怕將永無寧日。
一群人都在廳中等著,蕭義坐在椅子上一語不發,臉和今天的烏云一樣。
明軒也站在一旁,他雖想求,可畢竟還不知悉前因后果,想著父親正在氣頭上,此時開口只怕會適得其反,只好再尋時機。他吩咐旁邊的下人端來一杯茶水,雙手奉到蕭義跟前,“父親,先喝杯茶。”
Advertisement
看了一眼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兒子,蕭義僵的面容總算松幾分,他端著茶杯遲遲沒有送到邊。最近家中事頻多,而這一切似乎都是從蕭塵霜回來之后才開始的。
想到此,他抬眼看了看,一雙鷹眼太過銳利,似乎想要將整個人看穿,但看了半晌,也沒有發現蕭塵霜有任何奇怪之,難道真是巧合?
還是說本就是連蓉兒自己做賊心虛,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蕭義板著一張冷臉,“塵霜,既然知道是怎麼回事,為何你不早說,偏偏要等到這個時候才說出來?”
猜你喜歡
-
完結2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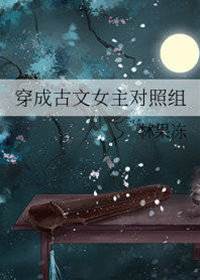
穿成古文女主對照組
楊海燕穿成了古文女主對照組里的那個對照組。 小說劇情里,兩人被賣進同一戶人家當丫頭:原主是大丫鬟、長相好、女紅好、讀書識字,主家落難,奉圣旨嫁給了邊關軍營里的百夫長秦放。 女主是粗使丫環、長相普通、女紅粗糙、沒讀書不認識字,主家落難,也奉聖旨嫁給了邊關軍營裡的百夫長男主韓臻。 自以為優秀的原主一直跟女主比較,結果,女主跟著男主榮陞將軍夫人。而原主作掉了秦放的前程,成了家屬院里女主的對照組。 穿書後: 楊海燕看著身材高大、四肢修長的男人,心裡想,這是她的菜。 秦放看著眼前這個弱不禁風,連桶水都拎不動的女人,心裡想,他一個月1兩銀子、30斤糧食的月例,這些糧食光自己都不夠吃,現在娶了媳婦,他還要把糧食分出去,他好苦。 內心戲很豐富男主VS聰慧隨遇而安女主
81.3萬字8 22007 -
完結964 章

惡女為嫡
渺渺紅塵,以善終,以惡始。一朝得以重生,坑渣男、虐白蓮,斗黑心祖母姨娘,調教善男惡女,宅斗宮斗一鍋燴,雖步步驚心卻翻云覆雨,攪動一方天地,開展快意人生。(女主非善類,玻璃心勿入)…
159.6萬字8 26911 -
完結503 章

重生之請妻入甕
聽聞鎮國將軍府,老將軍年老多病,小將軍頑疾纏身。作為一個不受待見的公主燕卿卿,兩眼發亮,風風火火的主動請求下嫁。本是抱著耗死老的,熬死小的,當個坐擁家財萬貫的富貴婆的遠大理想出嫁。不曾想,那傳聞中奄奄一息的裴殊小將軍化身閻王爺。百般***還…
77.7萬字8 29843 -
完結1277 章

爆笑穿越:王妃是朵白蓮花
戰神燕王說,我家王妃身嬌體弱,善良溫柔,你們都不要欺負她!被她坑的有苦難言的眾人,你說這話,良心不會痛?登基之后的燕王又說,我家皇后的端莊賢惠,朕獨寵六宮,眾妃們做個擺設就好!鎩羽而歸的眾妃們,皇后的手段比她們高百倍,爭個屁呀?終于,四海升平,海晏河清,燕王含情脈脈:“皇后,咱們好像還缺個太子呢!”
278.4萬字8 59504 -
完結260 章

流放路上炮灰寡婦喜當娘
許柔兒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穿成炮灰寡婦,開局差點死在流放路上!不僅如此,還拖著個柔弱到不能自理的嬌婆婆,和兩個刺頭崽崽。饑寒交迫,天災人禍,不是在送死就是在送死的路上。但許柔兒表示不慌。她手握空間富養全家,別人有的我們也有,別人沒有的我們更要有!“那為什麼我們沒有爹。”“爹?”許柔兒看著半路搶來的帥氣漢子,見色起意,一把薅來。“他就是你們的爹了!”帥男疑惑:“這可不興喜當爹。”“我都喜當娘了,你怕什麼喜當爹!”
47.3萬字8 29692 -
完結794 章
盛寵天下:不良醫妃要休夫
大婚之日,軟弱的草包嫡女雲安安被庶妹陷害與他人有染,渣男將軍更是將她打到死,並且休書一封將其掃地出門。 鳳眸重視人間之時,二十一世紀賞金獵人雲安安重生,洗盡鉛華綻,瀲灩天下。 “小哥哥,結婚麼,我請。” 雲安安攔路劫婚,搖身一變從將軍下堂妻成為北辰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攝政王寵妃。 世人都說攝政王的寵妃是個不知檢點的草包廢物,可一手銀針起死人肉白骨,經商道成為天下首富,拳打皇室太子腳踏武林至尊又是誰? “王爺...... 王妃說她想要當皇帝。 “ 北辰逸眼神微抬,看著龍椅上的帝王說道”你退位,從今日起,本王的夫人為天。 ”
155.3萬字8 163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