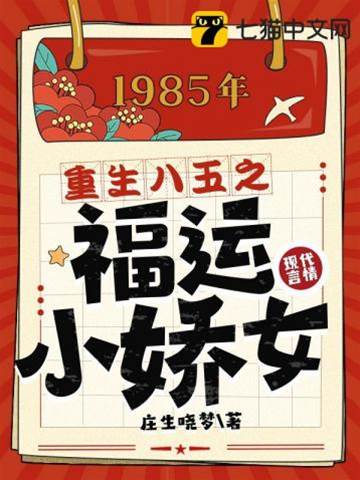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嫡謀:一品皇貴妃》 第082章 現在,還是應該將把正事放心上
輾轉之間,當這些都確定下來之後,雲歌緩聲說道:“皇上現在不應該將心思都糾結在這一才是啊!畢竟現在對皇上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後宮與前朝之間的這些牽扯,皇上您說呢?”
胤聽到這人說出來的話,竟是一個字都不能去辯駁的,好像錯在其中的種種全部都是被堵回去了,可是在心底匿的那些,還是會忍不住的想要去更深其中,直接問道:“如果這些都結束了,朕還是……”
雲歌見胤這樣說話,心中已然是有些錯愕的,立馬就將這些話打斷,直接說道:“皇上什麽時候也開始有這樣的想法了?這可不是皇上您應該有的啊,畢竟在皇上而言,做任何事都是那樣的有規有矩,而且每一步都是計算的非常準,什麽時候起,皇上也會因為這些而去忖度猜測以後的那些呢?”
胤眉頭微微一皺,但是就是找不到一個確定的方向去回應,因為,就算他說的再多,在雲歌心中也隻是將這些都切斷,而不會真正的往他所想的方向靠過去,“是,的確是這樣,可是朕在你上,願意將這些東西往後無限延,你難道就不能給朕一個回應嗎?”
雲歌凝,心口略微哽了一下,許久,才將這一份安靜打碎,然後開口對著眼前的人說道:“皇上覺得嬪妾應該用怎樣的回應來給皇上呢,其實皇上是很清楚的,這樣的況換是誰都……”這話說到這裏的時候,雲歌到底還是停頓了,因為胤從未給別人這樣的機會。
胤見凝而停頓的樣子,便開口說道:“怎麽不往下說了?”
兩個人的語氣織其中,那都是沉甸甸的環繞在裏麵,無論從哪一方都是不會有可以更改的痕跡,隻是將這些都堆積在那裏的時候,又能用怎樣的心思去料理呢,明明這樣的況在雲歌看來是很清楚的,可為何還是會無法呢?
Advertisement
想到這裏的時候,似乎這樣的事都會因為織的種種而變得有些錯落了。
終究,雲歌緩緩說道:“皇上所說的事太遙遠,嬪妾現在憑空也給不了皇上想要的答案,皇上或許還是應該將利用做到極致才是。”
“可是朕在你上並不想隻有如此而已。”胤冷然一句。
雲歌淡淡的聲音開口說道:“不隻是如此而已嗎?”
這一句反問從雲歌的口中口而出,胤聽耳中,緩聲說道:“難道在妃宮的那一刻起,就從未有想過,在這輾轉之中,會有其他的變化,莫非隻是因為那聖諭不可違,宮也隻是為了遵從而已?是不是意味著,如果沒有這些的話,你並不想……”
“皇上說的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宮是必然,而且嬪妾人現在就在宮中,這一點毋庸置疑,皇上要是再多說的話,那就有些過了。”雲歌直接將這樣的話切斷。
胤對上雲歌的雙眼,在那裏麵隻有無限的堅定,好像這裏麵的種種全部都是無法去更替的。
雲歌見眼前的人不再說話,所有的心思都沉頓下去了,隻是淡淡的聲音說著,“皇上想要借助定國公府離朝堂,卻有極高的威,以此作為契機,將嬪妾收宮中,嬪妾配合皇上,做好該做的,至於等到將來會變什麽樣子,那就是將來再去打算的了,皇上以後就不要再繼續在嬪妾麵前說這些未來的事了。”
雖然,雲歌很清楚,將這些說的如此決然是有些不好,可是非常清楚,現在對於胤而言,那就是一種令人充滿好奇的存在,可是那也僅僅隻是在好奇而已,帝王的心思,並不是那麽好拿的,現在是在互相合作,為了一份目的而織其中,可到最後這些都消散的時候,那又應該用什麽來維係呢。
Advertisement
現在將這些都區分好,等到將來,那樣才不會太過於顯得有些悲涼。
的牽扯,尤其是牽扯到帝王的時候,那都是會有些糟糕的。
“你……”
雲歌並沒有在意與胤的生氣,或許是因為對這些的在意,所以才會愈發的計較吧,可雲歌心中明白,才不會讓這些左右自己的心,縱然胤給帶來的那些刺激是在這一世從未會過的覺。
想到這裏的時候,雲歌不免沉沉的歎了一口氣。
胤眉頭蹙,沉然之間,直接開口說道:“了朕的人,永遠都是朕的人,一輩子,生與死都隻能是朕的人,不可能有更改的機會,你也不可能有擺朕的機會。”
雲歌聽著他這般冷沉的話,心裏麵略微還是遲疑了一下,可想到這裏的時候,那又有什麽好需要去計較的呢,隻是默然將那些心思都已經去掉了。
終是,胤從這雪宮離開了。
在這外間的紫蘇和許月兩人是有些擔憂的,因為皇上走出來的那一刻,麵是有些難看的,們匆匆忙忙之間,便直接走了進去。
們兩人看到站在那裏的雲歌,徑直過去,紫蘇擔憂的問道:“小主,剛才皇上和小主是怎麽了嗎?奴婢瞧著皇上的臉好像有些難看啊!”
雲歌隨即不顧哦轉在那人靠上坐下來,然後將那些凝重的心思都收起來,淡然的說道:“我不過是將那些最應該說明的況和皇上說了而已。”
紫蘇詫異,“那小主是說到了什麽惹到了皇上嗎?”
許月直接說道:“小主隻是說了該說的,又怎麽可能會惹到皇上呢,再說了,現在小主和皇上之間所有的事不也隻是限於在那件事上嗎?再多也不過就是維係在這兒啊,哪裏還有什麽不妥的地方會讓皇上為難呢?”
Advertisement
紫蘇琢磨之間,想想也對,可是為什麽皇上會有些生氣模樣呢。
雲歌看著們兩人一眼,搖了搖頭,“不用擔心,該是如何就如何便是,不用因為這些而去糾結,皇上的心思從來就不是誰能夠輕易的去猜測到的,既然不能為一個定論的話,那就完全沒必要去糾結其中,咱們隻需要將這些都撇開,淡然之就好了。”
紫蘇尋思這,“小主,您確定沒有什麽問題嗎?”
“怎麽?你覺得還有什麽別的狀況出來嗎?是不相信我了?”雲歌隨口說著。
們倆自然是立馬就搖了搖頭,然後隻是在旁邊站著而已。
雲歌心中非常清楚,和事是不能牽涉在一塊的,那樣隻會讓事變得非常的麻煩,任何事兒一旦牽涉到上麵,就會有千萬縷理都理不清的存在出現,雖然他們之間的事是針對其他,可這也是不應該的,既然不應該,那就沒有必要去做。
沉凝之間,殿隻有這無限的安靜存在著,似乎連那一份心跳都變得非常的清晰似的。
這個時候,雲歌靠在那人靠上,看向紫蘇和許月們,不自然之間,也隻是問道:“你們相信,有些會因為某些織而忽然有了變化,讓原本的那些變質嗎?”
紫蘇和許月聽到這話的時候,是詫異的,完全就沒有明白其中是什麽意思,紫蘇想法是比較多的,看到的事也是有些細致,便道:“小主的意思是與皇上之間嗎?所以剛才皇上有些生氣,是因為這件事?”
雲歌覺得自己就不應該多說這一句話,順然就讓紫蘇有了覺察,隨口之間,也沒有多想,就笑道:“倒也沒有,不過就是順口一問罷了,畢竟我宮是出於什麽狀態,所需要被用來做到怎樣的程度,那也是明朗的。”
Advertisement
許月不假思索的說著,“不過,小主,奴婢倒是看在眼中的,皇上對小主好像是有些不一樣的呢,就像是單純的男人看待人的那種。”
雲歌聽到許月的話,不由得笑了,“單純?在這宮中就沒有單純可言,至於所謂男人看待人,許月,你什麽時候對這些有了解了?怎麽?莫非是看中了宮中哪個侍衛了?”
許月被自家小主這樣打趣,臉緋紅,“小主,您又打趣奴婢了,這怎麽可能啊!明明剛才是在說皇上和小主之間,怎麽又轉移到奴婢上來了呢?”
紫蘇當然清楚,們家小主就是這樣,牽涉到自己上不願意說的,很快就會找到一個借口,轉移掉,隨之,也隻是開口順著說道:“小主,您拿著別的事說許月還好,莫要拿著這些來說,呀,最是經不得這樣的事呢!”
雲歌看著們兩人,在這後宮之地,所有的心思都是清清楚楚的,無論是哪一方,至在自己的邊還有們兩人在,至於與胤的那些,總歸還是太過於縹緲,不應該想的太多,就應該將心思放簡單一點,隻是傾向在那正經事上。
殿中,們主仆倒是說說笑笑,一應都是簡單了然的,暫且都是把那些丟開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61 章
他養的小可愛太甜了
他是商界數一數二的大人物,眾人皆怕他,隻有少數人知道,沈大佬他……怕老婆! 沈大佬二十八歲以前,對女人嗤之以鼻,認為她們不過是無能,麻煩又虛偽的低等生物。 哪想一朝失策,他被低等生物鑽了空子,心被拐走了。 後來的一次晚宴上,助理遞來不小心摁下擴音的電話,裡麵傳來小女人奶兇的聲音,「壞蛋,你再不早點回家陪我,我就不要你了!」 沈大佬變了臉色,立即起身往外走,並且憤怒的威脅:「林南薰,再敢說不要我試試,真以為我捨不得收拾你?」 一個小時之後,家中臥室,小女人嘟囔著將另外一隻腳也塞進他的懷裡。 「這隻腳也酸。」 沈大佬麵不改色的接過她的腳丫子,一邊伸手揉著,一邊冷哼的問她。 「還敢說不要我?」 她笑了笑,然後乖乖的應了一聲:「敢。」 沈大佬:「……」 多年後,終於有人大著膽子問沈大佬,沈太太如此嬌軟,到底怕她什麼? 「怕她流淚,怕她受傷,更……怕她真不要我了。」正在給孩子換尿布的沈大佬語重心長的
105.2萬字8 126762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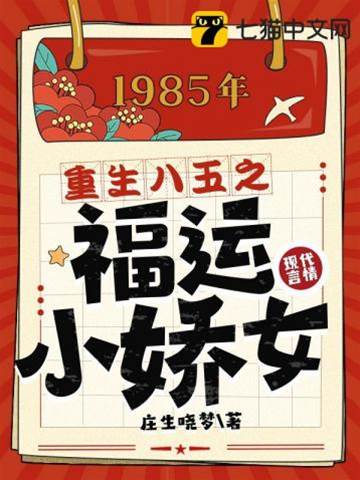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20870 -
連載552 章

妻女死祭,渣總在陪白月光孩子慶生
【重生+雙潔+偽禁忌+追妻火葬場】和名義上的小叔宮沉一夜荒唐后,林知意承受了八年的折磨。當她抱著女兒的骨灰自殺時,宮沉卻在為白月光的兒子舉辦盛大的生日宴會。再次睜眼,重活一世的她,決心讓宮沉付出代價!前世,她鄭重解釋,宮沉說她下藥爬床居心叵測,這一世,她就當眾和他劃清界限!前世,白月光剽竊她作品,宮沉說她嫉妒成性,這一世,她就腳踩白月光站上領獎臺!前世,她被誣陷針對,宮沉偏心袒護白月光,這一世,她就狂扇白月光的臉!宮沉總以為林知意會一如既往的深愛他。可當林知意頭也不回離開時,他卻徹底慌了。不可一世的宮沉紅著眼拉住她:“知意,別不要我,帶我一起走好嗎?”
101萬字8.33 182780 -
完結179 章

灼灼浪漫
大雨滂沱的夜晚,奚漫無助地蹲在奚家門口。 一把雨傘遮在她頭頂,沈溫清雋斯文,極盡溫柔地衝她伸出手:“漫漫不哭,三哥來接你回家。” 從此她被沈溫養在身邊,寵若珍寶。所有人都覺得,他們倆感情穩定,遲早結婚。 有次奚漫陪沈溫參加好友的婚禮,宴席上,朋友調侃:“沈溫,你和奚漫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沈溫喝着酒,漫不經心:“別胡說,我把漫漫當妹妹。” 奚漫扯出一抹得體的笑:“大家別誤會,我和三哥是兄妹情。” 她知道,沈溫的前女友要從國外回來了,他們很快會結婚。 宴席沒結束,奚漫中途離開。她默默收拾行李,搬離沈家。 晚上沈溫回家,看着空空蕩蕩的屋子裏再無半點奚漫的痕跡,他的心突然跟着空了。 —— 奚漫搬進了沈溫的死對頭簡灼白家。 簡家門口,她看向眼前桀驁冷痞的男人:“你說過,只要我搬進來,你就幫他做成那筆生意。” 簡灼白舌尖抵了下後槽牙,臉上情緒不明:“就這麼在意他,什麼都願意爲他做?” 奚漫不說話。 沈溫養她七年,這是她爲他做的最後一件事,從此恩怨兩清,互不相欠。 那時的奚漫根本想不到,她會因爲和簡灼白的這場約定,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丟在這裏。 —— 兄弟們連着好幾天沒見過簡灼白了,一起去他家裏找他。 客廳沙發上,簡灼白罕見地抵着位美人,他被嫉妒染紅了眼:“沈溫這樣抱過你沒有?” 奚漫輕輕搖頭。 “親過你沒有?” “沒有。”奚漫黏人地勾住他的脖子,“怎麼親,你教教我?” 衆兄弟:“!!!” 這不是沈溫家裏丟了的那隻小白兔嗎?外面沈溫找她都找瘋了,怎麼被灼哥藏在這兒??? ——後來奚漫才知道,她被沈溫從奚家門口接走的那個晚上,簡灼白也去了。 說起那晚,男人自嘲地笑,漆黑瞳底浸滿失意。 他凝神看着窗外的雨,聲音輕得幾乎要聽不見:“可惜,晚了一步。”
30.6萬字8.18 1968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