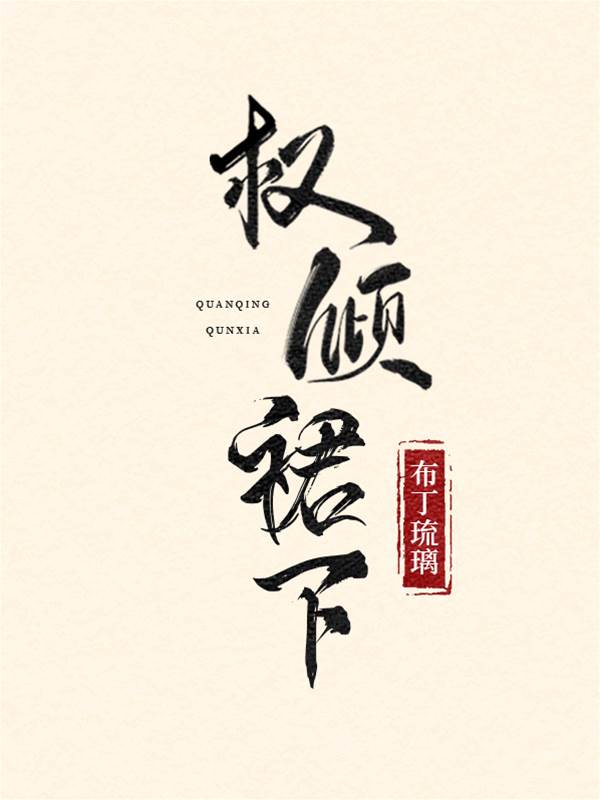《掌上嬌卿》 第71章 晉江正版71
冬葵房中搜出藥包的消息傳到褚玉堂時, 王氏正在挑選六月六玉佛寺曬經節的飾。
曬經節當日京中不貴婦前往法興寺誦經祈福,據知道的就有幾位國公夫人、將軍夫人、兄長同僚的夫人,里頭還有幾位是閨中的手帕, 想為兄長求, 即便機會渺茫,也定要一試。
繡眉慌里慌張地進來稟告時,王氏面上也只是薄冷意。
“手腳的蠢貨, 這都能被人發現!”
不過也不怕, 那藥包中不過是尋常藥材, 即便是加在老太太的湯藥中,在外人看來也只有百利而無一害,要想查到頭上,除非七娘有通天的本事。
王氏閉上眼睛,掩飾微的心神, 只讓繡眉盯著漪瀾苑,有任何況隨時稟告。
就這般又過了一個時辰,繡眉幾乎是慘白著臉跌跌撞撞跑進門:“夫人, 苦石藤被七娘搜出來了!冬葵不住打, 已經將您供出來了……”
王氏瞳孔一,滿眼的錯愕,整個人跌坐在榻上。
繡眉哆哆嗦嗦抬頭:“漪瀾苑來人正往咱們院子里來, 要請您過去……”
將苦石藤下在炭爐的外壁和邊緣, 是兄長王承平教的辦法,掘地三尺也不會被發現!
王氏此刻心的震驚甚至多過恐懼,但頃刻之后, 恐懼徹底打敗震驚, 在心猛烈攀升, 大浪拍岸般地蔓延至四肢百骸。
繡眉跪在地上哭:“夫人,我們該怎麼辦?”
怎麼辦……
也不知該怎麼辦。
沒有兄長了,娘家自難保,沒有人能為撐腰。
心積慮這麼多年,一朝滿盤皆輸,包藏禍心,謀害婆母,千夫所指!
不僅老太太不會寬恕,沈氏宗族也不會再承認。
Advertisement
百善孝為先,天下人都不會放過。
不,絕不能就這麼承認!
王氏眼前一亮,只要咬死不認,誰還能將怎麼樣?
況且早就做足了準備,冬葵手里的藥材都是從二房孫氏娘家的藥鋪拿的,要說下毒的可能,那也是孫氏更大!
王氏閉了閉眼睛,著自己鎮靜下來,隨即端穩起,朝繡眉冷喝一聲:“哭哭啼啼何統!生怕旁人不知你心里有鬼嗎?隨我去漪瀾苑,我倒要看看,僅憑那賤婢一張,能讓我王承念死無葬之地不!”
話音才落下,利落而急促的腳步聲夾雜著兵的聲從院中傳來。
幾個清一穿齊膝窄袖袍的衙役從外面進來,為首的亮出手中的令牌。
“大理寺辦案!王承念與其兄王承平勾結市舶司,涉嫌謀害忠定公,奉陛下旨意,即刻捉拿王承念押送至大理寺審,給我拿下!”
王氏猛然抬頭,仿若當頭棒喝,頃刻間將三魂七魄全都打出軀。
謀害……忠定公。
渾都在劇烈地抖,背脊已經滲出冷汗,還未及多問,就已被兩個衙役反扣雙臂,押送出去。
大爺在衙署上值,不在府上,褚玉堂的幾個大丫鬟、伺候的仆婦,甚至連躺在床上養傷的繡云都被一并拖走問話。
侯府長房只剩下幾個外院灑掃庭除的使下人,一時鳥雀無聲,人人驚懼。
漪瀾苑。
同樣的寂靜,同樣的驚懼,同樣的復雜難言。
原以為大房夫人對老太太下手已經是石破天驚的大事,眾人都沒有想到,當年死在海寇手中的三爺,居然也與大房不了干系。
年長的仆人中還有從聽雪堂調配過來的,他們都還記得沈三爺。
Advertisement
忠定公當年何等年輕英俊,何等耀武揚威啊!
那就像一桿筆直向上的白楊,郁郁蔥蔥,生機,撐起了整個武定侯府的天。
沈三爺一死,三夫人和小公子也跟著走了,老太太大病一場,七娘小小年紀父母雙亡,再也沒能說話。
十幾年來,眾人已經很聽到沈三爺的名字,斯人已逝,他們不敢在老太太和七娘面前提及,慢慢地,等到七娘長大、出嫁,底下人對三房的印象就更淡了。
盡管如此,眾人還是為武定侯府曾經有過這樣一位意氣風發、氣概不凡的青年將軍而驕傲。
在所有人的認知里,沈三爺是在與海寇的鏖戰中重傷沉海,是為國捐軀,可沒有人想過此事竟然另有。
下人尚且如此,更別提沈嫣與老太太了。
這個消息對于們來說猶如晴天霹靂,老太太險些站立不穩。
沈嫣腦海中亦是嗡嗡作響,一片空白,恍恍惚惚涌現出謝危樓離開之前說的那句——“作下的惡,恐怕不比王松圖。”
在冬葵招認之時,對這個“惡”字的定義還只停留在暗中下毒、謀害祖母,沒曾想竟還與爹爹的死有關。
花了十幾年去治愈心里最深最深的傷口,卻在此時被人揭開瘡疤,撕開皮,拖出來狠狠地鞭笞。
沈嫣渾僵著,抖,甚至不敢看自己的祖母。
轉頭看向沒有人的地方,抬起眼眸,淚水卻止不住從眼中奪眶而出。
古稀之年的老太太,曾經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母親,此刻一句話也沒有說,面上卻忍不住老淚縱橫。
這麼多年,需要用日漸佝僂老邁的撐起偌大的武定侯府,在外人面前做那個風雨不侵的侯府老夫人,做在兒孫面前威嚴而慈的長輩。
Advertisement
已經快沒有人記得,早已不是鋼筋鐵骨的將門虎,不是昔日威風八面的年輕侯夫人,只是一個年邁的、失去過兒子的母親。
而對來說更大的打擊,是兒子死亡的真相。
倘若他當真戰死沙場,那也該是作為將士的無上榮,伏波惟愿裹尸還,定遠何須生關,老夫人從小就教過他軍人不畏艱難、視死如歸的道理。
多年以來,喪子之痛猶能以此寬,可偏偏今日有人告訴,害死子的兇手竟是大房的宗婦,是信任了二十余年的兒媳!
活到這個年紀,自認從未做過任何傷天害理之事,一心念佛,卻為何招此孽障,讓那兒媳婦既害了老三,如今還要再來害!
沈嫣面上調整好自己的緒,扶住老太太的手臂,哽咽地喚出兩個字:“祖母……”
一聲祖母,讓老夫人從無盡的痛苦和懷疑中跳出來。
老夫人紅著眼眶,看著老三留下來的骨。
好像也只需這一聲,便能勾兌一生的苦痛。
還好,還有這個孫。
老太太拍了拍的手背,咽下嚨中翻涌而上的苦,“若能真相大白……是好事,你爹爹在天上也能瞑目了。”
沈嫣含淚點點頭。
大理寺審問總得有個過程,們等著便是。
沈嫣回到廊下,派人將地上奄奄一息的冬葵送到順天府。
晚膳時分,大爺邊的小廝來傳話,說大爺在衙署被大理寺帶走問話。
老太太深深地閉上眼睛,這輩子看似英明,卻在識人不清和教子無方上栽了個鮮淋漓的跟頭。
倘若老三之死當真與老大有關……沒臉去見死去的老侯爺,沒臉見沈家的列祖列宗。
月上柳梢,屋上了燈。
Advertisement
云苓將飯菜熱了又熱,沈嫣卻半點食也沒有,抱膝坐在窗邊,撥開黑的窗牗,神思恍惚地看著天上彎刀般的月亮。
手里挲著那枚金蟬,試圖勾起一些時的記憶。
可是隔得太遠了,記憶像覆了一層水波紋,過去便是水中的月亮,只能看到些冰冷的與影,卻怎麼都撈不起來的樣子。
想起爹爹戰死的消息傳到聽雪堂時,丫鬟跌跌撞撞跑進來,滿臉的淚痕,阿娘面上當時就繃不住了。
阿娘扶著碩大渾圓的肚子,地上全是,一滴滴地順著的角往下流,整個聽雪堂慌作一團。
在還沒有明白何為生死的年紀,最親的親人接連離世。
那時眼前似乎只有黑和紅兩種,黑是昏天黑地黑的人,紅是阿娘的,在淺杏的地毯上非常刺目。
阿娘離世那幾日接連暴雨,氣氛抑得難以呼吸,夜夜夢魘,高燒不止,上像沉沉地著一座山,眼皮掀不開,腦海中如同燒沸的水,不停地往外冒泡。
緒也是有記憶的,沈嫣現在就是那種覺,頭痛裂,渾冷汗,像被嗒嗒的厚重棉被遮掩住口鼻,全冷得發抖。
云苓看著的狀態著急:“姑娘,再傷心也不能跟自己的子過不去呀,咱們吃一點,好不好?奴婢去給您請個大夫來瞧瞧?”
無論云苓說什麼,沈嫣也只是默默地搖頭。
隔了很久,終于開口說了一句:“云苓,我想回聽雪堂看看。”
“好!姑娘,奴婢這就去準備!”
云苓見有了反應,自然滿口答應,命人在長廊和石道上都點了燈。
一路恍如白晝。
聽雪堂這麼多年打理得很好,即便為節省開支用度削減了一半的下人,但余下的人依舊勤勤懇懇地做事,守著三房的院子,就像守著三房一樣。
沈嫣靜靜地沿著石磚小路一直走,月下樹影婆娑,夜風吹起垂在后背的青,草叢里、流水間藏著無數窸窸窣窣的細小聲響,仿佛阿爹阿娘在耳邊輕輕的呢喃。
這麼多年,三爺夫婦的寢屋依舊灑掃得干凈無塵,擺設皆與從前一樣。
沈嫣出手,著屋那些有了年頭的桌案和。
案幾上擺放著天青釉的花囊,那麼醒目的位置,一定是阿娘最喜歡的吧。
將那花囊捧起來,輕輕在自己的臉頰,仿佛還有阿娘掌心的溫度。
云苓不知道姑娘還要待多久,安靜地站在廊下等著,怕姑娘緒不佳,出什麼意外,一直屏息凝神,仔細聽著里頭的靜。
直到夜幕中出現一個高大拔的男子影,云苓霎時睜大眼眸。
夜模糊,看不清來人的臉,云苓才意識到方才院中點亮的石柱燈熄滅了一半,這人竟然就這麼大大方方地進來,連值夜的小廝的不曾驚!
云苓大驚,正要開口喚人,男人走近,一雙暗如深淵的眼眸讓云苓為之一凜。
“鎮……鎮北王?”
云苓嚇得甚至連禮數都忘了,反應過來后趕忙躬施了一禮。
謝危樓緩緩走上臺階,迎著無比震愕的神,淡淡吩咐:“你先下去,到外院看著。”
云苓怔怔地應了個是,恍惚還以為這是鎮北王府。
丫鬟的素養教會不能窺探主子的,但十年來與沈嫣深篤的主仆分以及對姑娘的關心,還是讓忍不住往里瞧了一眼。
就這一眼,云苓幾乎是渾一震。
鎮北王……居然將們姑娘抱在懷中!
猜你喜歡
-
完結2728 章
冥婚霸寵:天才萌寶腹黑娘親
她,華夏古武最強傳人,醫手遮天的變態鬼才,卻因一次意外,穿越成了林家不受寵的廢物小姐。一睜眼,發現美男在懷,與她在棺材裡正上演限製級大戲……六年之後,她浴火重生,帶著天才萌寶強勢歸來,手握驚天神器,統率逆天神獸,大殺四方!虐渣男,踹賤姐,沒事練練丹藥,錢包富的流油,日子過的好不快活。可某日,某男人強勢將她堵在牆角:「你要孩子,我要你。」她輕蔑一笑,指間毒針閃現寒芒:「再靠近一步,你就沒命要了。」某寶道:「想要我娘親,我得去問問我的乾爹們同意不同意!」
476.1萬字8.18 113011 -
完結2346 章

快穿:女配又跪了
位面金牌任務者池芫被系統坑了,被逼無奈前往位面世界收集上司沈昭慕散落在三千位面世界中的靈魂碎片。作為一名優秀的任務者,池芫對于攻略這回事信手拈來,但是——三千世界追著同一個靈魂跑,攻略同一個人這種坑爹的設定,她拒絕的好嗎!一會是高冷的校草、…
424.5萬字8 51713 -
完結109 章

良宵誰與共
寡婦娘親改嫁到了蕭家,經歷了各種酸甜苦辣,終于把徐靈蕓養大了,到了徐靈蕓挑選夫婿的年紀,卻發現自己早就已經被蕭家的長子給盯上了……,相愛當中,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43.3萬字8 22174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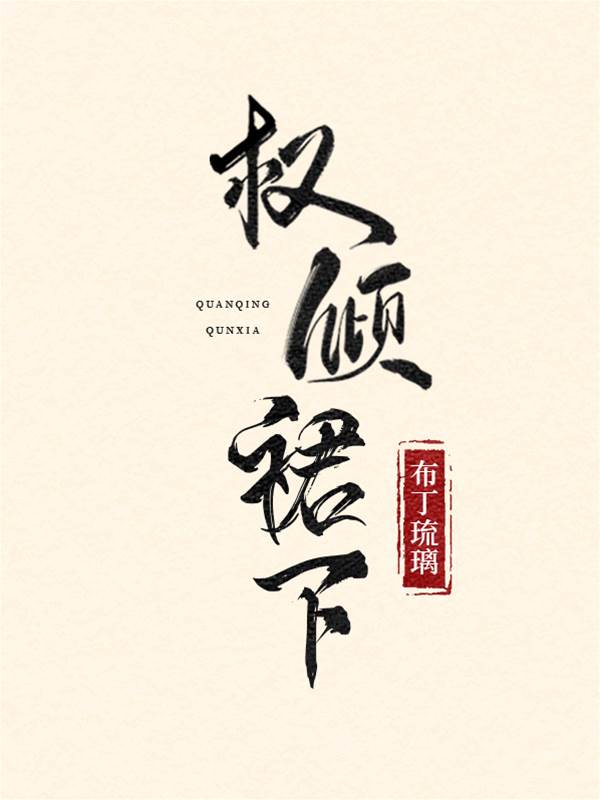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17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