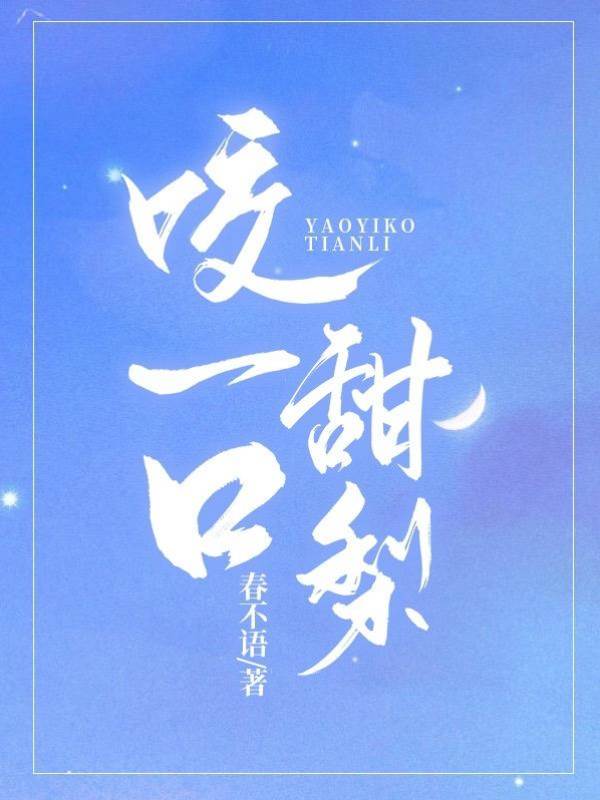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恃寵生嬌:誰說軍爺不撩人》 第445章乖乖在家裏等我,嗯?
“阿嚏——”
季明禮深告白,就在這個時候,陶夭極其不合時宜地打個噴嚏,鼻涕水四濺。
“對不起,對不起,啊——阿嚏——”
季明禮有嚴重的潔癖,陶夭完全想象不出,當季明禮被噴一臉鼻涕時是個什麽心,反正估計夠嗆的。陶夭連忙用雙手捂住了鼻子,笑意卻是從眼睛裏跑出來,很是有些幸災樂禍的意思。
陶夭還擔心季明禮會翻臉呢,當然了,如果對方真的翻臉了,到不了再道個歉就好了。
季明禮卻沒有陶夭以為地那樣沉下臉,他甚至連臉都沒有變過,唯獨在發現陶夭眼底的笑意時,目無奈,“捂著手做什麽?鼻子隻會更不通氣。”
從床邊他過紙巾,季明禮拿下陶夭的雙手,認認真真地用紙巾將的鼻涕給幹淨不說,還用寶寶巾給了一遍,之後,才拿過巾,不疾不徐地給自己拭。
修長、白皙的手裏拿著巾,睫微垂,眸認真,陶夭的心跳不控製地加快了速度——季明禮這個男人,實在是太溫了。
心髒好像是隨時都要跳出口。
不行,不能再這麽沉迷男,陶夭強迫自己轉移注意力,“你不是有潔癖呢麽?你潔癖痊愈了?”
不過,看著不太像啊!
又是用巾臉,還用紙巾把臉幹,最後竟然又用巾把手也給了一遍。
季明禮用巾手的作一頓。
痊愈?
好吧,從心理學角度上而言,過分潔癖也是一是強迫癥的一種,而強迫癥就是心理病癥的一種。
他的潔癖大約是一輩子都不可能“好”地了,隻不過在麵對幺幺時才有短暫地不藥而愈罷了。
把巾扔進紙簍裏,季明禮溫地注視著陶夭,“要不要起床?今天天氣很好,如果我們從現在起抓時間,等到達目的地,人應該不會太多。”
Advertisement
陶夭發現,自己可能真的是睡蒙了,竟然一時間愣是沒能反應過來季明禮說得目的地指的是哪裏,“嗯?到達目的地?我們要去哪兒?”
陶夭歪著腦袋,長如波浪的卷發披在後肩,因為剛睡醒,芙頰緋紅,眼神澄澈,介於嫵跟清純之間。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矛盾氣質在陶夭的上一直頗為突出。陶夭長相豔,很容易就給人一種風嫵之,偏偏的眼神太過澄澈,隻要接下來,就會發現對方的格跟外表截然不同,爽朗而又明。隻不過這一次,這種矛盾而又統一的氣質尤為凸顯,於是就形了一種獨有的。
季明禮心念一,修長的手指刮過陶夭因為連打了好幾個噴嚏而有些發紅的鼻尖,眸噙笑,“小迷糊,護城河賞花,不記得了?”
紅暈飛上陶夭的臉頰。
媽啊!
季明禮這個男人真是越來越能了!
“不去了。”
陶夭紅著臉,了還有些發的鼻子,蓋彌彰地轉過了臉。
季明禮眉頭微皺,“為什麽改變主意了?”
幺幺想要出門散散心,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應該不會無緣無故轉變主意。
倏地,季明禮像是忽然明白過來些什麽,眸子也瞬間躍上欣喜,“是因為我……”
“不,不是,才不是因為你!你可別自作多啊!我就是,昨天晚上沒睡好,這會兒還想睡覺。所以才不想去的,跟你沒有任何關係!”
季明禮眸晶亮,看著陶夭的眼神仿佛映著萬千星。
陶夭不住季明禮這樣溫、沉醉的眼神,仿佛能夠把人的靈魂都給融化了似的,抬手,擋住季明禮的眼睛,聲音染上幾分氣惱,“不許你再用這種眼神看我!”
完全是一副不講道理的蠻橫。
Advertisement
季明禮卻是半點氣也沒有,反而配合地“嗯”了一聲。
陶夭捂住他的眼睛,他也不掙。纖長的睫掠過陶夭的掌心,一麻從掌心一直竄至陶夭的心髒,陶夭就跟電了似的,驟然收回手。
眼前驟然恢複亮,季明禮眸鎖住眼前的人,“昨天晚上為什麽沒睡好?”
這人還有完沒完了?
今天問題怎麽就這麽多!
“你管我昨天晚上為什麽沒睡……”
“是不是,因為我?”
就像是燃燒至一半的炸,在聽見季明禮這句話是,陶夭忽然就啞火了。
季明禮步步,“是因為我,所以昨天晚上沒有睡好。還是因為我,所以今天早上改變了主意,是不是?”
“不是!不是!才不……”
不想再從陶夭的裏聽見這些口是心非的話。
右手捧住陶夭的後腦勺,季明禮低頭,吻住了的瓣。
陶夭陡然睜大了眼睛!
還沒有刷牙呢!
“唔唔唔!”
陶夭用力地捶著季明禮的雙肩,季明禮鉗製住陶夭的雙手,順勢下傾,將陶夭在了下,舌尖挑開的牙關,長驅直,攻城略地,完全不複平日的溫潤有禮。
這男人,真是反了天了!
陶夭眼神噴火,的右曲起,被季明禮提前一步東西,長橫在的雙之間,舌尖侵占口中的每一。
等到兩人的氣息都有些不穩,季明禮這才稍微鬆開陶夭,他一手撐在床上,目灼熱地鎖定剩下臉頰緋紅,眼波生的陶夭,“幺幺,你對我還有覺,是不是?”
“是。”
季明禮先是一征,爾後西德尼湧上一抑製不住地狂喜,“幺……”
“是你個大頭!”
陶夭終於把剛才未說話的話給補充完整,隨手抄過邊的枕頭朝季明禮飛了隔過去。
Advertisement
迎麵飛來一個枕頭,在季明禮下意識地將枕頭給擋開時,陶夭作利落地推開他,下了床。
赤腳踩在地上,陶夭雙臂環,冷睨著尚且有些反應不過來的季明禮,一字一頓地道,“季,明,禮,你,完,了!”
季明禮:“……”
那天,因為陶夭堅持要補眠,兩人最終還是沒能去護城河賞花。
之後的幾天,季明禮可謂是充分地會到了何為冷暴力。
再也不主開口跟季明禮說話都算是小意思了,期間,無論季明禮如何道歉,說得再真心實意,陶夭也是一律掏出手機,用微信來進行流,完地做到了視若無睹,充耳不聞。
就這樣,兩人冷戰,噢不,確切來說應該是陶夭單方麵跟季明禮冷戰了好幾天。
這天,季明禮在下了課之後第一時間就趕回家。
打開家門,在客廳裏,看見了一個整理好的碩大紅行李箱。
季明禮臉驟變。
他腳步急促地上了樓梯。
“嗯,我馬上就帶著小寶出門,你在哪裏等我……”
陶夭一隻手裏拎著提籃,陶小寶在提籃裏睡得正香。如今小家夥一個多月了,小臉蛋比幹出生時眼可見地圓了好幾圈,都長出雙下來了,虧得陶夭力氣大,要不還當真拎不住這小胖墩。陶夭的另外一隻手也沒空著,另外手裏握著電話往外走,季明禮站在門口,臉蒼白。
季明禮今天下午三四節有課,按說這個點應該還在學校才是,眼中閃過一抹意外,加上季明禮的臉看起來實在不算是太好,陶夭也就沒有繼續嘮嗑的心思。
“等會兒,我這邊還有事,我先掛了啊。遲點你定位發我。”
陶夭跟電話那頭的錢多多說了一聲,不等後者反應,就先掛斷了電話。
Advertisement
因為兩人還在冷戰期,當然了,是陶夭單方麵地跟季明禮在冷戰,這會兒陶夭也沒有主開口的意思,故意在原地等了等,等著季明禮開口問去哪裏,誰知道,等了半天,季明禮也沒有開口的意思,可把陶夭給氣的。
得,就當又自作多一回。
陶夭拎著提籃,從季明禮旁走過。
季明禮一隻手握住提籃。
當初,幺幺便沒有答應過他從今往後就住在他這裏,如今執意要走,他如何能夠攔得住?
長長的睫垂覆而下,季明禮艱地開口,“我送你們。”
陶夭心想,這還差不多。
陶夭順勢收了手。
季明禮拎著安全提籃下了樓。
車子就停在別墅門口的天車位,季明禮先將安全提籃放在車上,用安全帶係好,之後返回別墅,替陶夭將行李放進後備箱。
“去車站。”
由於季明禮剛才又是主替陶夭拎著小胖墩,還幫把行李箱給拎進車,陶夭總算是主打破了由單方麵發起的冷戰,主把目的地告訴他。
季明禮眸難掩錯愕,“車站?”
沒有注意到季明禮的反常,陶夭低頭係安全帶,隨口道,“嗯,我明天開始要進組拍戲。”
季明禮一愣?
進劇組拍戲?
不是要帶著小寶離開他的邊?
陶夭扣上安全帶的扣子,遲遲沒有聽見季明禮的回答。
等等……
陶夭像是反應過來些什麽,抬頭,別有深意地看了季明禮一眼,“季老師,你該不會是……該不會是以為我要帶著陶小寶離家出走吧?”
季明禮沒說話,隻是一雙目地鎖住陶夭。
陶夭原本是純粹為了揶揄季明禮,現在看見到對方禮這種反應後,反而笑不出來了。
這人……
所以,他之前是以為要帶著小寶離開,臉才會看起來那麽不對勁麽?
陶夭這才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季明禮造了怎樣的誤會。
想想也是,如果換是季明禮好幾天沒有跟講過話,一回到家,就看見了放在玄關的行李箱,之後上樓又看見他手裏拎著陶小寶,又是選在他上班的時間點,隻怕也會以為季明禮是要離開。
季明禮當時在想什麽?
陶夭並不認為以為,跟小寶的離開對季明禮而言是無關痛的,恰恰相反,坐月子的這段時間,能夠清楚地覺到季明禮對跟小寶兩人的用心。
之前提過要離開的話,季明禮之前的不舍絕對做不來假,這次誤以為要帶著小寶離開,季明禮不可能忽然就舍得了。
舍不得,但還是主送回去,替忙前忙後。
這個男人,怎麽可以這麽好?
“之前我不是跟你說過,經紀人給我發了幾個劇本嗎?我已經決定好要飾演哪個角了。前幾天把小寶給你,出門的那一次就是試鏡去了。因為不知道結果如何,所以就沒有提前告訴你。後來我一不小心就給忘了。劇中的男主角,還有除了配以及我要飾演的四還沒有定下來,其他角都差不多早就已經定下來的。合同也簽了。現在這部劇明天就要正式開拍,按照規定,我明天就要進組。你有工作,肯定沒有辦法全天候帶季小寶,我就想著,把小寶一起給帶到片場去,由多多幫忙照顧。我給你發了微信的,你沒看嗎?”
季明禮太好了,好到陶夭覺得這個時候必須要再多做些解釋,以免對方又有其它的誤會,心生失落難過的。
說起來,陶夭還真不是不告而別。
也是臨時收到劇組要求明天就進組的通知,說是主角檔期比較滿,要再過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才能進組,要先拍們這些戲份不多的出場人的戲份,於是不得不急急忙忙地收拾行李。
在把行李都收拾好後,陶夭就給季明禮發了一條微信,告知一聲。季明禮沒回,陶夭以為他還在上課,也就沒有在意,想著對方下課後遲早能夠看見。
“手機沒電,自關機了。”
季明禮發車子。
換言之他並沒有看見那條短信。
陶夭扶額,“這概率。”
季明禮薄微抿,顯然也在因為這樣的巧合而不大高興。
不管怎麽樣,那條短信都已經錯過,季明禮把注意力放在另外一件事上,“你要把小寶帶去劇組?”
“嗯。這樣的話,我拍戲的時候,多多就可以幫忙照顧小寶,而且也方便母喂養。”
“小寶我可以帶。”
“啊?”
陶夭知道季明禮的時間比較自由,但是這個學期他的課程好像比上個學期還稍微多一些吧?
猜你喜歡
-
連載1965 章

左先生寵妻百分百
她是能精確到0.01毫米的神槍手。本是頂級豪門的女兒,卻被綠茶婊冒名頂替身世。他本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專情總裁,卻因錯認救命恩人,與她閃婚閃離。他從冇想過,有一天,她會用冰冷的洞口指向他的心臟。“這一顆,送你去給我的孩子陪葬!”她扣下食指……
164.4萬字8 184421 -
連載2383 章

錯嫁纏婚:首富老公乖乖寵我
為了救父親與公司,她嫁給了權傾商界的首富,首富老公口嫌體正直,前面有多厭惡她,后來就有多離不開她——“老公寵我,我超甜。”“嗯......確實甜。”“老公你又失眠了?”“因為沒抱你。”“老公,有壞女人欺負我。”“帶上保鏢,打回去。”“說是你情人。”“我沒情人。”“老公,我看好國外的一座城......”“買下來,給你做生日禮物。”媒體采訪:“傅先生,你覺得你的妻子哪里好?”傅沉淵微笑,“勤快,忙著幫我花錢。”眾人腹誹:首富先生,鏡頭面前請收斂一下?
219.6萬字8 148207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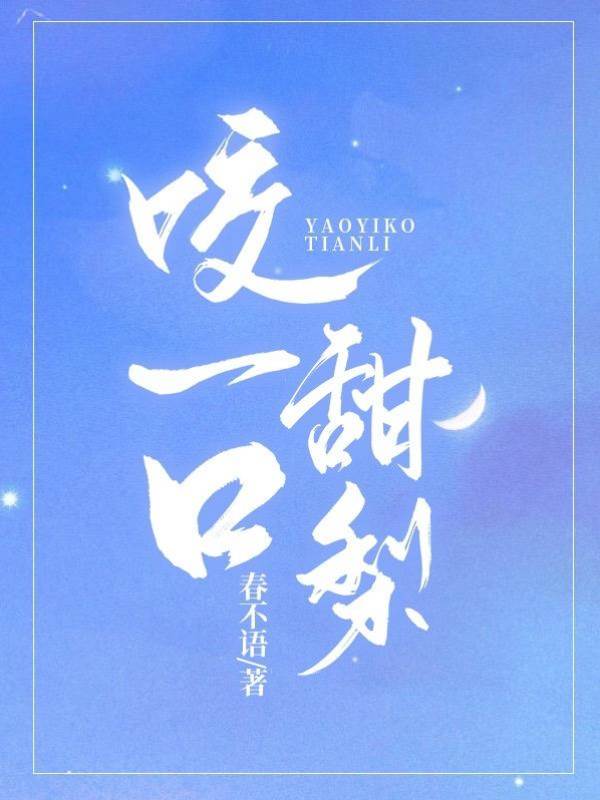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