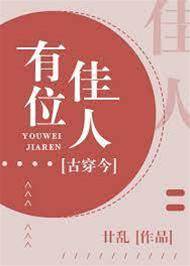《神醫世子妃》 第181章 匕首
約十寸長的暗格裡,放著一隻方方正正的紫檀木盒,盒烏紫油亮,並沒有過多的雕飾花紋,樸實地猶如一塊沉澱古。
卿黎小心地將它慢慢取出,沉甸甸的分量似乎在昭示著,裡面有不好東西。
打開後,只見是一些名貴草藥,以及幾隻悉的青瓷小瓶,那是之前與爺爺談條件時,割讓出去的三瓶瓊脂。
或許,這些東西本就是給的,爺爺只不過是面上過不去,所以“屢教不改”地藏在這裡,等來拿。
卿黎微微一笑,合上蓋子舒了口氣。
爲何要去對他人知知底?爺爺有事瞞著,自然是有原因的,既然選擇不告訴,又定是爲了好,倒是一時急,失了分寸……
自嘲地笑了笑,卿黎又將盒子放回了暗格,只是手指在到暗格底部的時候,竟發現有一條嚴合的突起。
描摹著那道隙,似乎在這暗格下方還有一道暗格。
卿黎心中一,對著那使勁按了按,便見那塊石板迅速收了回去,又漸漸升起一隻錦盒。
鮮紅綢之上,一把簡單緻的匕首靜靜躺著,沒有過多的裝飾,鐵匕尾部,鑲嵌了一顆鮮亮滴的紅寶石,而後便是那用鎏金燙出的一個“黎”字……
“丫頭,出門在外,還是要帶點東西防,這把匕首就送你了。”十四歲時,神矍鑠的老人這麼和說著,想也不想就直接扔到手中。
堪堪接過,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那顆紅寶石,而是那個鎏金小字,那樣狂草的寫風,除了這位老者,還有何人?
笑著揚了揚手,打趣道:“這匕首不本來就是我的嗎?何談相送一說?”
Advertisement
老人的絡腮鬍子都飛揚了起來,捋起袖子直接在額頭上用力彈了一下,罵咧道:“別得了便宜還賣乖!給你就拿著!”
沒好氣了額頭,癟著道:“是,我收著!不過這塊紅寶石就過於累贅了,我又不喜歡花裡胡哨的東西,倒不如拿了下來!”一邊說,一邊搗鼓那塊寶石,還真的被取了下來,霎時驚喜道:“呀!原來是可拆卸的啊!”
眨著一雙晶亮明澈的眼,看他吹鬍子瞪眼睛的模樣,笑嘻嘻著說道:“好,我收著……”
春日的風暖暖的,在那個桃花盛開的季節,簡單收拾了行裝,騎著一匹烏黑駿馬絕塵而去,而這把匕首,也了的隨攜帶之。
只是,上回在罔虛峰上,急之下,拔出來傷了夙蓮,自己也滾落下山,而那把匕首之後再無所蹤……
一直爲此憾,曾讓人回去找過,只是罔虛峰之大,無異於大海撈針,本是沒了多希,卻不想竟是出現在了這裡……
卿黎皺了眉,手搗弄匕首上鑲嵌的紅寶石,沒一會兒就拆了下來。那鮮紅到刺目的彩,和本分不出究竟是何材質的寶石,完全不容錯認……
…“怎麼會在這裡?”卿黎喃喃自語。
如果爺爺是找到了,直接給不就好了?幹什麼還要藏在這層暗格中?
想起先前曾經拿它割傷了夙蓮的手掌,而之前還在爺爺手上見到一條新添的傷痕,這一切是不是有什麼聯繫?
卿黎不敢再往下想,深深呼吸了好幾下,才抑住心中濃重的不安。
匆忙收起了匕首,便回了王府。
似乎從未有過哪一刻如今天那樣讓深深惶恐,突然有些後悔要管這些瑣事,以至於將自也搭了進去。
Advertisement
……
朔北的冬夜比之其他地方更爲寒冷了些,呼呼的寒風在空曠的營地上刮過,喑啞嘶鳴,零散的幾棵樹木,在夜風裡竭力挽留著枝椏上的幾片黃葉,更是如鬼哭狼嚎一般呼哧作響,聽著便讓人骨悚然。
大大小小的營帳整齊排列在這片營地之上,大多數的帳篷已是熄了燈燭,而營外仍有隊伍正在來回巡視,嚴整肅斂,火把映照之下,掠過的人影猶如鬼魅一般,卻更是增添了夜的蕭冷。
最大的營帳中,手臂的牛油巨燭熊熊燃燒,燭淚已經積了滿滿一個燭臺,盈不能盛,滿溢而出,落在案幾之上,凝一塊。
燈燭下,一個淵渟嶽峙的人影依舊在比劃著桌上的地形圖,剛冷俊逸的面容冷凝,周氣息低沉更是讓人不敢靠近。
營帳的門簾被人掀開,一個披鎧甲的高大男子走了進來,看到正鑽研著地形圖的人,無奈笑了笑,“辰,你傷還沒好,早點去歇著吧。聽說夜祭纔剛醒,這幾天會休戰,不用這麼張。”
凌逸辰頭也沒擡,眼睛繼續鎖著眼前的地圖,淡淡說道:“上回在樹林裡,西川擺出的陣法詭異,本雜無章,可是他們卻搶佔天時地利,要不是我方及時退下,那些兵士可能折損一半!阿越,你覺得這種況下,我還能定氣安心?”
他嘆息一聲,又搖了搖頭,“夜祭這次被我重傷,西川兵士心中悲憤不平,所謂哀兵必勝,只怕接下來的仗要難打了……”
南宮越一窒,看他愁眉不展的模樣,也跟著走到桌案前。
紛的地形圖上滿了小旗幟,本就錯綜複雜的圖形,如今看來更是眼花繚。
南宮越皺了眉,重重拍了拍凌逸辰的肩膀,道:“辰,你可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那夜祭雖說是個人,不過你可是我們水墨的常勝將軍,那些魑魅魍魎是見了,都要嚇得屁滾尿流的!”
Advertisement
之前南宮越在夜祭手下吃了虧,輸了首戰,心中可是憋了一口怒氣。
後來凌逸辰來了,就是給他漲了心,而上次手雖說水墨兵力損失比之西川嚴重,但凌逸辰將夜祭傷得下不來牀,可算大快人心,他對以後的戰事絕對充滿信心!
凌逸辰哼了聲,沒好氣地一拳打在他膛上,笑罵道:“你小子,給我來這一套!”
南宮越疼得悶哼一聲,忍不住咳了咳,頗爲驚訝一把抓起他的右臂,小心展起來,“辰,你的手這麼用力,居然沒事?”
夜祭那一槍可是刺在了他肘部,著筋脈而過,軍醫都說,要好好養些時日,否則那隻手也要廢了。
…怎麼才十幾天功夫,居然都打得他口火辣辣地疼?
凌逸辰沒好氣地將手回,脣角似乎勾了勾,老神在在說道:“山人自有妙計,我這傷已經基本痊癒了,就是現在去和那夜祭打一場,還能佔著上風!”
廢話,那夜祭都只剩半條命了,怎麼可能還是你的對手?
南宮越心中腹誹,又一把拉過他的胳膊,奇道:“不對啊!沒道理啊!你這什麼恢復速度?”
他上回了點輕傷都足足養了半個月,這小子怎麼好的這麼快?太沒天理了!
南宮越盯著他的胳膊,就像是要盯出個明窟窿出來。
凌逸辰不以爲意地笑了笑。
先前卿黎讓王搏送來的傷藥,每一樣都有奇效,他只用了幾天,就傷口就已經基本癒合,那其中的筋脈更是銜接完好,連軍醫都說神乎其神。
凌逸辰邊揚起一抹與有榮焉的笑意。
軍醫歎爲觀止那是當然的,卿黎給的傷藥,怎麼可能會差?他從來都相信卿黎的醫,這點小傷當然不在話下。
Advertisement
先前聽王搏說,黎兒聽說他傷,似乎是生氣了。
他可不可以理解,那是對他的關心?
凌逸辰傻傻笑了笑,瞬時覺得心中暖得發燙。
南宮越一副看白癡的樣子看著他,又帶了些如夢方醒般的恍然大悟。
能讓這位冷麪世子爺變稚的,除了卿黎,還能有誰?
卿家的醫哪用得著質疑的?辰恢復地這麼快也是有跡可循了……
上回在太后壽宴上,南宮越也曾驚鴻一瞥過,那卿黎確實是個清雅俗、明麗無雙的子,那種由心而發的淡然舒緩,似乎讓整個熱鬧的宴廳都靜止了下來,只有一人怡然獨立。
這樣的子,無疑是讓人心的,也難爲凌逸辰這個百鍊鋼,爲著變得有所不同。
只是,那麼優秀清麗的子,爲何他見了就沒有怦然心的覺?
南宮越納悶地了腦袋。
他以爲,連辰這種鐵石心腸的人都心了,他這個正常的大男人,怎麼著也不能落後吧?不然,過幾年,都有人說他有斷袖之癖了!
可是,他這些年見過的子也多了去了,就沒有一個讓他心過的!
連他都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那方面的潛質……
想到之前家書傳來,母親又給他定下了那高三小姐的親事,南宮越真覺得自己頭都大了!
一個好好的姑娘家,裝什麼瞌睡癥?
只怕也是個不省心的,估計他這輩子,是完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548 章
盛世嬌寵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於盡,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剛穿過來便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好,這一切她都認了,大家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來日方長,看她怎麼弄死這幫狗東西隻是,說好的不能人道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隻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裡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275.8萬字8.17 57607 -
完結1853 章

蝕骨溺寵,法醫狂妃
她是21世紀女法醫,醫剖雙學,一把手術刀,治得了活人,驗得了死人。 一朝穿成京都柳家不受寵的庶出大小姐! 初遇,他絕色無雙,襠部支起,她笑瞇瞇地問:“公子可是中藥了?解嗎?一次二百兩,童叟無欺。” 他危險蹙眉,似在評判她的姿色是否能令他甘願獻身。 她慍怒,手中銀針翻飛,刺中他七處大穴,再玩味地盯著他萎下的襠部:“看,馬上就焉了,我厲害吧。” 話音剛落,那地方竟再度膨脹,她被這死王爺粗暴扯到身下:“換個法子解,本王給你四百兩。” “靠!” 她悲劇了,兒子柳小黎就這麼落在她肚子裡了。
346.3萬字8.18 58913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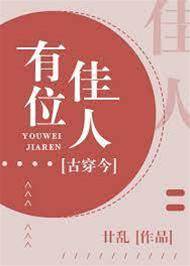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6 -
完結805 章

掌家娘子福滿滿
配音演員福滿滿穿越到破落的農家沒幾天,賭錢敗家的奇葩二貨坑爹回來了,還有一個貌美如花在外當騙子的渣舅。福滿滿拉著坑爹和渣舅,唱曲寫話本賣包子開鋪子走西口闖關東,順便培養小丈夫。她抓狂,發家致富的套路哪?為何到我這拐彎了?錢浩鐸說:我就是你的套路。
151.8萬字8 321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