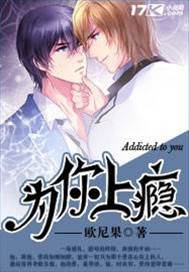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九千歲[重生]》 第50章 第 50 章
第 50 章
薛恕的話卻殷承玉想起了上一世。
上一世他被復立太子, 基卻遠沒有現在穩。在他被幽的五年里,殷承璋和殷承璟各自拉攏了不朝臣。利益綁定永遠是最穩固的關系,即便他是太子繼位名稱眼順, 但為了自己的利益, 那些朝臣也不可能立即倒戈于他。
為了拔除殷承璋和殷承璟的黨羽,他廢了不時間和功夫。
但等到兩人先后死,他手握大權,頭上卻還著一個隆帝。
隆帝這一生, 于家于國毫無建樹, 反而因為目短淺自私自利,給后世子孫留下不害,
都說禍害千年, 隆帝將這句話做到了極致。即便日日吃著丹藥,腦子糊涂了, 也被掏空了,但就是撐著一口氣沒死。
殷承玉等得都沒了耐心, 恨不得親自手送他一程。
但薛恕的作比他更快一步,親手毒殺了隆帝,搬開了在頭頂的這座山,他才順利登基稱帝。
隆帝駕崩的那晚,薛恕押著紫垣真人來尋他。他表一如既往平靜,毫看不出來剛剛弒了君。
“昨日咱家一時興起, 想親手為先帝煉制丹藥,便紫垣真人在旁指導。誰知煉制時不慎, 沒有控制好量, 先帝服用丹藥后便仙去了。”他輕描淡寫道:“咱家怕殿下傷懷,特意押了紫垣真人過來給殿下解氣。”
當時殷承玉對他偏見頗深, 只覺得這人實在囂張至極,弒君謀逆連眼也不眨。
可如今細細回想,卻覺得,他簡直是將把柄往自己手里送。
雖然后來他并未用到這個把柄。
殷承玉抬眸瞧著薛恕:“為何要告訴孤?”他出一手指,在薛恕脖頸上輕輕劃了下,聲音著些許冷:“弒君謀逆,可是誅九族的死罪。”
Advertisement
微微冰涼的指尖若有似無地自頸上掠過,薛恕結滾了滾,聲音又沉了幾分:“殿下說過,不喜歡邊有人。”
“狡詐。”殷承玉嗤了聲:“若真沒有,怎麼現在才來報于孤?”
說是這麼說,語氣卻并不見惱怒,還帶了些許笑意。
薛恕見他并未生氣,便悄悄松了一口氣。
讓紫垣真人給隆帝用還春丹,是他自作主張先斬后奏,他見不得旁人在殿下頭上作威作福。
雖然殿下與隆帝并不親厚,但他將人殺了又是另一回事了。
是以薛恕坦白時,是難得有些忐忑的。
眼下見殷承玉并未生氣,那點忐忑就變了欣喜。他私心里覺得,殿下和他才是一邊的。
他和殿下的關系,比親父子更加親。
薛恕的膽子又大起來,制在心底的/蠢蠢,得寸進尺道:“這次可算立功?”
他個子竄得快,不知不覺間已經比殷承玉高出了小半個頭,直勾勾盯著殷承玉時,頭微微垂著,眼底的緒毫無保留地展出來,像只使勁搖著尾討賞的巨犬。
殷承玉瞇起眼瞧了他半晌,抬手撓了撓他的下頜,似笑非笑道:“那就給你記一功。”
薛恕結了,有些不甘心地抿起。
他想要點別的。
可惜殷承玉并不給他機會討要,又問起了別的:“紫垣真人送了什麼消息回來?”
說起正事,薛恕只得收了心,道:“有兩件事。一是陛下前些日子聽聞直隸疫病之危已解,便讓紫垣真人算了一卦,問何時適宜回京。”
兩地消息來往不便,紫垣真人來不及和他通氣,只算了個較為靠后的日子,在九月里。
若是隆帝回京,行事又要多制約。
Advertisement
但如今疫病已經沒有威脅,阻止隆帝歸京也沒有其他合適的理由。
殷承玉皺了皺眉:“還春丹多久見效?”
“說不好。”薛恕道:“紫垣真人說需看個人質,一般人服用,要見效至也得個一年半載。若是在快,也會惹人疑竇。”
見殷承玉聽完眉頭深鎖,他又道:“不過紫垣真人傳來的第二個消息里,說肖人最近十分得陛下歡心,已經升了嬪位。文貴妃被分了寵,心有不甘,也尋了些偏門。”
肖人是德妃安排的人。
在隨隆帝去南京之間,文貴妃就因為殷承璟給殷承璋下套的事記恨上了德妃母子。殷承璟暫時不了,但面對比自己位份低又不寵的德妃,卻有的是法子蹉磨。
德妃忍了一陣子,在肖人完全得了隆帝歡心,升為嬪位之后,便不在忍氣吞聲,借著肖人的枕邊風,給文貴妃母子上了不眼藥。
兩方爭斗互有勝負。文貴妃不甘心就此被分寵,便人自南地尋了些偏門的法子來籠絡隆帝。
“這回二皇子的差事,便是如此得來。”薛恕鄙夷道。
這回隨殷承璋一道去山東平的安遠侯,正是殷承璋未來的岳丈。
安遠侯的爵位雖是祖上蔭蔽,但他自也算有些本事,早些年平剿匪也立了不功勞。文貴妃想方設法讓安遠侯隨同去,無非就是讓未來岳丈護著婿,讓殷承璋掙些功績。
殷承玉聽完,沉半晌,道:“便讓們先窩里斗著,左右吃虧的也不是我們。”
隆帝現在一人了三份藥,還自以為容煥發龍虎猛,殊不知自己只是后宮之中爭寵奪權的工罷了。
“至于其他,急也急不來,當徐徐圖之。”
Advertisement
總之不論況如何,總不會比上一世更差了。
*
兩日之后,殷承璋與安遠侯領五千軍趕往山東。
半個月后,平叛的軍抵達益都。
殷承璋調用了青州衛的將士,與五千將士一道趁夜突襲,打了叛軍一個措手不及,還活捉了叛軍的一個小頭目。
捷報傳回,朝野上下都一片贊譽之聲。
就連遠在南京的隆帝得了消息,也大加贊譽。
只是高興了不過十日,山東又傳回消息,這回卻是噩耗。
首戰告捷之后,那抓住的小頭目供出了上卸石寨的一條小路。那小路狹窄險峻,卻能直達卸石寨部。
如今叛軍久未被剿滅,便是占著卸石寨的地利。
殷承璋與安遠侯一開始唯恐有詐,先派人帶著那小頭目去探了一遍,證實他所言不虛之后,便趁夜帶兵繞了小路,準備在來一次夜襲。
誰知道叛軍早有預謀,準備了滾石和熱油。在將士經過時,滾石和熱油自兩側落下,將士死傷無數。
這一役,朝廷軍和衛所兵士共計折損了五千余人。二皇子殷承璋在撤退之時失足跌落山間,下落不明。
而叛軍氣焰囂張,在次劫掠了青州的衙和糧倉,人數已經飛快擴充至三萬人。
山東各地百姓聞風而,紛紛響應紅英軍的號召。短短兩月時間,已經有十數支起義隊伍。
安遠侯派回的信使,一為報信,二為求援。
平叛軍損失慘重,二皇子更是下落不明生死不知,朝廷可謂面大失。
如今這個形勢,招安是不可能招安了。當即有朝臣言辭激烈地提出在加派軍隊鎮。絕不能叛軍了氣候,了江山。
但是在派誰去,還需商議。
原先二皇子為總兵,帶兵平叛。結果叛軍沒滅,自己卻先出了事。這丟得可是大燕皇室的面子。
Advertisement
要找回來,唯有皇室之人出面。
一眾平叛人選里,有零星朝臣提議由太子親去山東平。
但也有不人反對,如今隆帝不在京中,太子監國。山東叛軍猖獗,二皇子已經出了事,若是太子在出點事,國柞都將不穩。
朝臣們爭論不休,爭論中心的殷承玉這回卻沒有發表任何看法。
虞淮安尋到慈慶宮來,就見殷承玉獨自坐在亭中,正在擺一局殘棋。
引路的鄭多寶悄無聲息地揮退了伺候的宮人,親自給虞淮安上了茶,便退了下去,在三步遠的地方守著。
虞淮安在殷承玉對面坐下,見他巋然不的模樣,捋了捋胡須道:“看來太子心中已經有數了。”
他本是察覺了如今這波暗里的異樣,才想來提醒一番。但此事看殷承玉有竹的模樣,反而是他多此一舉了。
殷承玉將殘局的最后一字擺完,不不慢抬眸來:“祖父此行,除了提醒,還想勸孤不要去吧?”
平叛軍大敗在意料之中,殷承璋雖武藝尚可,但實在沒什麼頭腦。
安遠侯居他之下,聽他行事,便是有幾分本事,也難氣候。
唯一蹊蹺之,是殷承璋竟出了事。
以文貴妃之謹慎,放殷承璋出來之前,還特意安排了安遠侯保駕護航,像抄小路夜襲這樣危險的事,安遠侯是絕不會放殷承璋沖在前面的。就是安遠侯出事,殷承璋也不可能出了事。
而且送信的時機也有些奇怪,山東到京,信使沿途換快馬,一趟也就兩三日功夫。
軍慘敗,殷承璋下落不明。消息卻遲了四五日才傳回來。
實在反常得很。
在加上忽然有朝臣提議太子親自赴山東平,便殷承玉生了警覺。
山東眼下正著,他若親往平叛,兵敗為叛軍所殺,著實合合理。
“若真是陷阱,此時山東定然已經布下了天羅地網,只等著殿下去了。”虞淮安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殷承玉卻與他的看法不同,他替虞淮安續上一盞茶,冷聲道:“但還有句話,不虎,焉得虎子。”
以他對殷承璋的了解,殷承璋定然沒有這樣的腦子。想出這個主意的,不是文貴妃,就是安遠侯。
他們想趁機要他的命,而他也正想將計就計,弄假真。
既除了一個對手,還能順道平息山東。
見虞淮安還在勸,殷承玉沉聲道:“外祖父的擔憂孤明白。但孤此行,不為平叛,只為山東百姓。”
猜你喜歡
-
連載114 章
偽裝學渣
分班后,两位风靡校园的“问题少年”不止分进一个班还成为同桌。 明明是学霸却要装学渣,浑身都是戏,在表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818我们班里每次考试都要争倒数第一的两位大佬。 注孤生戏精攻(贺朝)x不服就干泯灭人性受(谢俞) 基本上是一本正经的搞笑文,关于成长的一点小事。
31.3萬字8.4 6351 -
完結109 章
情予溫寒
一個(偽)性冷淡在撞破受的身體秘密後產生強烈反應然後啪啪打臉的集禽獸與憨憨於一身,只有名字高冷的攻。 一個軟糯磨人卻不自知的受。 一個偽性冷、偽強制,偶爾有點憨有點滑稽的故事。 為何每個看文的人都想踹一jio攻的屁股蛋子? 面對“刁蠻任性”又“冷漠無情”舍友,他該何去何從?
25.9萬字8 36814 -
完結2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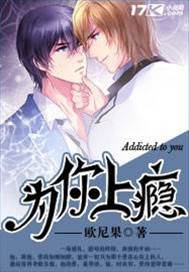
為你上癮
一場婚禮,游戲的終結,真情的開始。 他,林浩,愛的如癡如醉,放棄一切只為那個愛在心尖上的人,最后落得身敗名裂!他的愛,是笑話。 他,時炎羽,愛的若即若離,利用他人只為完成自己的心愿,最后痛的撕心裂肺,他的愛,是自作多情。 沒人能說,他們兩的愛能走到哪一步,錯誤的開端終將分叉,再次結合,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54.2萬字8 6910 -
完結122 章

重生后,我送渣攻火葬場
戚寧玉盛世美顏,能力卓群,無數人等他換老闆或者換情人。 可惜他跟著邢譽川18年,眼裡只有邢譽川一個人,邢譽川說什麼他就做什麼。哪怕邢譽川情人一堆,只要他是最特別的一個,也甘願做其中之一。 直到邢譽川身邊來了個小助理,成了對邢譽川更特別的那個。 小助理問起他們的關係,邢譽川說:“不過一起長大而已。” 他一怒之下開車撞了邢譽川和小助理的車後,重生了。 從此,他眼中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邢譽川。 - 邢譽川分不清對戚寧玉的慾與愛,以為戚寧玉能包容他的一切,哪天他厭了花天酒地就和戚寧玉好好過日子。 等他明白他非戚寧玉不可,卻發現他的寧玉寶貝變了個人,眼中對他再無半點愛意,他瘋了。 邢譽川:寧玉,你想要什麼我都給你,求你看我一眼! 戚寧玉:你扔了的垃圾,還會多看一眼? 年上,相差5歲,人美心狠隱忍受&風流自負佔有欲攻
27.6萬字8 114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